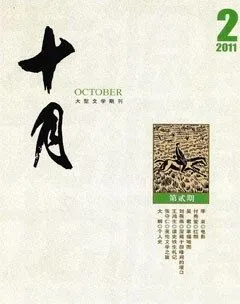读史铁生札记
“性命攸关的一跃”
那一年,《务虚笔记》问世已两年了,除了三四篇专业性评论和几处捎带提及的文字,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社会性激动。就像黑暗中有人投湖,那沉沉的一响,于投湖者是性命攸关的一跃,而在湖水的知觉里,却和掷入一块石头没什么两样。也许,这不值得惊讶。在商业化时代,有多少珍贵可爱的事物、语言和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我们不是照样没有一点儿揪心的感觉吗?
但事情还是有些蹊跷。按当年《收获》的发行量再加上出版社的印数,国内至少有10万人拥有这部长篇。这些人大多知道史铁生,大多喜欢和传诵过短短的《我与地坛》,该是最懂得文学的一类。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同一作者呕心沥血的40万言,却保持了长时间的缄默呢?
“缄默的理由”
曾有仁慈的友人告诉我,铁生的这部长篇是失败的,实在读不下去,真不忍心去说它。也有年轻作家真诚地以为,在一个崇尚行动的年代,这种优雅的形而上冥想已经过时了。而更值得关注的批评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务虚笔记》中的“我”只是各种可能世界的发现者,而不是创造者,“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存在,一个能动的主体。
我不能否认他人阅读感受的真实性,也无意与各种私下的或公开的看法进行讨论。当伴着料峭春寒,再度沉入《务虚笔记》,又一次呼吸它命若琴弦般的纯粹的语言气息,我只是在想,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探询者,尤其是作为与史铁生和他的一系列精神化身(Z、I、F、C等)有着相似经历的“老三届”,为什么我也曾是缄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
当然,这部作品写得细微、缥缈而抽象。由于注重的是印迹,由于在叙述上拒绝构建情节、人物的主线,而它所沉湎的词语或问题既天真又深奥,既尖锐又暧昧,有的甚至玄虚到不可理喻的程度,的确使人很难一下子进入,即便进入了也随时可能被甩出来,所以接受起来需要特别的触角和耐心。而我们大家都活得很累、很匆忙,口味似乎已经被各种文化快餐调教过了,有多少心劲可用于细酌慢品呢?
这能是我得以解脱的理由吗?显然不。扉页上的落款提醒着,作者题赠这本书的时间是1996年11月,而我的几段草率的阅读笔记则写于次年2月。那么,这一年多里,自己究竟忙了些什么,竟无暇对这样一部真正给出了多维叙事空间,并以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努力去复活一代人内心历程的重要作品,作出哪怕些微的反应呢?
由而可知,对“投湖”的人,我们常常是有理由冷漠的。
“阅读伦理”
我知道,阅读史铁生的文字,其反应必须是朴素的、沉静的,就像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低语。它不需要夸饰,不需要宣告、命名,甚至也不需要坚硬的术语和逻辑的较量。触碰《务虚笔记》,就是在触碰一代人乃至一个人的精神隐秘,任何喧哗都将意味着冒渎。
但我们似乎久已不会这样轻声说话了。在这个嘈杂、纷扰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怕自己的声音不够响亮。为了让别人听见,为了引起重视和产生影响,我们更喜欢用亢奋来批评浮躁,用专断来呼唤民主,用智性的狡诈去追求灵性的境界,用即兴想出来的花招去代替孕育和创造,以至长期被套在某种角色化的话语面具里而失去了言说的本心。
我们忘了自己热爱文学的初衷,也忘了批评的兴趣乃始于交谈的必要和发现的喜悦。在体制力量与职业身份的双重钳制并保护下,我们跑马占地,作茧自缚,远离自我,无所操守,还俨然以为自己是既有学问又有德行的。为了确立自己的“品牌”,或为了养家糊口的实际需求,我们不惜拿语言之道的神圣性开玩笑,挖空心思地鼓吹一些不值得鼓吹的东西,煞有介事地争论一些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炮制出一大堆谎话、废话和唬人的话,却无心给那些真正的求索者以最起码的支援、安慰,从而加剧文坛的荒凉、好作品的寂寞。
“词语托付”
我不知道,我,还有我们,是否已伤害了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人曾战粟着,把他的生命、思绪和悲伤变作词语交给了我们,而我们却不置可否,一个转身,就轻慢而随意地丢下了这份艰难的馈赠。如果心没有茧化,如果趣味也没有败坏,我们为什么听不懂那一声声命运的咒语,也感受不到被秘密精神之火焰灼烤的痛楚呢?
想起来了。在断断续续的阅读和联想中,在往事、故人和落叶的飘转中,我也曾用红笔画线、加圈,也曾为一串串会突然燃烧或哭泣起来的句子和影像出神。然而,关于《务虚笔记》,关于包围着它的巨大的冷漠,我依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写,仿佛这完全是一桩与己无关的事情,可以听之任之的事情。
在这本书的第465页,作者曾写道:“如果你看我的书,一本名叫做《务虚笔记》的书,你就走进了写作之夜。你谈论它、指责它、轻蔑它、嘲笑它、唾弃它……你都是在写作之夜,不能逃脱。”
可我们大家不仅逃脱了,而且逃脱得非常轻巧。
“务虚”
让那些真正困难的创造自生自灭,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真相。关于这一点,不说也罢。问题在于,我自己是怎么回事?难道在骨子里我也对“说”和“写”的意义失去信心了?
是的,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确常感到无望,感到滋润一切文学之梦想的东西已瓦解殆尽,而寒意和无力感则浸透了全身。在物质化的喧嚣声中,我甘愿承认自己的卑怯,一种属于肉身的不由自主的卑怯。不服气吗?请看现在,这个致命的现在,除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神话,除了对钱、权力、名声的炽烈兴趣,又有几个文化人愿意切切实实地“务虚”,愿意在夜阑人静时分坐下来,就“我”的来历和去向作一番史铁生武的盘问呢?
“写作之夜”
唉,凌晨出生时的那场大雪,要做一个好孩子的决心,希望自己成为烈士遗孤的幻想,没能赶上战争年代的遗憾,还有写在美丽女孩脸上的童话和那房子里成排成排的书柜,或者串联时闷罐子车里姑娘肉体的温热和突然掠过心头的羞耻感、罪感,以及在一场历史编排的戏剧里所发生的歧视与孤独、仇恨与惩罚、光荣与屈辱……如今,还有谁记得它们?
如果没有语言“务虚”的炼金术,没有“写作之夜”的游思、招魂与天问,那么,“我”就不啻一个失散久远的梦,一个沉没在无垠黑暗里的梦,你将上哪儿去找“我”?!
“我在哪里”
尤其在那个个人化写作刚刚开始的年代,《务虚笔记》被“埋没”似乎更显得意味深长。什么叫“个人化”?什么叫“个人叙事”?实在已被人弄得一塌糊涂。于是,一些不断复制着普遍现实和可疑生活,甚至在经验、趣味和语汇的卑琐性上也十分雷同的东西,总有人赞赏、有人炒作;而唯独心灵的远行,疑惑不定的歌唱,以及从无尽的自我争论中才产生的严酷的诗意,却少有人加以问津。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强调“个人化”,却无视“我”的存在或缺席,难道“个人化”反而拒绝自我的追溯,反而不要求面对个人的真实,不期待灵魂在语言的历险中一次次重新生成?
我们在恐惧“我”,压抑“我”,不想让“我”有出头之日。我又恐惧什么?我恐惧“夜”,恐惧“思想”,恐惧真正有挑战力的“写作”,因为它们须得用血肉来喂养,必须得和成堆的烟头、着火的神经一路同行,而死神的阴影就尾随在后面——谁体验过这一切,谁就会加倍渴望闲适、轻松和愉悦。
“重量”
而那个叫“史铁生”的人却说:“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为了获得这一点“重量”,现在他必须隔一段时间到医院去做一次“血透”。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沉默的健康人,是否也活得过于祥和、怯懦?
写到此处,窗外起了大风。风打着卷,呜呜地叫着,送来一阵又一阵悲戚的哨音,就像不绝如缕的爱与死的歌声。我想,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来讲,只要还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旋风中站立,那么,它的重量就永远也不会被轻轻抹去。
“心游”
不必讳言,史铁生的写作并不具备社会批判的直接性。如果熟悉他的风格,这一选择的美学缘由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我们知道,被迫接受轮椅里的日子,曾使史铁生感到非常愤怒,但肉身的难以行走,最终却帮助他发展出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心游”能力。作为心灵历程所留下的一串串影像、印迹,他的作品从题材、形式到语言,都发散出一种“心游者”所特有的气质:缥缈、隐秘、执著、自由,细致入微却大而化之,凝神玄想又无所羁绊,直到秘密的精神之火燃起,思想便开始了沉静中的舞蹈。心游的具体性不同于现实的具体性,当然,心游的具体性也不能替代现实的具体性,也许,这正是史铁生总是敏感于某些特定日常情境,却始终避免从正面突入现代生活故事及其场景的原因。
“行魂的身器”
心游的经验对史铁生肉身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铁生第一次使用了“行魂的身器”这一说法,迂回地发掘出一种关于“人”这种生灵的诗性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亲密而又疏离的叙述语调,使行魂与身器像一对如影随形的伙伴,处在一刻也不得消停的对话之中。两者虽不平行对称,但也不存在权力或主奴关系:一方面,行魂与身器互为依存、不可分离,就像“我”从“亚当”到“丁一”再到“那史”迁延而来,行魂出离了某一个身器,又会冲向另一个身器;另一方面,身器并不简单地就是行魂的容器,身器也会说话,就像性也是表达,因为“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
“字迹”
如果行魂可以说“我”,身器也可以说“我”,那么两者之关系就类乎印度哲学所谓的“我中之我”了;但又不仅如此,因为史铁生叙述的落脚点其实不是意识或潜意识、经验或超经验的层次问题,而是虚无缥缈间那一点不死如我的“心识”,或小说结尾处那需要久久端详、辨认的“字迹”。
似乎可以推想,行魂的最终身器离不开语言,身器与行魂的扭结点也离不开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梦与醒、遮与裸、祈告与回忆、拥抱与吻别、哭泣与吟唱、出发与回归,人世间乃至宇宙间的一切声音、动作、形态,其实都昭示着某种神秘的源于生命的表达意志。
“身体语言”
语言即道。尽管史铁生关于“行魂”、“身器”的意绪十分缠绕,可一旦从语言入手,其思想竟变得单纯透明起来:不是道“成”肉身,而是道“在”肉身!史铁生曾反复强调,爱包容着性,爱与性不可剥离,“爱情之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确切地说,在基督徒那里,洗净“我”罪身的宝血必来自耶稣基督,但对史铁生来讲,这“宝血”却是诗,是裸露、抚摸和战栗,概而言之,是身体语言的仪式化。
“非框架化”
当命运的展开与归宿成为向“上帝”的一次践约,某种故事的终结性就出现了,一切变数在根本上应是己知的和可完成的。时间经验的可框架化,清晰地画出了文本的边界。
而《我的丁一之旅》则完全不同,这是一部极为奇特的精神自传,写得如天书,如伪经。全书共156节,叙述体例摇曳多变:1、标题释义(7节);2、行魂的第一人称叙述(136节);3、史铁生插话(4节);4、引文与猜想(6节,大多引自史本人的《摇滚与写作》一文);5、电影《性、谎言、录像带》转述(1节);6、唱词《魂觅长宵》(1节);7、补遗(1节)等。文体和句式也五花八门,从诗和戏剧,独白与对话,口语和方言,抒情与分析,格言与警句,直到骈文、唱词与科普小品不一而足,遍布全书的大量问答则颇似佛家讲经用典。
小说中,虽然被叙述者丁一的生活时间从出生到死亡情境历历、有迹可循,但叙述者“我”(即丁一的行魂)的旅程却是未知的和未完成的。时间经验的梦幻化和非框架化,使文本的边界显得模糊、开放而充满弹性;叙述的空间化倾向,视点逡巡的游移不定,语态的幽默、暧昧,心魂在重重疑难上的纠结、盘旋,都表明作品的语义释放方式具有弥散性、反复性、随机性。可以设想,如果不打破各种时间限制,作者是不可能写得如此自由放浪的。
“魔术时间”
小说往往以虚构形式探索时间之谜,小说也赋予时间以不同的形体,这些不同的时间形体正体现了时间经验的多样性。也许,对线性时间观及由此而导致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小说正是天然的解构者。这是因为,在写作或阅读过程中,“过去”、“将来”必然涌现于意识的“当下”,从而时间只能共时性地凝缩为空间的“面”或“点”;同时,阅读时间、故事时间、叙述时间三者之间所发生的多向、多重、多回路关系,总是会不断地打破线性时间的幻象。
史铁生是深谙这一时间分裂、聚合的奥秘的。在他的想象中,时间是跳荡的、非匀速的、不可量度的,时间片断可以任意剪辑、组合;但又不仅如此,时间还因与心情毗连而具有感性特征,它有时是活泼的、满怀热情的,有时又是沉重而忧伤的——时间静静地流淌,“时间真是沉重又忧伤啊”。
如果说生活时间(身器的时间丁一的时间)有开始有结束,而神圣时间(上帝的时间爱的时间)总体上仍滞留于将来未来之际,那么行魂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呢?是贯通心识与身器的时间,是出生之前、去世之后的时间,也是从有限通向无限的时间,一种无名的时间,难以图像化的时间。也许,它就叫“魔术”和“戏剧”。
“在姑父讲过的故事里,最是一个涉及魔术的故事让我难忘”:在倚山面海、景色宜人的E城,一位华裔魔术师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神奇地拨动了所有观众的手表,让他演出迟到的半小时不翼而飞,在时光倒流中,全场一片惊嘘。魔术通过对线性时间刻度的改变,彻底打破了人们预设的时间观念,使所谓的客观时间忽然变成了主观时间,这使丁一终生难忘,也给他日后梦幻般的生涯埋下了一大伏笔。
“爱情乌托邦”
丁一之旅的后半部分,重心就落在了“爱情乌托邦”的戏剧构思与排演上:先是丁一与娥,在月光如水的房间里彼此凝望、呼唤、裸舞、絮语,对童年的卑微、青春的失落给予种种补偿;继而,萨又加入进来,在月色迷蒙的三色地上,心彼此穿“墙”而入,令人感动的躯体敞开它们的秘密,爱与自由在晕眩中扩大;然后,是白昼到来……
爱作为一个约定,原是为了把“别人”合成“我们”。但行魂寻找亚当或夏娃的旷古难题却一向是,“遮蔽之中,就怕‘纵使相逢不相识’。敞开之下,又可能‘过尽千帆皆不是”’。虽然已明白劳动、语言、精神、爱均系于一“情”字,但丁一却又对“性”忽生亘古之疑:“裸体,为什么可耻?……嘴可以笑,齿可以露,何以单单屁股要小心地隐藏?”性,这自然之花,这天赋的吸引与交合,何以会导致“羞耻”?那两片无花果叶究竟藏着什么玄机?当然,时下那些黄书、裸照、毛片,那些简单快捷、直奔主题、不让人感动、不具备仪式感的“脱”,丁一实在看不上,但若盼望、惊惧、晕眩、迟疑、踌躇、颤抖伴着那一声“脱”字而来,岂还是堕落?丁一太不甘心了,既然是谎言、墙、“裸体之衣”等使“伊甸盟约”变得遥遥无期,那么,“至少在某种时刻,至少要有一种机会,人与人可以赤诚相见,可以相互袒露心魂”。
“夜的戏剧”
戏剧就是这种机会和时刻,丁一的理想生活就在夜的戏剧里。夜的戏剧能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让不现实可以实现,“比如说,白昼的戏剧先要化装,夜的戏剧是以卸装开始。比如说,白昼的戏剧是要你来扮演别人,夜的戏剧则一概由‘我’来演出自己”。于是,舞台灯光照亮了一种时间,这时间是现实外的时间,时间之外的时间,这种时间可以被“眺望”,也可以被“拥有”。如果说时间是第四维,那么梦就是第五维,梦的时间就是戏剧时间,戏剧时间是用仪式化的身体语言来重塑时间、创造时间的时间。
“设若时间并不是钟表,现在就到了‘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设若时间不是钟表,亚当和夏娃便可借助任意的男身女器而畅诉别梦离情。设若时间不是钟表,一切就将回到创世之初:心魂消失掉界限,冲破‘你’‘我’的命名,跟随着上帝的灵在浩渺的水面上汇合……”
然而,丁一“去掉一切墙”、打破“他们、你们、我们”之壁垒的自由交往理想,却遭到了清醒如秦汉者的反对(“人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现实当成戏剧,又把戏剧当成现实”),也让女孩们感到危险和恐怖(“就怕你消灭不了隔离,反倒消灭了保护”;“你们的戏剧,不会助长出一个指挥者,或操纵者吗?”),尤其当丹青岛上那一记沉重的斧声传来,诗人岛与其两个爱人的美丽故事竟以流血告终,丁一彻底傻了。
秋风已经起程,荒野不知何往,他实在无以回答:“爱情,既然是人问最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却又为什么要限制在最最狭小的范围内?”但爱人“如果可以多,为什么不可以再多”?爱情要求彼此“交出”自己,这会不会造成“权力”对自由的控制?如果放逐权力的自由之爱却要用权力才能来维护,一切岂不是太荒谬了?然而,“不给人自由固然有点儿那个,可要是都他妈自由了呢?咱还往哪儿走”?天哪,“自由与梦想之间,上帝的手指向何处”?!很快地,(嫦)娥离去了,萨(宾娜)走开了,丁一神思迷乱,周身滞胀,那沐浴了忧哀与怨恨的癌之花再度盛开,他终于不甘地合上了眼睛。行魂“我”悬浮其上,徘徊其周,不得不带上他的遗梦继续追寻——“一切话语,都被白昼之王所废。那便是心魂回归黑夜,重新去锻造一种语言或一条道路的时候”。
“心识”
行魂不死缘于心识不死。这“心识”概念显然源于佛教的“一切种子心识”,即除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之外的第八识,也叫阿赖耶识。在佛学唯识论中,该“识”属根本识,它是起因,是实有,是保存善恶业的种子,也是众生轮回的主体,虽瞬间有变,却恒常存在,即便修身成佛时也不会中断。“如同水在沙中嘶喊,或风自魂中吹拂,虚无缥缈间凝聚起一点欲望——心识不死。我知道,我即将进入又一轮身形。”由此可见,一如佛家用语,史铁生的“心识”也具有欲向性、持存性,既指一种生成的能力,也指回忆、祈盼和希望的能力。所谓丁一的戏剧时间,不过是心识无量时间的自由变造罢了。
“丁一”
说起来,这丁一倒确乎是个“情种”坯子,行魂当初特别看好他,投向他,是因为一想到托魂犬马、猿身鱼体的往事,顿觉“情思沉荒、爱欲凋敝、寸梦不生”的生命没有一点盼头。凭借心识,行魂唤醒丁一的第一步是让他学会叫妈妈,第二步是眺望自然:太阳、新鲜的眼眸、风、树影、山峦、飞霞;待人形之器长成,丁一便喜欢起阿春、小姐姐、泠泠、梦中的白衣女子,并沾染了虚荣、馋嘴、好色、好名的流风积习;初省人事,他幸或不幸地经历和目睹了红袖章、批斗会、父母级别、贵贱轮换的人间真相,也备尝蔑视、羞辱和被逼“出卖”朋友后的绝望;他先后结识过牛氓、保尔、江姐、甫志高、浮士德、哈姆雷特、奥赛罗、西绪弗斯,还学会了许多像“兰花花”、“十五的月亮”、“田野小河边”那样土的或洋的情歌;自然,也离不开屈原、李贺、艾略特的诗,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昆德拉、博尔赫斯的小说,以及伯格曼的“钟”、达利的“表”、帕瓦罗蒂的“太阳”……设若没有这些,没有更多的神话、猜想、故事、民谚、歌谣陪伴着孤独的岁月,又哪里会有若多心识的积业,又哪来的丁一之旅?说到底,所谓行魂,不就是这一系列的消息和传说,不就是对这一系列消息和传说的惊诧、感悟、领会、记忆和传递吗?
“心史”
我们务必要避免对“行魂”的误读,仿佛它已是某种存在的“物”。“行魂”是动词,至少是动名词,绝不可单一名化地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若发生混淆,则好比西哲所谓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那问题就大了。故而,植入史氏文本的大量人文用典,当然也就与不涉灵魂历史的后结构主义“互文性”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打动我们的这一切,绝不是“词语联想”而是“生命体认”,不是“语言游戏”,而是“存在之思”。
一代人的心史也是一个人的心史。今天或今后的中国读书人,但凡有踟蹰于“情种”与“强者”的,要“平等”而不要“平庸”的,或对“唯一真理”和“随便怎么都行”存在着双重疑惧的,相信都不会对“丁一之旅”所遭遇的困顿感到陌生。虽然“丁一之旅”是一段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但它也是“一切历史的征兆”;虽然,《我的丁一之旅》是对这一段奇特生命的极为瑰丽的怀想、依恋、传承。但它也是刻骨铭心的纠缠、反省和告别。
“死”
丁一死了吗?!
这里不妨逗留一下,让我们先想一想:什么是死亡?
直观地来看,死亡就是不再呼吸,不再开口说话,即一切生命行为的终止。现代生命科学也告诉我们,生命其实是一种应答和表达机制,死亡即意味着不再能够应答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对不再能够继续表达的恐惧,宛如“对留下一件未完成作品的恐惧”。
进一步探讨则可以发现,人类乃是唯一能预知自己死亡的生物种类,其“生”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其“死”倒不是一次性的,人确乎会一次又一次地面临或遭遇死亡,甚至他人的死也会成为自己的死,所以,当海德格尔把“向死而在”作为人的基本生存特征来加以阐释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但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非伦理性却表现在,由于夷平了此在的迥然不同的具体处境及其应答,也就夷平了辗转于生死之间的生存活动的价值差异,要知道,那些亡命徒个个都不缺乏向死而生的自觉和勇气啊。关于死亡,同样出自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门下的犹太思想家列维纳斯,却与海德格尔有着不同的体验,在他的暧昧的智慧形式里,死亡将始终作为一个疑问而存在。例如,死亡肯定是告别,但能否重逢却是一个疑问,因为死亡也是“出发……向着陌生出发,毫不复返地出发,‘不留下地址的’出发”。既是告别又是出发,既是对生命的公然劫掠又是对它的亲切召唤,这一模棱两可性毋宁在告诉我们,作为无名者的判决,死乃是不可思议的,垂死者接受死亡的心情无论怎样平静或者不甘,也不能改变死的荒诞性。饶有意味的是,在列维纳斯的想法里,正是持有了这一“死”的荒诞性,才使“我对他人不求回报的责任心变得可能”,因而,与死亡的关系也就成了自我对他人的责任关系。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了,史铁生为什么一方面确凿无疑地安排了丁一的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把他托付给永远的“行魂”。这一“死而未死”的矛盾,不仅扭结着作者乃至读者对人生命运的十分复杂的态度,而且隐微地转达了任何信仰表述都不得不依赖的某种神话式的语言智慧。也许,只有把死亡永远地留在疑问里,才能留出一个伦理的上升空间以有效地抵抗虚无主义,也才能为幸存者赋予生的责任,并使其在向死而生的紧张里葆有某种希望的可能性。
这一思考死亡、对待死亡的方式大有深意。沿着这一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朽也是可能的了,比如,当那些伟大的亡魂所留下的事迹或文字仍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说他们已经死了呢?所谓不朽者,难道不就是指那些能够不断复活的表达吗?既然表达和应答一直在进行,那么生命的存在及其价值、意义的永恒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若不是参悟到这些,史铁生也许就不会那样去设计丁一的故事,而小说的叙事功能和信仰功能,也就不会如此完美地统一在一个关于“死”的疑问里了。
“自由的反讽”
史铁生因深入“自由”的疑难而不得不借助“反讽神话”——这对我们来说,已不是什么难以揭晓的秘密了。从窥破人间真相、构思爱的戏剧直到落入自由的悖论,短暂的丁一之旅经历了漫长的精神跋涉,一如骄傲的行魂要丁一那厮记住的:“我就是旅途,是坎坷……”在这条道路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疑难,像心魂与心魂怎样才能相见,不敌视也不怨恨的世界是否可能,究竟是什么让人不得不爱,又是什么在阻止b7c95eedcf643939719571c5fa6e84c3着爱的到来等问题,都曾使丁一伤透脑筋。
但最大的疑难还要数自由的疑难,其难就难在一方面自由的本性是无“度”的,另一方面自由又必须与真、平等、爱等统一起来,两者只要缺一,“自由”肯定就交得不自由了。以此观之,一部以“自由”为主题的小说的叙事构型,几乎注定了只能是反讽的、神话的。这就难怪丁一也难怪我们了:徜徉于自由之迷宫,陶醉于自由之神吉光片羽的闪拂,为什么搜遍古往今来的哲言,也找不到那破门而出的秘诀?
行魂“飞飞飞,茫茫而不知将飞去何处”,但人们又听说,“所有流传的歌都是情歌,所有的情歌都似哀歌……所有的哀歌都是祈祷”,莫非祈祷就是自由之路的希望,而“希望,恰恰就是通向,而非到达”?想当初“那丁”是直承亚当、约伯而来,如今“此史”会不会奔阿罗汉、释迦牟尼而去?行魂的自由之旅啊,你一次次永不知疲倦地起程,秉承的又是谁的旨意呢?
“重写”
在下意识中,每个猜测着存在之谜的作家,都会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永恒,之所以需要反复讲述,乃是因为它一向无形,且变幻不已。
《我的丁一之旅》等于把《务虚笔记》又重写了一遍。这次重写让世人感到惊心动魄、难以置信,但那个轮椅上的骑士却显得这样安详,这样出神入化,还带着点儿俏皮。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重写啦。
这次重写意味着:史铁生完成了,永远地完成了;他已经给当代汉语文学注入了它从未有过的东西;他真正找到了“存在”的灵魂,也找到了讲述这个灵魂故事的出窍的语言。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