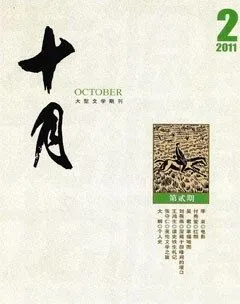轻喜剧中的危机与隐忧
小说家劳马在大学任职,他是一位校领导,但他首先是一位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的身份又写小说,劳马就非同一般了。我们可以在有这样身份的人身上看到性情,看到他在关心什么,看到他站在哪里看社会又看到了什么,他是什么态度。劳马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集,除《傻笑》是中篇结集外,劳马多写短篇,特别是微型小说。这里集中发表的八个小说,也是微型小说。劳马的小说写的是人间万象,是官场、机关、交际场合和日常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小人物是劳马观察和书写的对象,而他的小说反映和折射的则是一个大社会。因此,劳马的小说大体属于社会批判小说。但劳马的批判又不是金刚怒目、怒火中烧、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式的仇恨。他的批判都是寻常人普通事,他是用讽喻、调侃、漫画式的笔调书写他的人物,因此他的小说有人间轻喜剧的味道。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看到劳马善意的人生态度和他的小说立场。
劳马笔下的人物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地产公司联络主管白丽、生意人老鬼、公务员小张、班干部王广田、乡长老曹、科级干部老赵、处级干部老史、司级干部老庄等。这些人物就这样构成了劳马的“社会”,对他们的书写,也就是劳马对社会的面面观。有趣的是,劳马的小说是围绕着当今社会的“中心”——官场展开的。他从小公务员一直写到司局长。两个与官场无关的生意人白丽和老鬼,他们的性格塑造也是在官场和世俗生活中得以完成的。这个场景是世风最典型的场景。一个庸俗不堪的交际花,在交际场合的资本就是自吹自擂的“旺友旺夫”,那些不断附和的“麻友”是何等人物不言自明。小说几乎是对白构成。不但处长、博士、科学家都在证实“白姐”的神奇,“反正凡是与白美女见过面的人,事后要么升了职,要么赚了钱,要么分了房,要么出了国,个个都沾了光。就连老赵的小孩也说白姨救了他的命,有一次吃饭让鱼刺卡住了嗓子,正好碰上白姨到家里串门,他一看见美女姨姨不知怎么着,这鱼刺就下去了”。这是“白姐”神奇功效的基础,它助长了“白姐”“旺友旺夫”的自我膨胀。但是,就在一次送醉酒“自姐”的路上,“我”出了车祸。在医院面对重伤的“我”,“白姐”仍然夸耀说:“你说你多幸运,要不是我在你身边,你早就给轧成肉馅了。那辆车都撞报废了,你还能活着,简直是奇迹!而且,撞你的是一辆新款宝马,多有档次!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总会给周围的人带来运气,这回你信了吧?”已经重度脑震荡的我居然觉得她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在当事人康复出院后:“我瘸着腿一步一拐地走在路上时,又不时地怀疑白丽女士的说法——我因跟她在一起而发生了车祸,撞成了终生残疾,这怎么会是一种幸运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若那天不是她在身边,我会不会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呢?”这当然是一个反讽。一个经常处在幻觉中的人,也会使正常人产生幻觉。这个小说貌似简单,但就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却让人欷歔不已——那是我们经常见到的熟悉的人物。
当下生活中颇流行“潜”什么——潜规则、潜话语……《潜台词》是“潜”生活的一部分,“潜台词是一种表达艺术,在某些特定场合和特定人群中普遍流行。它指的是不明说的言外之意。俗话讲‘敲锣听声,说话听音’,就是让你去用心体会弦外之声、画外之音。”老鬼是研究“潜台词”的,因颇有心得而深得上司欣赏和信任。但“潜台词”的学问因人而异深不可测。他从领导的“你这条领带挺漂亮”开始,先送领带,然后是衬衣,然后是西装皮鞋。但领导的一句“这种衣服我平时也没机会穿”,将他送的东西全部否定了的同时也暗示了老鬼新的行动。他迅速组织了“企业家考察团”陪同处长赴欧洲各国考察,当听到领导鼓励儿子到德国留学。老鬼一口答应处长儿子留学的事情包在自已身上,老鬼的“大项目”也终于尘埃落定。劳马发现的是,权钱交易也是一门艺术。
《脑袋》、《重要情况》、《老史》、《佩服》、《初一的早晨》,都是写官场的。官场小说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长盛不衰,其中的隐秘并不复杂。官场腐败既是一个现象,也是一种奇观。作为现象对其批判是政治正确;作为奇观又满足了读者窥视欲望,潜在的市场有可以预期的剩余价值。这两个因素是官场小说前赴后继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么多年的官场小说在美学意义上与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相比,除了时代背景的差别外,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元素,我是怀疑的。那里除了钩心斗角、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情妇情夫就很少再看见什么了的官场,一定是想象的“官场”o但在劳马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官场。这是一个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官场,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官场。官员并不是每一个都居心叵测青面獠牙,都在等待送礼美女上床。就像《潜台词》一样,交易是一门艺术,它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比如《脑袋》,局长生病了大家都要到医院看看。这原本也是人之常情,领导也是人,也要交往或关心。如果有人不去看也很正常,就像我们也不是谁生病了都要往医院跑一样。但当下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局长生病了下属没去看,不仅老婆着急,就连打扫厕所的保洁员都着急。这就不正常了。有趣的是,局长连这个下属姓王还是姓张都不清楚。更糟糕的是好似局长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癌症。不久于人世的局长不仅再没人去探视了,而且准备接替局长的副局长正在调查曾探视局长的名单。世道人心在一个细节里将炎凉写尽,人际关系的全部学问如千年古潭深不见底。但不知所措的不仅是下属,《重要情况》中的赵科长,如何当上科长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东拉西扯的本事足以让再有修养的人忍无可忍。他的所谓“重要情况”无非是告知处长:新上任的厅长是他舅舅。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重要情况”,将赵科长内心的致命庸俗跃然纸上。与赵科长略有不同的是《老史》中的老史,这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他得到了体制所有的好处,可以分到最大面积的房子,后来又升任了副厅级。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精明,他把体制的问题和可能得到的好处都看清楚了。因此,他不必请客送礼,不必阿谀奉承,也不必低三下四就把事情都办了。老史是好人吗?老史怎么会是一个好人呢。这种人的可怕就在于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清楚了,然后又掌握了权力。老史与老赵是一种人的两种表现,他们的话语方式不同,但背后的目的没有区别。如果对这种人物没有长期的观察想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佩服》中的“庄领导”是一个典型的“喜剧”人物,讲话时嘴角有两堆白沫卷起,这个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京剧中的“丑角”。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能够将秘书作为备份的另外两份讲话稿一起读下来,一样的稿子他读了三遍还浑然不觉,却抱怨秘书将稿子写长了。对这样的领导除了“佩服”还能说什么呢。《初一的早晨》是一个过于离谱的早晨。大年初一乡长带了一干人马给村民赵三柱一家拜年,乡长不是每年都来这个村民家拜年,今年的拜年只因赵家出了“中央领导”。赵家二儿子不过是一个在国家机关工作、工龄不满四年的青年。春节返乡探亲在乡长看来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敲锣打鼓”三拜九叩,第二天县领导还要请吃饭,只是他们请的不是村民赵三柱,那些煞有介事背后的诉求昭然若揭。
如果说劳马写的那些官场场景带有轻喜剧意味的话,那么《班干部》就显得有些悲凉了。一个几十年不见面的初中老同学千里迢迢、带着两箱成鸭蛋来找“我”,不是为了叙旧,不是为了少年时代的友谊,只是为了证明他初中时当过“班长”然后填进“干部履历表”里。一个即将退休的人,一个是否当过“班长”同学都似是而非的人,执意证实曾经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但在王广田看来,“他这样做不为提拔,也不为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这个不可思议的“荣誉观”透露的是当今社会的“价值观”:“班长”也是“干部”。它深入人心可追溯到初中阶段。过去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必须是“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在今天确实被夸张地放大了。对社会、对个人,具有支配力量的价值观才是“核心价值观”,如果“官本位”的价值观有如此的支配力量,它对于社会和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劳马的担忧当然不是杞人忧天。
对世风描摹目光的老辣,在貌似轻松中的深刻,在并不复杂也无一惊一乍的风浪中表现官场的生活,是劳马的功力。劳马的功力就是四两拨千斤,就是从容淡定中望穿秋水。这就是绵里藏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人物塑造上,劳马是白描的笔法,寥寥数语、几句对话一气呵成,性格面孔和盘托出跃然纸上。这种功夫现在的小说家已很少顾及,更多的是钟情于更复杂、更有“技术含量”的手法,看起来技术成熟了,小说也复杂了,但是就是看不见人物。小说如果写不出让人记得的人物,大概就有问题。多年来,我们总是说如何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但那是整体文学方向、文学观念的影响。在写人物方面我们大概接受得还很有限。在俄苏作家那里,比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中小文官的卑微、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阿尔连采夫的阴谋家嘴脸等,都因写得生动而令人过目不忘。这些经验在当下的小说中已经很少看到,但恰恰是这些细部的描写、刻画,帮助小说完成了人物的塑造。我们当然不能说劳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高度,但他的人物塑造显然有效地汲取了这些经典作品的艺术经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更重要的是,劳马的小说在轻喜剧般的戏谑中,隐含了他深切的隐忧。他对官场日常生活场景的捕捉和提炼,表达了他鲜明的批判立场。在那里,没有路线斗争,没有方向错误。但是,就在那习以为常的日常状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危机或危险:这就是没有敬业,没有责任,人浮于事,心不在焉,得过且过,官员只有“身份”要求。如果这种“身份”建立的只是等级社会而不是责任,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当然,劳马的风格选择似乎也让我感觉到,为了文学,他牺牲了尖锐;为了善意,他选择了轻喜剧。但是,他书写的生活已经令人惊心动魄,那里隐含的惊涛骇浪足以摄取人心。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