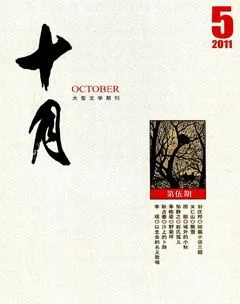安丰镇
安丰为兴化地区第一大镇,人口十万,土地一百平方公里。从兴化乌巾荡起始,海沟河向东北方向由西鲍、钓鱼镇,缓缓绕了一个弯,经安丰、老圩、新垛、大营四乡镇,进入串场河。这条河道应该是境内四条入海水系中最长的一条(测量数据记录,从西鲍镇到出口处,计50.3公里),未通公路前,这条河道联结了兴化东北部地区几个主要乡镇。安丰镇在沿河六乡镇中段,也是海沟河由北向东的拐弯点。最近六十年兴化地区治水工程中提到最多的是中腹车路河,北面的海沟河相对比较平静,2009年的兴化水利规划中,也只是提出浚理安丰下游二十公里长的河道,以便出口畅通。现在我们已不太能够看出海沟河对于安丰镇的重要,但按照当日兴化地区四大东西径河形成的地形来看,安丰成为兴化最大粮区以及东北乡镇商贸中心,相信与海沟河的水利有关。当海堤挡住了海水倒灌后,海沟河安丰以东部分形成了一片可供耕种的良田,尽管由明入清以后很长时间,安丰还兼带管辖串场河沿岸刘庄、白驹、丁溪、西团四大盐场,但那是国家经营与专卖所特设,安丰本身却依赖土地之利走向“物丰民安”。农业为安丰立镇根本,在1940年之前,土地虽见兼并之势,但相对集中的土地耕作,却也使安丰镇成为东北乡粮食运储与交易中心,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本镇商贸的发展。说安丰是兴化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型农贸乡镇,应该没有问题。也因为有如此经济社会,安丰镇在该地区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地方政治传统中,乡绅阶级通过水利这一特定的地方需求,持续发挥着社会中心作用。设立于清乾隆时期延至民国后期的“东北老圩局”,可以看做是安丰镇乡绅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
兴化旧制分为十镇六区六十六图,安丰镇分领兴化东北乡,所以称“东北”。老圩,则是由海沟河与兴盐界河之间最早筑圩形成的一块三十多平方公里十五万亩土地的圩区,该圩区从乾隆时期为东北乡主要农业生产区。后来圩区向西扩展到海沟河中游的钓鱼庙,分别又有“中圩”和“下圩”加入。“局”是清初以来中国南方乡土社会普遍设立的民间组织,有多种社会作用,安丰镇的“局”专为管理圩区水利,由各圩区不同等级的乡绅组成,其中分总办、圩董、图董、庄董、段董等,均由圩区内各图(图:纳粮单位,通常以多个村庄为组织,区域范围较乡要大)各庄推举。每年4月至9月六个月,上述人员“在局”办事,按照制定的规约,处理水情旱情。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中水利与农业生产的关键,例如西水下注时的分工协调堵坝筑堤,或旱情发生时水源的分配等,等9月一过,秋收在望,大家就解散了。
写于1940年代的陈邦贤《自勉斋随笔》,其中一则关于安丰土匪李花魁的逸事,从另一角度和层面可以看到乡绅政治在“乡治”社会中的作用。
李花魁的主要活动在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末年,离陈邦贤的记述相距近四十年。当年李花魁的横行不法,以及安丰人的同仇敌忾,在这部笔记里叙述得还算生动:
“兴化是一个水乡,他在钓鱼庙一带,横行无忌。到了秋天,那城上的人都要下乡去收租,必定先要向他打一声招呼,3wK2SMCcvTvy/pAA2XpdFw==由他派人坐在船上,保护那稻子出境;否则那稻子或是卖出来的钱,休想带得回去。他在乡间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没有一个人不愤恨他,也没有一个人不畏惧他。可是报到官厅里来,官厅里也没有方法去剿办他。安丰镇到钓鱼庙一带,几乎都成了另一个世界。乡下人气愤极了,便私下集议一种联防的方法,一遇匪警,鸣锣为号,那邻庄听得锣声,便随即赶来,以翻扒、扫竹做武器,和匪尽量地抵抗。那庄有通匪的地痞流氓,便自己处置,把他活埋。某天大家齐集到了安丰镇,便把匪首李花魁打死,其余的匪党也就如鸟兽散,于是各乡镇也就安靖了。”
李花魁,安徽人,为出身“安清帮”的一黑社会头目,在安丰地区纠结党羽,盘踞多年。他在安丰上游十多里处的钓鱼庙私设关卡,掌控了整个东北乡往兴化城的粮食运输与贸易水道,坐地抽税强制收费。这就危害了本地区经济社会利益,为乡绅们所痛恨。事实上,并非一般民众“私下集议”,而是安丰乡绅以靖安地方的名义,公开发起民众,将李花魁一党彻底铲除。安丰地方志作者对此有详细说明。1906年秋天的这次地方治理运动,由六十六图总董中圩的赵士范策动,他邀请东北乡各图董在安丰镇罗汉寺集会,会议商定农历8月12日举事,各村庄每一“烟囱”18岁至45岁青壮农民,自带农家工具作武器,到安丰镇上“除匪”。帖子发下,这一天据说前往安丰镇的农民达到万人,而李花魁则在追躲中,被一农民发现,用大锹铲死在一个猪圈旁的草堆里。当日之事,以李花魁的帮派势力,非以此万人之力不足以清除,而以乡里社会而言,则非通过有威望的乡绅,不能有效组织如此强大力量,以解决地方政府所不能解决的治理问题。
当我从安丰地方志资料中发现上述事例时,我觉得叙述安丰的方式,与其他地区应该有所区别。就地理形势而言,需要从安丰周边地区展开观察,才能够理解安丰实际所处政治经济位置。
按照近代历史上的区域划治,安丰镇统领东北38乡,但这说不上有多大的行政意义。事实上,尚处“乡里空间”的时代,安丰作为兴化东部重要集镇,其地方政治的重要性,覆盖了包括邻区“远东乡”的许多村乡。上述“老圩局”及来自三圩各图、庄乡绅们的经济政治活动均以安丰镇为平台,从而体现出该镇的区域中心地位。正是出于这种历史成因,在我看来要观察完整的“安丰镇”,不可不超出现行的乡镇区划,把安丰东北各圩区纳入整体的乡里/区域空间中。
我在第一次去安丰时,因特殊原因已先去过安丰镇东南角位于旧永丰圩南端东塘港河边的戚家舍,而第三次去安丰,又先后分两天去了东北的老圩、新垛、大营。关于戚家舍后面再叙,却说老圩、新垛、大营。这几个乡镇至少在1949年至1994年,在行政上甚至仍旧沿袭了“老圩局”时期的旧称叫老圩区。老圩现为乡建制,乡政府设在肖家舍,一个千把人口的村庄。肖家舍大体保留了最近三十年的风貌,庄北有一座老式瓦房,是1943年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办公地,为该村唯一的“文物”。庄中间最新的建筑为中国移动通信销售点。老圩当年为兴化东北粮区的基础,是因为它在最早成功通过修筑围田堤坝,改造了受水害与卤害的土地。老圩与后来的中圩、下圩,地形上极像三扇打开的屏风,形成了对安丰镇的水利保护和粮食后园。由老圩往东,为现在的新垛镇。新垛是从大营与老圩分出来的新地区。为什么划分新垛,理由不详。《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家乡施家桥,就在新垛镇。施家桥周边水势复杂,依稀可见海沟河下游一带西水下泄与海潮倒灌留下的地貌痕迹。大营位置在兴化最东北角,其区域为明清屯兵处,驻军可能兼有保护盐场与屯田垦荒之任。大营有一些村庄以“营”、“屯”为名,如东营、陈营、屯南、屯北、屯军等自然村庄。大营地形中有一条“官道”尤为特殊,它叫张官路,是在河道中间堆筑起来的一条长达十多里的大路,由串场河东的刘庄,直通大营张庄。当年筑路的动因不太清楚,民间认为是张庄出身的官员,退休回乡后专修,为了与官府来往方便,仅此亦能折射当年乡绅势力在地方上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我觉得还是水利设施上的需要。由“圩”成“路”反映的是水利上的变迁。
尽管上述三乡镇尤其大营乡部分村庄在政区所属略有变化,但我的观察中,在安丰以东沿海沟河北岸排列的这三个乡镇,与安丰镇构成了一个以海沟河下游为地理域度的“乡里空间”。这个区域/乡里空间,不仅存在和结构了历史上该区域乡里社会形态,实际上在今天仍然适宜采用同样的眼光来加以描述。以地形而言,“圩”不仅仅代表这一区域典型的水利特点,而且更突出了该区域土地与农业的治理与社会发展的乡里联动关系。这是为什么对安丰的描述,我会首先注意它的“乡治”或“地方自治”历史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乡治”在该区域主要通过“圩董”的作用而达成,反映出与其他地区乡绅阶级领导“乡治”的不同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圩董”的力量,以其特有“水利”强势身份,实际上维系着该区域的社会生产关系,他们在组织农业社会的同时,也保护着农业社会诸如粮食的安全。这使安丰作为区域/乡里空间越发得到彰显。19世纪末的一则记录,可以用来作为补充说明。当时连接海沟河与白涂河的纵向水道东塘港河,穿过安丰南万乡、戚家乡一带,两岸农田因河道淤积,水旱频发。晚清政府财政严重短缺,官方无力加以治理,只能靠地方组织财力疏浚。于是,由安丰两位董事万清选与翁绂牵头,发动乡民“义浚”,经过1890年整个冬天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对此河流的全部整治。万、翁二人分别获得政府发给的奖牌“谊笃梓乡”。这个例子不仅重申了“乡里”社会道义关系及运作的可能性,而且它也通过其“自治”活动,有效地塑造了这个空间的社会特质。
也因此,当我现在涉笔安丰镇时,对于有关“乡治”资料叙述,并非要作专题研究(实际上,安丰地方“乡治”在清末民初这个时间段里,故事很多,恰恰应合了那个时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总体政治趋势;而且安丰一直到四十年代,乡里社会还保留了一种叫“乡老”的古老称呼,乡老的工作主要为调解地方矛盾,由此可知“乡治”在该地区的传统),而是依据历史现场,重构安丰的区城/乡里空间。与一般“乡里空间”的地缘性和亲缘性不同,我要重构的安丰这个区域/乡里空间,是以地形为依据展开的,也就是说,当安丰以东沿海沟河南北两线各处圩堤的修筑形成了至少五个方整的粮区,这个区域/乡里空间呈现了它特殊的经济社会力量。就我的叙述而言,其有利之处,不但能够在地理上描述它的位置,而且主要还可以通过时间性的描述发现其社会结构价值。而重构安车区域空间,在今天的乡镇政治经济发展情势下,也许能够为我们对于该区域现状以及未来走向的观察,提供一种历史方法。
回顾有关中国小城镇的叙事,我想安丰镇在这个区域/乡里空间中,是可以作为小城镇的典型案例的。我不太清楚,费孝通先生十多年前来兴化考察时是否留意过安丰镇,如果说小城镇在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更大潜力,是费孝通持之以恒的见解,那么安丰镇应该是一个首选目标。
与长江下游南部发达的小城镇相比,安丰镇不仅具备与之相似的基础,甚至还有超出之处。14世纪末明王朝在安丰初设巡检司时,虽说出于政府特殊的经济要求,但亦能看出这一管理性的设置,对当年这个叫安仁乡的地方日后影响肯定不小。中国传统的权力构架,基本上只达到县级,安丰设巡检司,自然是特殊需要。与兴化县级七品官员相比,安丰巡检为九品小吏,但有独立管辖权。巡检司所管盐场,为政府重要财政收入,虽与地方经济有着分别,但司衙所在地为当地私盐贸易之集散地,则有效地扩展了地方市场。安丰逐渐形成入口繁盛的市镇,与此当有一定关系。二十世纪初,安丰曾被设为“市”,这一年是宣统二年,在国家制度“维新”末期,虽说带有模仿西方的意思,但也说明安丰这时候社会经济的规模。
2010年安丰镇党委书记常传林在七月的一次全镇干部会议上,提出“建设安丰美好小城市”,虽说是在目前城市化刺激下的一种官方表达,但其中未必没有安丰历史基础提供的信心。赵振云为安丰地方志的主要编撰人,在当地颇有声望,称呼他赵三Bai(这是本地对伯父、叔父的方言称呼)。我想邀请他座谈,他因身体不适未能前来。赵振云对安丰作为市镇近代以来的商贸史了解得非常详细,由他收集整理的资料,不单单可作安丰地方知识,而且对规划和建设中的“小城市”安丰也是一种历史支持。
赵振云的记录主要为1930年前后安丰镇的商业活动及其组织。这份内容翔实的《民初安丰商业》中,共叙述了安丰镇五大工商业类型,其中“行商”最能反映当日安丰镇作为区域性“集市”的商业规模。如前所说,安丰镇既为兴化东北堤区农业产品集中地,所以粮食贸易是安丰镇的商业支柱。安丰近百家行商中,粮行占到近一半,可见粮贸执地方经济社会之牛耳。当时粮行称为“陆陈行”,“陆陈”即指稻谷、大小麦、大小豆、芝麻等等可以长久贮存的粮食。农业经济社会,粮食不仅是消费品,而且还是用来保证生活持续下去,保证社会安定的必需品。理想上“物丰民安”,要的就是粮食这个“物”。“陆陈行”的兴盛,不在于它们的市场额度和商业利润,而在于通过粮贸,体现了安丰这一区域/乡里空间的社会实力。农业经济在像安丰这样的区域空间里,其活跃程度既依据粮食产量,又依据粮食的贮运流通量,所以前述乡里社会“治水”的成效,以及粮食流通的安全畅达,最后都集中到本地“陆陈行”的粮食贸易的繁荣上面,而后者则成为安丰区域经济的晴雨表。
再回到《民初安丰商业》的资料中。1930年代的安丰,其“市场”几乎全部围绕农业经济。诸如牛行、猪行、草行、鲜行(青货、蔬菜类)、渔行以及粪行等,由这些行业的经营形成了该镇每月“六集”,进行农产品交易。交易的对象为整个兴化东北乡里的农民。适用于农业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亦通过集市贸易得以流通到农民手中。例如犁木店与铁匠店,制造水犁旱犁、风车(车发)、拂板、榷子、戽掀、翻扒、板锨、大小锹、镰刀、犁耳、篙子等,这些农具均为圩里外农民所需。为农业产品加工的作场或作坊,统计数据称:全镇有磨坊5家,垄坊9家(后发展出碾米厂4家,周边地方则有更多的小型垄坊用于加工稻米),糟坊9家,糠坊4家,油坊2家,染坊6家,坑坊4家,粉坊3家,另有豆腐坊、糖坊等不计。农业产品需要加工而成为日常用品,而这些日常用品为本地自给自足,亦是乡里社会稳定运行的保证。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酒坊。1931年整个兴化地区有酿酒糟坊23家,对比安丰的糟坊数,光镇区就有9家,另外各乡各庄其数亦不低于这个数目,因此最新兴化县志说,糟坊“大多数集于东北乡”,其原因自然与东北乡的粮食生产有关。糟坊原料为稻米,大、小麦以及豌豆等,甚至稻田里的野生稗子,亦可用来酿造上好的白酒,本地人叫“糁子酒”。足够的粮食产量保证了酿酒业的发达,除白酒以外,东北乡糟坊出产的米甜酒19世纪中期在淮扬一带已广有名声,尽管当日销售量没有具体统计数字,然而若非达到一定规模是不会有如此市场影响的。而米甜酒,须要用上好的糯米酿制,这也体现了东北圩区粮食种植的一个特点。圩区内多为“老沤田”,即每年只种植一季稻谷,秋收后就将田地灌水养土,利于来年水稻生长。(前述老圩局为什么9月即解散,从种植特点上说,这时候土地已经不再种植,无所谓水涝干旱,而来年4月则开始种植,就又必须水利管理了)这样的土地所产稻谷,产量不高,但质量上等。兴化地区自14世纪中期水稻品种有44个,至20世纪中期这些品种多有保存。“中秋糯”为著名品种之一,为农民喜种,想必这是酿制米甜酒的需要。中秋以后,新糯上场,糟坊里的米甜酒酒味飘浮在整个东北乡。从一个角度看,安丰的酿酒业,作为地方农贸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满足了日常生活与消费需要;从另一角度,则可看做是粮食流通的一种方式,只是通过手工业的转换。
由粮食贸易产生的市场,自然带动了安丰镇的其他各业。如饮食服务业中的茶馆,镇上共有茶馆六家,进入茶馆的主要为“各行”生意人,茶馆成为行市中最方便、最有成效的集聚地,同时也是解决生意纠纷的合适地点。甚至医药业也作为特殊的社会服务在安丰发展起来,1930年的安丰十数家中医诊所中的东街陈氏诊所,前来就诊号脉的人数最高达一天156人;而此时镇上的药店计有杏春堂、回春堂、同春堂等18家。医药业的发达,为乡里社会安全提供了保障,“物丰民安”当中的“民安”,同样把“物丰”的经济影响力扩展到了生存健康需求的层面。
地方志的叙述不可避免遮蔽了乡里社会的另一面,相信1930年代的安丰,亦非尽如历史所记录的这样,民生艰难对于当时的乡里社会是一个普遍性的状况,无论从自然经济格局相对封闭带来的不利,还是从国家政治治理、时代造成的社会动荡等方面看,乡里社会都还远非一个理想的社会。然而,我这里复述安丰地方志史录,重点在于指出安丰这一乡里/区域空间,通过粮食经济所塑造的社会基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或者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段里,具有模态性的意义。安丰镇在20世纪初期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市镇内发力量,仍然可能通过自然经济的能动性,建构乡里/区域空间经济主体。中国乡里社会的存在及发展自有它的途径和方法。这样来看待问题,我们就不会陷入所谓“历史美化”的叙述困扰当中。而且,正如我以前所引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乡土社会各地殊异,安丰虽非特例,但以兴化各乡各镇之历史悠久的积累,在1930年代本地区相对稳定环境中,有足够的结构力量,按照其自然发展方向,促成乡里社会繁荣面貌。
1940年代的10年期间,由于战争原因安丰作为农业经济社会遭到全面破坏。日本侵略者占领的1941到1943年,安丰集市贸易彻底关闭,军事封锁和公开的粮食等资源抢夺,再加上侵略军的横征暴敛及敲诈勒索,不到三年时间,肆意破坏之下,甚至安丰镇那些商业性建筑和名宦大宅都成了瓦砾。不仅安丰镇各业萧条败坏,同时也切断了周边各圩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而出于战争的直接需要,各圩区圩堤被挖断,地形的改变严重影响了农业种植,水旱侵袭,过去的水利保护组织如老圩局,亦无组织农民的可能(1941年春天,成立一百多年的老圩局被拆除)。由于土地失去安全保障导致的粮食歉收,使安丰经济遭受17世纪以来最深的重创。1943年安丰先期从侵略者手里夺回,但随后国共之间在本地区展开的军事斗争,亦无法使安丰经济在战后得到恢复,只有等新政权成立了。
1949年后(安丰为兴化“老解放区”,这个时间可能会稍早一些),安丰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越过其历史规定性而另有变更。新政权既提供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无论农业合作化还是人民公社的出现,事实上也未从根本上打破乡里/区域空间原有结构。但从这一时期,到1980年代末,以粮食经济为基体的农贸安丰,一方面生产条件充分良好,另一方面却因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路径的改变而离开了“传统”的自然模态。
首先,治水成为安丰地区主要社会任务。与旧时代相比,新政权利用其政治动员力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主义”协作,按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关于中国的“公”的研究,实质上延续了地方公义之观念,将乡里社会传统“相互扶助”的道德伦理,发挥到了新的集体主义动员之中,起到了传统的“善举”所不能达到的组织效应。有资料记录,几乎每年或隔两三年,冬天会汇集几百上千甚至万人的大、中、小型河工,改善和强化所有各圩的水利功能,圩区内农业生产由此得到充分保证。
其次,种植技术的集体推广,也提升了粮食生产。以乡或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农技站,在改良品种、科学种植等方面,不仅起着引导性作用,同时适应土地集体化和公有化以后的大面积生产。与传统的水稻种植相比,过去的品种通过改良与选择,大部分被淘汰,一些产量高的新品种成为本地区主导性作物;土地改良也成为人民公社时期“科学种田”首要方法,从前的“老沤田”几乎全部“沤改旱”,一茬水稻后,接着再种植大、小麦,土地利用成倍提高。过去极少种植的棉花,在土地改良后,也进入本地种植序列中,成为国家购销的重要农业经济作物。棉花收购站与粮站是人民公社并列的两个重要经济机构。其他如人民公社后期的农业机械化,部分替代了劳动力,增强了粮食生产的效能。
第三,生产制度化将农民组织在一个固定单位,先是互助组与合作社,后来为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这一方面仍然保持和利用了乡里空间的原有连接,例如亲缘与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则又重组了乡里社会权力架构,使这些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归置和服从政权安排。这就把传统乡里/区域空间政治功能中的自治部分化约到了“社会主义”统一性的公正平等之中。过去村庄、个体农民之间的“利己”主义引起的矛盾冲突,诸如争水、开坝等相关“公事”,无须通过“调解”而自行解决,由此大大增强了生产力,减少了粮食生产成本。
然而,如同所有中国那一时期农业经济产生的结果一样,安丰区域内的粮食生产,却未能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大推进作用。以安丰镇来看,过去那种由粮食贸易带来的社会景观,再也未能出现,其原因显然与粮食生产在此期间由于制度和政策限定,失去流通性,从而退出自由贸易有关。人民公社制度,作为独立核算单位,将原先富有流通性的乡里社会,区划成相互隔离的经济单元,计划经济则从更高的制度要求上,用分配形式在人民公社内处理各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关键的则是,随着1954年“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推进,国家范围内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1955年1月,兴化地区的全面“统购统销”,终结了像安丰这样的乡镇传统粮食自由市场,从而扼制了乡里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主渠道。当粮食只是国家征缴的计划生产品,而不再是商品时,至少在农村乡镇,粮食的生产意义就只剩下单纯的食品价值了。后来农民一直称为“口粮”,就是说明。即使到1970年代,“以粮为纲”将粮食需求提高到最重要的“国民经济”,却也不能改变粮食生产与乡镇经济社会的脱节。最近有人认为,1950年代后造成农村经济贫穷的原因主要在于粮食统购统销,虽然还不能说全部如此,但至少统购统销使乡里社会剥夺了粮食流通,从而失去了自然经济的内发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粮食是传统乡里社会的经济血脉,一旦这条血脉被堵塞,那么乡里社会就失去了生气和活力,仅此可以想见安丰镇1950年代以后,是不可能复原当年的曾经繁荣的经济基体了。而那些围绕粮食市场而展开的乡里社会的工商业,亦因无关于粮食市场的基本需要,不得不改头换面,被纳入一种配给性的计划经济之中。
那么1950年代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前后,安丰镇通过什么维持它在本地区的重要性呢?除了行政设置外,如从1956年3月起它一直是统辖数个人民公社的“老圩区”政府所在地,安丰镇实际上是通过“脱乡”方式,来突显它在原乡里/区域空间的地位。我说的“脱乡”方式,是指在人口设置上,将安丰镇置于“全民所有制”中,即人口全部城镇化。这个任务完成于1960年代中,安丰镇郊三个蔬菜生产大队的农民,全部转为城镇人口。而在这种利用1950年代后设计的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脱乡”化的同时,安丰为了适应其社会变化需要,则又另谋经济出路,走上了工业发展之路。从1958年开办社办工业安丰机械农具厂开始,1970年到1980年代,为安丰“工业化”最显著的十年,几座本地区的“大型”国营工厂都兴建于这个时期。通过不断壮大的“国营企业”,安丰镇从原来的经济社会传统中悬浮起来,从而形成了不是城市却又是城市的工业化经济,在周边地区农业经济越来越困顿、越来越贫穷的对照下,显示出乡镇“工业社会”的强劲。
1994年编纂的《兴化市志》,对作为兴化地区“国营企业”重镇的安丰,有比较详实的记述。
安丰镇从1970年到1990年二十年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人口的增加,使安丰镇终于走完了“脱乡化”的最后路程。1980年代前后,安丰镇的显耀之处,实非它的经济能力,而是它的工业人口指数,每年在全县范围内的“全民制”招工,累计达到4千多人的国营工人,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只在本区域,甚至在全兴化地区,安丰镇都成为令人羡慕的地方。然而,这样的工业经济也许可以用来指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乡镇二十世纪中期的实践,却不能内化为乡镇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上面那些固定资产、利税、利润等,固然谈不上有多雄厚,且都与乡镇经济社会的建构无关。易言之,安丰镇既被“工业化”,它便不可能与传统的乡里社会经济重建联系,而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复又通过这种“被工业化”所强制而致“被城市化”,则又与现代经济无从接轨,最后结果只能长期处在静态的经济停滞中。
5月19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经兴盐公路,一直向东北乡。在海沟河下游,车转向以前圩堤改扩的乡村公路穿行,河岸两边有大小不等的麦地。今年春天天气偏冷,小麦灌浆晚了一些时间,这时候,麦穗青芒上才带一点微黄。一路上,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东西,这个季节里,油菜已经歇花,除了麦田而外,能够吸引目光的不多。但有点奇怪的是,麦地周边及低空,无数白色飞蛾随风起落,有时密集得像大片雪花。凭我以前的农业知识,我知道“麦秀”半个月是粘虫的活跃期。这些飞蛾肯定是粘虫成熟后蜕生出来的。1970年代中期,兴化地区曾因大面积爆发粘虫,每亩麦地最多高达10万只成虫,可怕地吞噬着即将成熟的庄稼,当年三麦损失超过15万公斤。那么,这么多粘虫飞蛾出现,是否意味着今年遇上了虫灾?在大量使用农药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再有如此多的粘虫,那么是停止使用农药了,还是粘虫又增强了抗药性以致农药失效?不得而知。本地现在很少能看到关于农田病虫害的测报,因为土地种植和粮食生产,好像早已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们只要知道每年粮食丰收的消息就足够了。
但眼前的虫情,让我将一年多来在乡镇观察中对于粮食与土地的关心,重新调集起来,联想到我看到的普遍存在的粮食种植问题,让我又再一次为乡村与土地的关系深感疑虑。去年秋天,参加一个村庄的村民选举,在等待收集票箱(要从各自然村将投好票的票箱攒汇到村委会)的空当里,到这个村周边走了一圈。当时正逢中季粳稻上场,那些已经脱粒过的稻谷,随便摊布在公路上晒干。且不说这种在农村十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晒谷方式,使粮食在经过农药后再受沥青二度污染,单是稻子的成色,就让人对粮食生产起了疑问,那些谷粒细小,浆汁饱满度只有六七成,外皮暗黄的稻子,真是今天农民们种出来的吗?但农民对此非常坦然,他们甚至满意地说,产量很高的,每亩一千好几百斤昵。农民又介绍水稻的种植方法:现在不需耕作,不需插秧,麦子收割后,浅翻一下,连麦秸根都不清除,上水后,密下种,然后大量撒化肥催长,又是高产的种子,也不愁收不到粮食。问为什么?农民简要回答省工啊。他们补充说,土地出不了几个钱,花费太多劳动力不合算,省下劳力去城里和工厂打工。事实上,我所走过的村庄,现在种地的大都为老弱病残,很难看到守着土地的青壮年农民了。粮食好坏只是一个表层现象,怎么样种地,为什么种地,深层地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疏离态度。自从粮食统购统销的五十年瓦解了农民、乡村与土地的感情与生存联系后,重建农民与土地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在土地承包制之初或曾萌生,却又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而昙花一现。在获得了土地种植权后,土地的价值却在新经济背景之下异化了与农民的关系。以粮食种植为观察点,你可以看到“后农业”时期,土地的“失能”及在乡镇社会经济中的位移。我的一位师范同学,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本市农业生产,作为本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他到处争取农业发展基金,用于本市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虽说也有一定成效,然而今天“农业”何为?可能我这位当市长的同学最后的努力还是无功而返吧。这里面当然纠缠了很多因素,我自然也未易说清,但有一点我很明确,当“土地”已经“变性”,连所谓“红线”云云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是我对安丰观察中的一个插叙,但也可以当做我对安丰乡里/区域经济社会历史连续性叙事的过渡。在我后面的叙述里,“土地”会作为我对最近二十年来安丰经济社会转型分析的主要着眼点。
戚家舍离安丰镇不到两公里,这个不大的村庄,现在叫戚舍村,以前属安丰镇,后来划归永丰镇。可能由于建在安丰镇北坝头的戚家祠堂,与戚家舍有着宗姓血缘联系,戚家舍人自视安丰镇与他们一体。我七十五岁的母亲和远在外乡的二姨母,一直都讲自已是安丰人。这就是说,我的外祖父作为戚家舍的地主,从前作为安丰地区的乡绅,也是这个乡里社会中风光的一分子。外祖父的糟坊,从我听母亲以及舅族亲戚的介绍,可能是东北乡最大和最兴旺的制酒业之一。他由于拥有永丰圩里一大片土地以及长时期粮食经营而成为本乡首富,因此有财力为戚家本族弟子们兴办了一座义学,延请乡镇名儒坐馆教导。然后,在1946年的战乱中,外祖父病故,同时家产破落。我第一次去安丰,就先到戚家舍,目的是想看看这里的村庄和土地。我出生后,从未去过戚家舍,不知道我外祖父生活的这个地方到底如何,也不知他的糟坊出产的白酒和米甜酒,怎样从这里、从东塘港河出发经海沟河水道,运往淮东城镇那些市场。但去戚家舍,在村村通公路的今天,却意外困难,一路上到处都是养殖螃蟹的水塘,将原先平展的土地分割为数量众多的水面,公路绕过这些水面花了几倍于直行的时间,而我在戚家舍所见除了一些老人之外,就是太多的空屋,和壅塞的河沟。种植庄稼的土地,收缩蜷紧在那些高高的人工水面之下,我外祖父时代的一位后辈,如今九十多岁的老人王大贵,在村外指着那些刚刚收割过的剩余土地,说当年他就在这儿为外祖父看护粮食。现在,我看到的是几块不大的稻田里由小型收割机割下的稻谷,随便散铺在地里,与那些精心装置了养护栏网的庞大的螃蟹养殖水塘比起来,显得多么不重要。对此,老农民王大贵没有其他说法,他说能不能让镇里把这里的道路修好一点,方便我这样的老年人行脚?
戚家舍所见,并非没有收获。这里的土地形势产生的观感,使我在感情上不能满足之外,却对安丰地区乡镇经济取径另有了一种直观的现实的认知。也就是说,当我已经注意到乡镇经济,在经历了1990年代后短期内的农业恢复以后,迅速面临着全面的经济发展主义急切要求下的选择,尤其像兴化各乡镇,属于后发展地区,农业成为经济贫弱的代名词,更是受经济发展主义的逼迫和驱使,而把选择的希望投放到现代资本运作上,即所谓的“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展开,无论其名目怎样繁多,其经济作用以及对未来的影响,都无法回避土地资源问题。随着资本对乡镇的进入,首先改变的就是“土地”性质,即“土地”成为资本对象后其农业性能的转变与丧失。最近十年,安丰镇(包括邻近的永丰镇)“招商引资”的经济效能,似乎不像别的乡镇那样完全集中在工业产业上,而是突出反映为养殖业的兴起。至少我从安丰镇提供的有关材料中,能够发现安丰镇的经济目标,其中有一个重点是放在通过新兴的养殖业,重建其农贸型社会经济,包括它的“小城市”理想。当然,安丰镇并未放弃工业兴镇的思路,对“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仍然是他们“坚定不移”的发展理念。但引起我更多注意的,则是安丰镇农贸经济在最近十年中的新崛起。也许因为安丰镇有着本地区深厚的农贸经济传统支持,更容易从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开发新的特色经济类型,以此与其他乡镇的经济发展模式区别开来,例如兴化戴南镇以不锈钢产业形成的绝对工业经济。与从传统的粮食产业自然生长起来的农贸经济不同,养殖业在今天有着现代消费市场的指定性需求,其短时间内能够迅速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成为安丰镇推进农贸经济的首选。安丰镇能否用此农贸经济,另辟蹊径,发展出一个既能与传统接轨,又能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有独特乡镇经济社会内涵的新安丰,虽难设定,却是我的兴趣所在,甚至是我专门只选取农贸经济来作为观察视点,而不顾“片面化”的原因。因此,这次所行所见,昔日种植的土地大多改变为养殖的土地,农田日渐被“水田”替代和淹没的情景,对我的触动自然不小。
从1999年开始,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安丰镇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确定养殖业为本地区经济重要发展取向。这一年安丰有三万亩土地被用来进行淡水养殖,养殖的产品主要为河蟹。说起来,河蟹养殖在兴化地区并不陌生,东北乡亦为水网地带,1950年代后即有专业水产大队从事捕捞和养殖,其中河蟹也在1980年代后逐渐成为养殖品种之一,只是数量偏少。1990年代中期后,南方城市及港台地区螃蟹消费市场需求量急速增长,促使养殖业向河蟹养殖集聚,安丰兴起河蟹养殖应是受此市场需要的影响。然而,就乡镇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安丰在“农业结构”的调整上,将推进本地区农贸经济的重心放到河蟹养殖业上,与其说是建立在市场的吸引力上,不如说是追求规模型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要达成地区规模型经济目标,资本的投入与吸纳,就不能不成为主要手段。所以,2004年通过地方政府主导下成功的“招商引资”,成立了本地区最大的“红膏蟹”养殖基地和集团公司,这才是安丰地区实现“农业结构”调整,进入新农贸经济的真正起点。
让我先做一点关于河蟹养殖方法的说明。与十年前本地农民零散的养殖方法不同,目前大规模的螃蟹养殖,采用“人造湖泊仿野生稀养”,专业性的简称又叫“提水养殖”,主要方法是“框堤,提水,种草,投螺,稀放”。具体地说,通过围堤,将原先土地填高,提升积水高度,从而便于养殖中的水质水量的控制,同时将池塘面积扩大连片,大的可达到2000亩以上,形成“湖泊”式的水面,并且用种草方式将农耕性土壤土质改造成具有“湖泊”特点的沙泥土质,以提高河蟹的养殖质量。
从养殖方法上,我们看到这些不只属于养殖技术问题,而且主要涉及到土地资源的集合和使用。承包制以来,农民掌握的土地是分散性的,规模化的现代养殖业,需要将各家各户土地“流转”过来,才能聚集为如此大型的“人造湖泊”。因此,租用并改造、合并土地,有效地整合农民、村庄各种利益关系,靠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多靠投资式的资本运作才会实现。红膏蟹公司以其巨大投资,一进入安丰,便迅速建成一万亩土地的养殖基地,成为本地区养殖业的龙头老大,显然是资本运作的成果。
规模化的河蟹养殖产业,其经济发展能力又需要通过规模化的市场经营来显现。为此,安丰地方政府同时还须借助于充分的资本,在“产销一体化”,“营销体系化”,以及如何建立完整的“河蟹产业链”,等等方面“做大做强”。在安丰镇,现在最引人注目、也最繁盛的商业区,是“河蟹销售一条街”。据介绍,每年秋天螃蟹交易季节,这里人头攒集,车流如潮,连日继夜,为安丰贸易史上所仅见。这还不够,政府打算在今年吸附和利用新的投资,兴建设施完备现代化的河蟹销售市场,统领整个地区的产业。对此,这届镇政府表示,他们将以坚定的“务实态度”,和“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做好这件“服务”于本镇经济发展的工作。我相信,对安丰镇政府来说,河蟹市场项目的建成,正是他们“狠抓有效投入”以实现经济“集约发展”的有效体现。
就以上两点而言,安丰通过资本运作所建立起的养殖业,是否能够连接其农贸经济传统,重建一个完整的现代农贸经济,我不能凭此断言;而且是否可以通过养殖业在安丰兴起,来证明这样一种农贸型经济可以达成未来乡镇稳定持续的发展,更非我有能力所预期。但我要说明的是,今天乡镇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混合式经济”,在越来越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之下,哪种经济方式能够迅速带来地方产值和财政增长,就会使用哪种方式,因此,当安丰镇不仅把养殖业作为一种地区特色经济,而是借此致力于对农贸型经济的重塑时,让我看到了乡镇经济在面对发展主义要求和竞争性情势下,可以采取的合理路径和适用模式,同时也有了对这一路径和模式的优势以及隐含的困境进一步分析的依据。
安丰镇主管农业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告诉我,2010年河蟹养殖量,全镇已达5至6万亩,也就是说,有着十万亩土地的安丰,养殖面积占56%。5月19日下午,在有三个村支书参加的座谈会上,我听到这个数字后,并没有多少惊讶(我还得知,在土地总面积比安丰小的永丰镇,河蟹养殖量达到8万亩,几乎是永丰镇的全部土地了)。但我还是问副书记,那么你们是否进一步鼓励和扩大河蟹养殖业,或者随着养殖与粮食种植面积比例越来越大,你们将怎样在两者之间平衡?副书记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已有犹疑,她说,农民们会用更高的价格租出土地,也会因更高的价格更多地租出土地,农业面临的矛盾更多也更难。这些问题,也许提出来还不是时候,而且也没有更多时间深入讨论。
然而,安丰观察后,我一直将思路固定在“农贸型经济”与土地资源上面,一份来自上级政府部门关于河蟹养殖的调研报告,可能加强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这份以正面肯定河蟹养殖具有“高效农业”经济价值的报告,其中也指出了河蟹市场不稳定性及其风险,河蟹市场其容量是有限度的,一定的时候就会饱和,供大于求随时会发生,而且其消费无论怎样庞大,但都是“即时性”的,一个很小的因素,例如食品安全都会带来市场的锐减,甚至毁灭。这样看来,确实如该报告所言,河蟹养殖业“固有的劣势”在“可持续发展”上面暴露无遗。因此,建立在这一养殖业基础上的农贸经济,其脆弱性亦可想而知,如果拿传统的粮食经济来比较,则养殖业市场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农贸经济,实难稳固持久。
由此,我有更深一层的思虑。我认为,市场产生的危险,其实不只是毁败了一个产业和一种特色经济或一种经济模式,而是直接威胁到土地资源。当河蟹养殖业有一天丧失了市场,不再具有经济发展价值,那么大量用于养殖的土地,能够退养还耕,恢复种植功能吗?询问有关农业与土壤专家,回答说经过改造为“人造湖泊”的土地,是不能复耕的,至少在短时期内不能复耕用于种植。那么,以安丰镇来说,照最保守的估计,就会有五万亩良田一段时间里废了。我不知道将来很有可能出现的这一后果,对一个乡镇是不是一场沉重的土地灾难?
无论现在乡镇经济中还有多少可知的和不可知的问题,也无论这些问题的预后有多么严重,但现实中所有这些与乡镇发展相关的选择,几乎都不可逆转。不用说,“发展主义”已经左右了乡镇的各种经济要求,扼住了乡镇通向未来的方向和道路,今天的乡镇之所以冒着包括环境破坏、资源丧失等等在内的种种危险,也要“敢想敢干”地把经济发展推进到最快速度,正是“发展主义”所致。然而,或许我的态度应该尽量撇开这种“发展主义”的纠缠,来理解安丰的乡镇发展观。我在查看安丰镇近年来多种政府文件时,发现他们在表述其社会建设目标时,用了一个核心短语:富民强镇。并且,安丰镇政府朴素而坚强地将这个短语解释为“最大的政绩”。这不仅无可指责,而且的确让我看到了一个务实的乡镇政府奉行的政治责任和信心。与安丰镇在上个世纪初“物丰民安”的历史表述相比,安丰镇政府有关“富民强镇”的目标设置,更突出地反映了现代经济观点,以及隐含其中的政治观点。两者的分别在于,“物丰民安”是将乡镇的物质(经济)繁荣,归之于“民”所构成的乡里社会的稳定,而“富民强镇”,则在于通过经济积聚,达到乡镇的强大,以保证一种竞争性的能量。由此我隐约感到,今天乡镇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回到传统中去了,新的安丰也将是一个富有竞争性的“城市空间”中的安丰,它的强大力量随时都在粉碎乡里社会的理想。
责任编辑: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