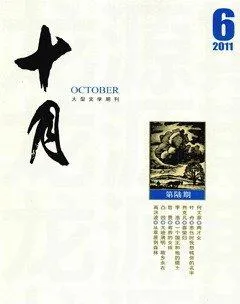扣子棋和山影拳
一
每当我走进这条繁华的大街,过三个路口,通常我会向右拐,拐进胡同,再走不远就是小姑家了。如今这儿不通了。在胡同的原处,立起一座规模不小的商厦。
虽然,我只能直行,随着过往的人流,在一幢幢建筑物以及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上走着。我时常就这样走进了记忆,并试图穿越商场下面那家派头十足的名牌鞋店,走进小姑家的那个院子。这是北京一个普通的院子,它有两扇老式的木门,青石板的走道,花坛和缀满了果实的枣树。这个温馨的小院儿,它就像小姑家院墙上的雪豆藤,爬满了我童年的记忆。
那一年,还没放暑假,姥姥就开始叮嘱我,去了北京要懂规矩。她一边给我试穿一双刚做好的新鞋,一边说:“过马路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答应着,眼睛却只顾低头看着姥姥给我做的新鞋。
那是个久远的夏天。街道旁槐树的叶子油绿绿的,茂密的树冠里传来了阵阵蝉鸣。姥姥一手领着我,一手攥着一张记着小姑家地址的旧日历,在胡同里东张西望地查对着门牌号。云儿胡同是胡同里的胡同,它拐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弯儿,姥姥费了很大工夫才找着它。她望着门檐上蓝底白字的门牌,高兴地叹了一口气,伸出了她那只戴着铜顶针的手,厚厚的门板便发出了木鱼似的响声。我从门缝往里瞧,从走道的尽头走来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白净的皮肤,黑亮的短发,穿着—件浅蓝色的翻领短衫,带着江浙口音:“谁呀?”
“是我们呢!”姥姥大声地应着。
小姑开了门。后面跟着一个孩子,这就是姥姥常提到的辛胜,年龄和我差不多,留个小平头,黑瘦,有点像画报上的印度孩子。辛胜不爱说话,见了我话倒不少。他把我带到邻居们家,告诉他们我是他的表弟。
“你还有表弟?我怎么不知道。”他们这样问他。他含糊地答一句,马上跑了。他又打开花坛边上的水龙头,让水流出来一下,问我农村有没有水龙头,我说农村有水井。他又把我带到白大爷家去看金鱼,另一个玻璃瓶子里有几只小白虾,白大爷说是少先队的孩子们捞了送给他的。我羡慕地凑近玻璃瓶,问小白虾是在哪儿捞的。我一问,他们都笑了,说我的方言重,还学着我发山东黄县地区的“姥姥”音。“俺说的有啥不对?”我一问,他们又笑了。不过,邻居们都很友善,晚饭的时候,白大爷还过来问姑姑家里住不住得下,说可以去他家住。他长得比较胖,胡子很重,眼泡有点水肿,喜欢摇着把蒲扇坐在桌子边上喝茶,或透过珠帘子望着外面的院子,一望就是老半天。
我喜欢从傍晚直到天黑之后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邻居们会搬出板凳坐在院子里聊天。各家的窗户都张开着,露着一个个神秘的黑洞。我和辛胜还有邻居的孩子在院子里东跑西串,弄得满身是汗。直到大匣子他爸开始唱京戏,我们才停下来。他表情很滑稽,哼哼嗓子就把大家逗乐了,但他一开腔,立马鸦雀无声。丁香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蛐蛐儿在院墙下面发出悦耳的鸣响,雪豆的叶蔓像剪纸映在满是月光的山墙上,这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大人聊天和扇扇子的声音。直到很晚大家才迟迟散去。
回到屋里,我仍然不能入睡。我睡的是里屋的一张上铺,这里十分狭窄,闷热的空气中散发着潮霉的气味。挨着下铺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盏日光灯,微弱的光线使周围陷在黑暗里。我摸索着爬上Tq4BzjOpOrcO9xek3RGntA==了这块离天花板很近的床板,躺在床上,我不是在睡觉,而是在胡思乱想:天安门离这儿好近啊……要是老能睡在这张床上该多好啊。我沉浸在一种幻想和忧伤的情感中。这样,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我要上厕所,床板便开始吱吱作响。去厕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通过姥姥睡的下铺,然后拉开两屋之间的门,经由外屋小姑一家三口睡着的大床,开门到院子里。然后,轻轻打开院门上的木栓——这时我通常会换一口气,并顺着月光下空荡荡的胡同急速地向西奔跑,经过菜站,再经过自行车存车处,就能闻到厕所的位置了。厕所里没有灯。我还会在黑暗里和一个不认识的黑影聊天。有一次,黑影说:“来点纸。”我赶紧撕下一小块《人民日报》递过去。黑影接了报纸不说话,只顾擦屁股。等黑影擦完屁股站起身来,提好裤子才说:“谢了。”
清晨,一束阳光从南墙高处一个有栅栏的小窗户投进屋里,也从那里传来了街道上的喧哗声和自行车急促的铃声。在这些声音里,有时会听到一阵悠长的吆喝声,由远而近。而这正是辛胜等待已久的声音。他从外屋闯进来,穿着短裤,慌里慌张地问:“听见了吗?”我把头钻出被窝:“听见什么了?”他不由分说,跪在地上,从床下拖出一个木箱子,里面装满了废品,有用过的瓶瓶罐罐、破布头和挤干的牙膏皮,分门别类。我赶紧跳下床去,当我们迅速把这些废品抬出去时,仍然站在了几个老大妈的后面。收废品的推着一辆平板车,他身穿一件灰旧的有补丁的褂子,面色黑瘦,严肃的表情略带着职业的尊严。他手上把着一杆秤,先称了报纸和布头,再数数牙膏皮,完后清点瓶子。除了牙膏皮,要属铜最贵,红铜又比黄铜贵。这些辛胜都没有。过秤的时候辛胜也像大妈们那样斜着脖子关注着秤杆,称秤的男人为避免对他有瞒秤之嫌,他用粗糙黢黑的手指稳住秤线,请人过目。事后,辛胜挣了一块多钱:有一张五毛的,两张一毛的,其他是五分和二分的。我很羡慕。可他把钱揣进兜里时却表情平淡。后来,我忘了什么时候,在我人生走过的那些坎坷的岁月里,我还真曾萌动过以拾废品为生的念头呢。
小姑家的屋里很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平时我和辛胜总是在街上,在西单商场或在那些散发着水果香味的柜台前闲逛。只有大人不在家时,我们才可能在屋里下围棋。围棋是辛胜教我的。在我来的那天,他就拉开了抽屉,拿出两包扣子,一包黑扣子,一包白扣子。他摊开一张纸糊的棋盘,晃着脑袋说:“金角,银边,草肚皮。”我捏起一个扣子,马上想到我姥姥。她最需要扣子。她常为少一个扣子没法完成一件衣服坐在炕头上发愁。我穿的衣服也常会比别人少一个扣子。所以扣子是珍贵的。我还知道扣子在我姥姥眼里和在别人的眼里不一样。在我姥姥眼里,扣子和珠宝都是一类东西。在她的首饰盒里,除了有一枚订婚戒指和一对耳环,还有几粒样式不同的扣子。但我从没有问过姥姥,为何把那几粒扣子留在那里。难道它们有一天会被凑齐?
然而,眼前的这些扣子并不是姥姥需要的。这些扣子都是些残次品,不是缺眼了,就是豁边了,挑不出好的来。辛胜说,别挑了,不可能的!他抓起装棋子的布袋子掂了掂说:“这种扣子是论斤卖的。一副棋至少得半斤。”后来我发现在这条胡同里很多人家都有这样的扣子,不知是打哪儿弄来的。
我对这种扣子棋很快就入迷了,一没事我们就摊开棋盘拼杀。晚上我们还常把棋盘搬到白大爷屋里去,那真是个下棋的好地方,我们再闹他也不会赶我们,还请我们用他的杯子喝茶。有时直到他老人家进入梦乡,我们才会被他震耳欲聋的鼾声驱离出去。辛胜做事有他的一套。每次下完棋他都会把黑白扣子分出来,装好。甚至还要数上一遍。如果有一个扣子滚到床下面了,他就会爬到床底下去。要是没找到,他会爬出来再去找手电。手电没电,他就会去找电池。有时为了找—个扣子,他一连要去找好几件东西。
有一天,我们闹翻了,就在我和姥姥离开北京前不久的一天。我也没想到,本来我们是准备去天安门的,外面下雨了,我们只好在屋里下棋。事情是由一片草肚皮引起的。事实上,我们在那片草肚皮上已经拼杀了很久,最后我打截成功。但我刚松了口气,桌子就晃动了。结果棋子全乱了。我知道这是辛胜成心的。他的表情也由紧张不安变为幸灾乐祸。“这盘不算。”他咧嘴一笑。我骂他输不起,赖皮相。他学着我发山东黄县的“姥姥”音。我这时一股火,顺手一扑落,扣子落了一地。他先愣了一下,突然向我扑来。我想,你扑过来就扑过来吧。结果,我还是被他给扑倒了。在我倒下去的时候,我想,倒下去就倒下去吧。结果,我倒在窗台边一盆仙人掌上了。我尖叫了一声——我是光着膀子的呀。小姑和姥姥从外屋跑进来,小姑涨红着脸,一把将辛胜拽到外屋。我听小姑在外面训斥他。可我越听越失望。原想小姑会揍他两下的,可她一直在说:“你是主人,人家是客人,主人应该善待客人。人家大老远从山东黄县来北京看咱们……”我心想,你就别再说他了,赶快揍他吧,最好能让我听听他的哭声!小姑最终还是没有下手,我心里很不高兴。小姑说了一阵子,就擎着一瓶红药水进来了。我心想:他这都挨不着打,哪里还有挨打的机会?后来我明白了,并不是小姑舍不得打他儿子,而是小姑根本就不会打人。小姑不知道打人是可以解恨的。
小姑叫我趴在床上,她擎着红药水和姥姥像看地图似的检查了我的伤势。根据她们的对话,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可又说有几根刺在肉里。她们显得无能为力。小姑出去了一趟,找来一个清理猪皮的小镊子,问题才解决了。然后涂了些红药水,而且,红药水也弄多了,凉飕飕地顺着我的后背流下来——一转身,又流进了我的肚脐眼儿。“别动!”姥姥边说边在我背上吹了吹,让药水再挥发挥发。完后我坐在床上,见她们在处理那盆仙人掌。
“这叫山影拳,”小姑说,“多好听的名字呀!”名字是好听,可养什么花不行,要养这种带刺的花呢?小姑说,这是观形的植物,优点是不疯长,形状像山,所以叫山影拳。但我注意到它有一边已经断裂了,流出白色的汁浆。后来小姑用一根布条,费了很大劲才把断裂的部分固定住,又把它摆回到了窗台上。
晚饭前,姑夫打着雨伞去菜市场买了五毛钱肉回来。我觉得这块肉与早晨发生的这件事有关,平常总不会无缘无故吃肉,要买也是两毛钱的,不会是五毛钱的。我趴在床上,望着那块肉,它被小姑用刀切得很薄,薄得像一片片卷起的花瓣。我又想起小姑说的:我们是主人,人家是客人,主人要善待客人。
这件事之后,我和辛胜谁也不理谁了。有时,他见我站在枣树下面抬头向上面观望,他就斜着眼睛把嘴对着花坛边上的水龙头喝个没完;我见他在屋里翻看小人书,我就找个苍蝇拍在窗前打苍蝇。这样,直到我和姥姥要离开北京,我们都在憋着劲儿。
时间很快,姥姥开始准备走的事了。她还买了些北京果脯和一些土特产,然后把东西放进一个有拉链的草绿色的帆布包中。在最后的几天里,拉链开拉的声音,每每预示着离别日子的临近。然而,这一天终于到了。夜里大家难以入眠,我听姥姥一直在外屋和小姑说话,除了离别的话,她们还有很多话题。一会儿农村怎么了,一会儿城市怎么了。说的多是有关粮食、豆油和副食券的供应问题一直到深夜。我躺在高高的床板上,面对着龟裂的天花板,所有的声音都变得模糊而遥远。
辛胜在干吗?外屋静静的,仿佛他已入睡。
早晨,大家送我和姥姥来到北京火车站。辛胜跟在小姑和姑父的后面,他还是一声不响。大匣子也来了。大家在站台上等待离别的一刻。直到火车响起了汽笛声,辛胜突然从窗外塞给我一包东西。没等我细看,火车就移动了,在雄壮的音乐声中,我见他们都张着嘴,向我们伸着胳膊,却听不到什么声音,直到那几只挥动的手臂迅速消失在远方的晨雾里。
火车走远了,我才注意到手上拿着的那包东西,当我打开它时,原来是两包扣子——一包黑的,一包白的。我望着车窗外面飞动的树木和田野,眼泪有节奏地折射出田野的色彩……
就这样,我离开了——带着两包扣子,保留着我对童年的这段记忆。它曾是我最骄傲的往事,因为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每个人都向往着北京,但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正在上初中,农村的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我参加了红卫兵,接着就是大串联,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来到了北京。我和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当我们疲惫地来到这个仰望已久的城市时,发现,北京乱糟糟的,到处飘荡着红旗,建筑物上悬挂着红色的巨幅标语,红卫兵戴着红袖章在街上三五成群,来来往往。人们成天在街上看大字报,看布告。
我去小姑家那天,已近黄昏,胡同显得有些狭窄。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小姑家的院子,小姑家亮着灯,透过玻璃我见小姑和姑父正在家里糊火柴盒。小姑坐在床上,成堆的火柴盒摞在一旁,他们比记忆中的他们老了不少。我没看到辛胜。
我进屋之前先看了看院子。院子看着并不大。其实,我在院子里待了很久。我发现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不在记忆中的位子。没有雪豆紫色的藤蔓。那些开在我记忆中的花坛里的丁香已变成了在干裂泥土上的杂草。院子里冷冷清清。
我意外的到来惊动了他们。他们放下了手里的火柴盒,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小姑为我沏茶,找出一些北京干果堆在我的面前……我问辛胜哪儿去了?他们说辛胜正在工人体育场参加有史以来中国最隆重的批判大会。还说他即便不参加这个大会,也要参加学校里的批判大会。每天最早也得夜里十二点才能回来。
我注意到屋里还是我记忆中的那几件家具。小姑身上仍然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翻领衫。这难道还是原来那一件?我心里想着嘴上却说:“小姑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儿也没老。”
“人怎么会不老呢?”她说话时习惯地看看窗外。这时,窗外已经黑了。月光下,有人在院子里唱京戏,一板一眼的,是《沙家浜》里指导员郭建光的一段唱。我问小姑,这是谁?小姑说是大匣子他爸,改唱样板戏了。我问起了白大爷,她放下了手里的火柴盒,又看了看窗外,说有一天晚上来了一群红卫兵,把白大爷带走了,之后就一直都没回来。她说起这件事,显得很伤感。我只好转了话题。
我边等辛胜边跟小姑和姑父聊着。那天,电报大楼的钟声响到十二下,辛胜还没回来。我见桌子上有些旧报纸,上面写满了毛笔字,字体和毛主席的字体很相似。小姑说是辛胜写的。当时,毛主席的狂草体诗词被他临摹得已近乱真。有一天,我去学校找他,他在汗流浃背地写大字报,完后又用斗笔书写出一条条的巨幅标语,其中,写得最多的是“革命、打倒、团结”这些字。这些字也是那些年我们最常看到听到和用到的。
那天,辛胜回来已经是半夜了。我见到了辛胜,之后又见到了大匣子。在北京期间,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去过一次八达岭,还爬过香山的鬼见愁。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临别前我们还进了照相馆,留下一张合影。那天每人都找来一套绿军装,照相之前我们先读了门口一个黑板上的照相须知。辛胜知道我有爱笑的毛病,就念了两遍照相须知里的第二条:凡是照瞎照笑,均由被照人负责。我站在镜子面前,摄影师拍拍我的肩膀,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好了。可他让我把袖子再挽一圈儿,手里的毛主席语录再抬高一点儿。他摇着头说:你太瘦了,袖子挽一圈儿是远远不够的。我只好把袖子放下来,又重新挽一遍。之后,他边退边举起一个黑色的橡皮球,嘴里喊着:严肃啦——注意!他捏了一下橡皮球。结果照了一张穿军装戴军帽手拿毛主席红语录的合影。这也是当年最流行的照相姿势,这种姿势也被塑成水泥坚硬的塑像,到处可见。照片洗好后,虽然看着没瞎也没笑,但我还是摇了摇头。因为,照片当中的我,由于袖子挽得太高,看着就像是要准备下地干活;而且,由于我的疏忽,风纪扣也忘扣了,露着我那拱起的使人看着心事重重的喉结。我为此闷闷不乐。可这怪谁呢?我告诉小姑,这就是我摇头的原因。但小姑还是把它镶在了镜框里,挂在了墙上。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北京。直到许多年后,我们的青春年华终于和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同过去了。时代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情,姥姥已经过世。许多记忆中的事情变得更加遥远。没想到的是,在经过无数的周折和努力,我也调到了北京,在一家刊物搞摄影工作。
有一天,我带着极大的好奇和对童年的记忆走进了云儿胡同,但眼前的一切都不再是记忆中的了。小姑和姑父已经老了。辛胜和大匣子都已结婚。白大爷没能挺过那段动乱的年代。在我们老去下棋的他住的东屋里,又搬进一户陌生人。而那个恬静的小院儿也早已原貌无存。这里没有枣树,没有花坛,也没有雪豆紫色的藤蔓。院子里每家都加盖出一间小房子,仅留下了一条狭窄的走道。走道两旁堆满了蜂窝煤。头顶上交织着晒衣服的绳子。叫我吃惊的是,小姑家里一切如故。没想到岁月能改变一切,却没能改变小姑家的室内布局。屋里还是那几件家具。不过,里屋成了辛胜结婚的新房。我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从昏暗中传来,我童年睡过的那个上下铺竟然还在那里。墙上依旧挂着那个陈旧的相框,我和辛胜还有大匣子那张早已发黄了的合影依旧镶在里面。
辛胜当了工人。那天他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壮实的身上还带着一股机油味儿。我见他都不敢认了。因为,在他老气横秋的脸上,无论怎样,我都看不到他小时候的影子了,只是声音一点儿没变。看得出,他很高兴。我们十分困难地找着可谈的话题。除了提起小时候,我们能聊几句,沉默的时间太多地间隔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说工厂很远,常常要加班。他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起烟来。我见他那只能写一笔漂亮书法的手上还残留着没洗净的黑油。你还下棋吗?不知怎的我这样问。
他笑了笑,摇摇头,却起身进了里屋,不一会儿,竟然又拿出了两包扣子来。不过,那天辛胜输了。他说当了工人就很少下棋了。听他这样讲,我头一次感到赢得不舒服,从此对围棋也没了瘾。小姑和姑父那天情绪非常好,小姑的脸上因兴奋焕发出红润的光泽。我记忆中从没见过她那样快乐过,或许是多年不见;或许是我们都已长大成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了,除了机关里的事务,我也常去外地出差。后来,我虽然多次去过小姑家,间隔的时间越来越久了,相互联系得也越来越少。甚至,我常常忘记是和小姑一家同住一城了。这样,久而久之,最终还是断了联系。一切都是慢慢被遗忘的,许多事情,似乎也合乎情理。可白天不去做的事,晚上反而会梦到,有几次夜里我梦见了云儿胡同,梦见童年去小姑家的情景。有时,我从梦中醒来,在往事的回忆中失眠了。漫漫长夜里,我盼着天快点亮起来。因为,只要天亮了,就能去小姑家了。何况,小姑家并不远,只要顺着长安街往西走,到了西单再往北,散散步就能到了。可白天和晚上是不一样的,许多夜里感到急迫的事情,到了天亮也就没有那么马上去做不可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些年,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型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包围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从外地来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胡同里越来越拥挤。有些胡同被拆了,很快盖起了大楼。可人还是越来越多,剩下的胡同也都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只是小姑家的那条胡同有些例外,虽然它也在旧城改造的行列中,但迟迟没动。就这样有一天,云儿胡同突然开始拆迁了,可拆到一半就停了。据说,云儿胡同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土地和搬迁费等问题停下来的。谁知道呢?总之,只有云儿胡同拆了一半,剩下了一半,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周边的胡同一条接着一条都拆了。后来,建起了一片楼群。这些新型的建筑物苍然耸立,到了夜晚更加华光璀璨,它们居高临下,仿佛以傲慢的姿态把这孤岛一样的半截胡同围在了中间。每当人们经过这里,都会疑惑不解地转过头来,看看这半截破旧的云儿胡同,它为何还没有被清除掉呢?
小姑一家仍住在那两间小屋里。房子已经多年失修,潮湿,漏雨,油漆脱落,墙上留着需要填补的裂缝。房顶铺着防雨油布,墙头长着野草,野草上落着蜻蜓……即便这样,由于随时都有被拆迁的可能,没有人愿意再花钱装修它了。
就这样,直到有一天,我们搬进了一处新居,这是一套全新的公寓楼,我们在第二十八层。说来也巧,那天我从窗户向外瞭望,竟然看到了云儿胡同和小姑家的那个院子。我十分惊讶,我的妻子和女儿见我望着窗外发呆,不知我怎么了。我告诉她们,我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我见她们好奇的样子,就叫她们再靠近点儿,我指给她们:“你们看吧,那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对了,你不是说要去看看姑姑他们吗?说了都几年了。”我妻子说。
“是呀是呀,该去看看了。”
“那就定个时间吧。”
“五一节怎样?”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我妻子说小姑他们来过了。我感到有些意外。她说那天下午她没有认出他们来,她以为是有人走错门了。姑父手里拎着两盒点心,头发都斑白了,尤其是小姑,白得几乎没有一根黑发了。我妻子所说的小姑,似乎并不真实,仿佛是我记忆里那位年轻的小姑化装而成的。小姑那次来,是要告诉我们搬家的消息。据说,云儿胡同这次是真的要拆了,而且是要通通拆完的。
我妻子说,除了点心,小姑还送来很大的一盆花。小姑说她老了,这盆花他们不能再养了。记忆力不好,有时都忘记给花浇水了。她说我们这儿光线好,可以好好照顾它。
这时我才注意到了,客厅的阳台上多了一盆高大的仙人掌。我走近它,摘下了眼镜:
“山影拳?”我说出声来。
我细细地端详着这棵硕大的植物。只见它峰峦叠翠,就像一座巍巍壮观的山景。然而,在它一处峦脉相连的地方,我看到了一道垂直灰白色的疤痕,仿佛是幽谷间垂流而下的山泉。那不就是我和辛胜为了下棋打架碰伤的地方吗?这盆花竟然能养到今天!这时,我想起了那年——想起了那个有着绿荫蝉鸣的夏天,姥姥带我去小姑家的那个遥远的日子。历历在目的往事,激起了我对小姑家那个小院儿的不尽怀念。虽然时光不能再现,但那段童年往事,只要推开沙发边上的那扇窗户就能看得见了。为什么一天能做的事,却一生都没有去做呢?好吧,现在就让我来做这件事吧!我穿好了衣服,带了早就准备好的礼物。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视线不由得望向窗外——望向了更远的地方,然而,那个地方的景象使我赫然惊呆了;那些波浪般起伏的瓦房不见了,云儿胡同变成了一片废墟。灰雾中有几台推土机正在清理着堆积如山的垃圾。
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辛胜写的。信中告知,小姑一家已经搬离了北京。据说,那是一个离山很近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也听说过。虽然交通没有城里这样方便,但他们对那里的生活感到满意。
后来,在云儿胡同——在那半条胡同的旧址处,一座新型的商业大厦拔地而起。可我老了,每当我走进这条繁华的大街,过三个路口。我还会想着向右拐,因为,拐进胡同再走不远就该是小姑家了。
责任编辑 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