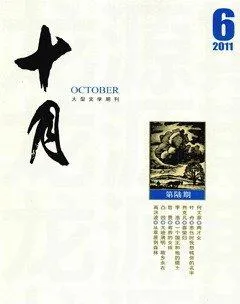—个国王和他的疆土
国王F成为国王完全是个意外,他几乎就是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当国王F得知他将成为新的国王,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他的第一感觉不是兴奋不是惊喜不是满足而是恐惧。这一消息就像一团乌云,里面包含着闪电、冰雹和不可见的魔鬼,他扑到母亲的怀里哭了起来。《稗史搜异》、《聊经》中有一段大致相似的记载:他送出传旨太监的时候裤子是湿的,而母亲的哭声跟在后面,尖锐而沙哑。
他们母子的哭是有道理的。这个,我们暂时不表。
无论如何挣扎,如何拒绝和不甘,国王F都不得不接受他将成为国王的事实;他必须要离开自己的父亲、母亲,独自一个人进入到王宫之中。这于他和他的家人简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生离死别,过不多久,他的父亲,南怀王就将作为国王御使被派去戍边,直到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病死。对此,国王F根本无能为力。至于原因,我们也暂时不表。
进入王宫的国王F还不能算是国王,因为他有太多的事务和礼仪需要学习,何况他还过于年幼,只有九岁,此时的权力主要掌握于几个大臣的手上,他们需要为新国王分忧。好在他们都不坏。他们为国王F请了三个老师,他们分别负责为国王讲授治国方略、宫廷礼仪和艺术。负责讲授治国方略的老师叫姜方亭,他曾担任过之前几个短命国王的老师,因为“讲述不够尽责”和“传授偏见、邪恶”而几次被免,甚至被打断过两次肋骨。他在自己的《轻云集》中这般记述自己第一次与这位新国王的相见:九岁的国王显得憨朴、怯懦,如同受惊的小兔。他迎着自己的老师,低着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姜方亭问他,你读过某某书没?他摇头。再问,你读过某某经没?再次摇头。国王F窘态十足,似乎极为惶恐。姜方亭有些意外:那你读过什么书?难道,南怀王从未找人教过你什么?国王F的脸上有了汗水,也,也读过些书。不过,不过,先生说的那些书,父亲不让读。他说不读更好。
听到这里,姜方亭重重叹了口气。《轻云集》中没有多说,一向以耿直敢言著称的姜方亭在这里惜墨如金,我们无法从被记述的文字中得到更多。但这口气,叹得确实百感交集。
九岁的国王F进入王宫,十四岁的时候举行亲政大典。大典进行了整整七天。在大臣们、侍卫们、太监们、宫女们的安排下国王F遵循那么繁复的礼节终于完成了豪华、隆重的亲政大典,如同一个牵线木偶,看得出,他的全部精力都在如何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规范、不致疏漏上,有些战战兢兢,却丝毫没有半点儿的兴奋。大典之后,国王F便病倒了,这可忙坏了内务府的太医院,好在国王F只是精力上的问题,并无大碍。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吩咐太监、宫女闭紧门窗,拉好窗帘,都不要来烦他,在病着的时候他谁也不见。谁也不见。是的,那时庞大的帝国风起云涌,种种事端甚至叛乱层出不穷,堪称多事之秋——好在,掌握权力的大臣们都不坏,他们尽职尽责,不让烦心劳神的消息进入国王F的耳朵。
正午时分,天气晴朗得有些晃人的眼,然而在国王F的房间里却是一片黑暗,只有一盏油灯微光如豆,以至前来送膳的小太监不得不立在门边,眯着眼睛,停上好大一会儿以适应房间里的光线。身影模糊的国王F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显露出来,他指点小太监,放那里吧。小太监听得出来,国王F的嗓音有些异样,可能是病还没有痊愈的缘故。
小太监退向门边,国王F似乎想起什么,突然叫住了他。“你今年多大?”
十一岁。小太监有些惶恐,因为国王F虽然从未处罚过谁,但也始终冷冰冰,还从未有谁能跟他说过多少话。
“那你,为什么进宫?”国王F似乎没有听出小太监的惶恐。他竟然有着兴致。
因为……回您的话,是因为,家里,穷……小太监的身体也跟着声音一起发颤,他的脑袋里有一股不断回旋着的风,在里面飞沙走石。
“你不用紧张。”国王F走过来,他竟然笑了,“你的样子,很像我刚进宫里来的时候。十一岁,我那时,觉得自己活不到十一岁,现在,我都十四了。”国王F抓住小太监的手,两个人的手都有些凉,“以后,你要多陪我玩儿,我都快闷死啦。”
国王F指指屋子,“你看里面多暗。我觉得,这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的鬼魂儿,它们在空气里飘着,伸着手,总想什么时候把你抓走。”
“光线暗下来的时候,你就能看得见。”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在位十三年,国王F都做了些什么?历史中鲜有描述,许多时候,他只是一个影子,把自己的年号印制在铜钱上,这是他标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国王F什么都没做,尽管他所在的时代,历史将它记述得跌宕起伏,群雄四起,生机勃勃。许多时候,国王F都只是一个影子,暗淡的影子,就像摆在酒宴上的觥筹、陶罍、觞、角,更后面些的花瓶,花瓶里已见枯萎的花儿,或者没人弹奏的琴。一次,酒后。国王F略略有些醉意,他让那个小太监把自己房间里的那些摆设的物品一一搬到屋子中央,然后一一指给这个太监看:
这个玉如意,谁谁谁的,他是国王C的儿子,因为谋反被杀。虽然后来国王c知道他并无谋反之意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他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
这把琴是谁谁谁的,他是国王C的儿子,在国王C死后继位,但后来染上风寒,死掉了。那风寒来得有些蹊跷。他只当了十七天国王,死时,不过十一岁。
扇子,原归谁谁谁所有,他在十二岁的时候成为国王,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成了废君,被关进地牢,据说后来被老鼠咬了一口,病死在牢中。他是我伯父的儿子。伯父在儿子被废之后也关入狱中,以教唆年幼国王意图杀害功臣、自己篡位而被处以极刑。
谁谁谁,在国王的位置上只待了七个月。他留在宫里的是这个瓷瓶,据说他喜欢剑,不过我叫内务府仔细查过,他并没有为自己铸造任何一把属于自己的剑。谁谁谁,这件衣物是他的,是我偷偷藏起来的,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国王……后来发生的事你也知道,是不是?
……国王F轻轻拂了两下琴,摇了摇扇子(虽然那已经是初冬,夜晚的风里浸带着冷,屋外露水沉重),拿起瓷瓶仔细把玩,将衣服披在自己身上(那件有些旧,而且被虫蛀过的夏衣略显小了些)……从小太监的方向看去,国王F的脸上笼罩着一团青白色的光,那团光里似乎包含着某种的不祥。小太监语出谨慎,国王,您,您不……我觉得您还是将它们放在另外的房间里为好,我知道它们都是您亲人们的遗物,可,可……现在您是国王,您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威严有魄力,您可以,可以……
“那你说,我可以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小太监喃喃,他一时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国王F的神态有些黯然,“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不同,就是我更软弱,更无用。因此我也活得长些。我可以做什么?我什么也不可以做。当初,”国王F再次披着被虫蛀过的锦衣,上面的图案已经相当模糊,“当初,我父亲在家里总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至于他忧虑什么从来也不曾跟我母亲和姐姐说。他只是天天钓鱼、喂鸟,到酒肆里喝酒直到大醉而归,还不许我和弟弟读什么什么书,倒叫我们画画花鸟、山水……我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什么也做不了。”
“他被杀了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因为……最终,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
国王F醉了。他醉在那些先前国王们的旧物中,醉得糊涂一片。“我总是能见到他们的鬼魂。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让我每天都如履薄冰。”
《轻云集》中记述,国王F很不愿意听自己的课,他说那些东西太沉重太严肃太宏大了,一听到这些,他的脑子里面就生出许多的虫子,咬得他脑仁生痛。他也不愿意批阅大臣们的奏折,那里面也有快速繁殖的虫子,总在眼前嗡嗡嗡嗡,让他烦乱。这个姜方亭有着自己的天真,他劝告国王F,你是一国之君,你要胸怀天下,你要思谋大事,何况当今……已经长大的国王F不再像先前那样怯懦、忐忑,他甚至显出一副无赖的模样:姜先生,够了,你来替我掏掏耳朵里的茧子。听我的太监说,南方有一种什么鱼,肉味鲜美,据说放在酒和童女的尿里腌制七天会更美,天下难寻。我已经叫人去弄了,也让内务府准备下酒和尿——等做好了,也送先生两条尝尝……
不只如此,国王F还总是借口头痛或其他的什么理由逃学,时问久了,他甚至连理由也懒得更换,那种倦怠让姜方亭感到痛心疾首。他在国王F的面前惩罚自己,痛哭,不停叩头,甚至威吓——然而根本无济于事,国王F似乎没有带来耳朵,装在他脑袋上的那两只被称为耳朵的东西是假的,是为了应付姜先生而设的。姜方亭给他讲前朝旧事,讲那些无能、昏聩、不学无术的国王,讲他们的荒淫、愚笨,倒行逆施,也讲某某国王如何勤勉,如何遵从礼法,如何仁,如何智,如何从一只三年不鸣叫的鸟一飞而起……那些时候,国王F根本没有带来耳朵,他的耳朵应当是假的,里面被他有意地塞满……于是,当姜方亭被自己的讲述感动得全身颤抖、几乎都要痛哭失声的时候,他发现国王F哈欠连连,或者是在纸上画一条瘦小的鱼。不只如此,国王F还和陪同他读书的王公、贵族子弟一起想办法捉弄老师,并在姜方亭的一本心爱的古籍中涂写文理不通的打油诗。他还带进过一只兔子和一只鹌鹑,那两只畜生先后成为课堂的主角,让这个被称为天下第一大儒的姜方亭气得面色苍白,一股腥腥的气在他口腔里冲撞,几乎将他撞倒在地。
姜方亭向监国大臣们请辞,坚决地请辞。那些大臣真的不坏,尤其是大司马和相国。他们也对国王F的所做颇有微词,颇有不满,但还是努力挽留姜先生:他还只是个孩子,长大了也许会好。如果姜先生都教不好他,那天下就无人能教好他了。他对天下,对百姓苍生负有责任啊。大臣们拉着姜方亭进宫,当着他的面,对国王F的怠学进行劝导、训斥,国王F认真地听着,眼里竟然含着泪水——那一刻,姜方亭也是百感交集。他的两条肋骨在隐隐作痛,也许,即将有一场连绵的阴雨。
《轻云集》里还记述了一件事,关于国王F的头痛病:有一次,国王F称病没去早朝,他说自己头痛得厉害,一切事务由大司马做主就是。早朝之后大司马过来探望,询问了病情,然后告诉国王F,自己有一名医生,来自西域,他或许有什么办法能够治愈国王的头痛。没多久那名医生真的来了,很快,他给国王F开出了药方:把一只黑蜈蚣捣碎,呈粉末状,然后加入赤环蛇的胆,少许红枣,鹿血,和他从西域带来的香精一起放在水里煮,煮成粥状即可。一日三次,七天之后就能清除国王F头脑里的全部虫子——可以想见国王F的反应。他当然拒绝,他说自己的病并不重,没什么大事,以后早朝过去就是了,以后……但在太监、宫女们的坚持下,国王F还是咬着牙喝掉了第一碗粥,第二碗则说什么也不肯再喝,甚至威胁,如果再让他喝,他宁可去喝毒药,宁可去死——不过,此药还真的起到了效果,国王F的头痛病很长时间都没有再犯,直到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怀南王病重的消息。
姜方亭在自己的《轻云集》记述了自己的教学体会,尤其是在晚年充当帝师的日子。看得出,他极为赞赏国王F之前那个未能登基的少年,对他的早天欷歔不已。而对国王F,姜先生的书写少有敬意,甚至,带有一种不太合君臣礼仪的鄙视。顺便提一句,在后来的史书中记载,那位少年因为与大司马发生争持而被另外的大臣击杀,虽然大司马狠狠处罚了那个杀王的大臣,但人死已难复生,另选国王的事已迫在眉睫。大司马和群臣连夜商议,于是,国王F被选入宫,成为了新的国王。《稗史搜异》中记述得则更为详细,它说,随着少年的长大,他对大司马的处事越来越不满,进而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有了一次、两次、三次的冲撞。构成少年“国王”死去的事件本是微不足道,但,少年和大司马,和大司马的心腹大臣们的芥蒂已经日深,小事儿生出了火花,直到引爆。《稗史搜异》说,那日的发生根本是个阴谋,是大司马计划好的,或者说他一直在寻找某个借口,那天,毫不知情的少年国王给了他借口,给了他理由。大司马指鹿为马,他当然是个故意。问题出在少年国王的身上,他悄悄纠正大司马,不是,不是的。你说得不对。怎么不对?大司马似乎很委屈,老臣真心可鉴日月,怎么会不对?尊贵的、至高无上的国王,你问一下你的臣民,我说的有错没错?
没错。大司马说得完全正确。几乎是众口一词。
只有一个职位低微的小官儿,向身侧的另一位大臣耳语,大司马,真是……身侧的大臣马上高声,他说大司马说得不对。
那个噤若寒蝉的小官儿已经直不起他的身子,他说不,不不不,他没有说什么,当然是大司马说得对,说得正确……
这番表白已经无法获得大司马的原谅,《稗史搜异》猜测,他的出现其实让大司马感觉窃喜,不足轻重的官吏正好充当威吓猴子的鸡。于是大司马沉下脸,这个无用的东西!你现在把说过的话收回,谁知道以后你不会把说过的话再次收回?这样朝三暮四的人怎么能为国家效力?如果你敢于坚持错误倒还可原谅,现在,你只有去死啦!拉出去!
少年国王站起来,他代那个小官儿向大司马求情,无论对错,他都罪不至死,请大司马看在我的面子上,重重处罚他一下就是了,还是饶过他的死罪吧。
大司马哼了一声。他问,众位大人,你们说,我们应该不应该饶恕他呢?
不能,当然不能。有人站出来,跪倒在少年面前:国王,此人饶不得啊!如果你饶恕了他,那如何能树王法之信?如果你饶恕了他,那之后臣子和百姓谁还会把国王你和大司马放在眼里?(少年国王的话在沉入水中的那个小官儿听来就像是一把稻草。他伸长脖子向少年哭喊,有几个大臣冲过去狠狠给他几记耳光,异常响亮。)
书中说,少年大怒。他冲着大司马:明明是鹿,你非要说马,可恨的是他们也都跟着说是马,这个人,只是说了句实话,也并非针对大司马,可你们就是不肯饶过他,你们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大司马并未说话,不过,大殿上已经是一片喧哗,他们向少年表白,在这个国度,只有国王你有至高的位置,没有谁敢不从;但,你也不能践踏大司马的一片苦心,他可是一心为国,再也没有比他更忠于你的人了;我们并不是为大司马说话,而是为道理说话,因为它明明是鹿,圣人说……
够了!少年忍无可忍,我早看够你们这副嘴脸啦!你们不觉得恶心?
众人嗡嗡嗡嗡,甚至有人向少年威胁,你的王位是谁给的你应当清楚,如果你如此不顾事实,不顾道理,那就请国王退位,让有贤德的人代替。
毕竟,他还是个少年。这个冲动的少年一边后退一边拔出身上的佩剑——一直跟随在大司马背后的一个武臣箭步上前,夺下国王的剑,然后刺向国王的胸膛……
《稗史搜异》把那段故事叙述得充满传奇。考虑到《稗史搜异》属于民间野史,“指鹿为马”也发生于前朝的前朝,所以并不可信。不过,有大臣杀死了即将登基的少年国王确有此事,他被杀死在大殿上也确有此事,确有此事的事国王F应当很清楚,当时,他父亲怀南王就在众位大臣之中,把事情的经过都看在了眼里。
南怀王病重的消息是一个宫女悄悄告诉国王F的,这个平常的消息却似乎是种危险,国王F也从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叮嘱这个宫女,千万不可再向外传,就连王妃也不要告诉,否则……
像历史上所有无能、昏聩的国王一样,国王F很少关心自己的国土、疆域、边关,这一切一直都由大司马等几位大臣处理。国王F日常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大司马他们的奏折上添上朱批:知道了,请大司马定夺;或者:由大司马办理。然而南怀王病重的消息让国王F想到了边关,想到了疆土。他叫人拿一本王国的地图。然后询问身边的侍卫、太监:你们谁去过那里?
大司马前来宫中,那天,患有哮喘的大司马有很高的兴致。两人下棋。说着说着,两人就说到了边关,他问国王F,你为什么对边关产生了兴趣?是因为南怀王吗?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不过,国王F还是做了隐瞒。他说,自己最近总是梦见自己的父亲,他在梦中湿淋淋的,很是憔悴,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国王F说,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就像是我的亲生父亲,所以在这许多年里我竟然忘记了他,竟然没有问过他的冷暖……
在一阵猛烈的咳嗽之后,大司马叹了口气,我得到消息,南怀王病了。很重,可能,可能挺不过这个秋天了。
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国王F有着夸张的惊讶和悲痛,眼里的泪水简直可算是汹涌。他倒向大司马的怀中,我想去看看他,行吗?
大司马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他在棋盘上落下一个无关紧要的子,“我老了。我知道我老了。”他盯着国王F的脸,眼里闪过一丝慈祥的光:“人生真是苦短啊。”
……大司马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此时,国王F已经二十岁,娶了大司马的侄女为王妃,生有两个女儿(国王F的王妃是一个极为有名的醋坛子,当然,野史中也说F一直很不检点,和宫女、另外的王妃偷偷摸摸,又做得拙劣,总是被王妃抓住尾巴)。在得知父亲病重之后,一向怯懦、慎小的国王F竟然未与大臣们商议便下达命令,让侍卫和太监准备,他要去边关探望自己的父亲。这,也许是最后一面。
国王的命令遭到内务府的阻拦,他们向国王陈述自己的理由:国不可一日无君,国王F如果要离开王城,必须要安置好各项事务,让大臣们分担职责;边关路途遥远,山高水恶,舟马劳顿,万一国王不小心染上恶疾,他们实在担待不起;同时,边关战事频频,且路上强寇众多,如果走漏风声,中了贼人的埋伏肯定会有凶险,他们万万不敢让国王如此涉险……不行。这次,我的决心已下。国王F回复得异常坚决,朝中诸事,尽可由大司马全权处理,我在的时候不也如此吗?
太监和大臣们也纷纷相劝,他们的理由和内务府的理由大致相同。国王F依旧那么坚决,你们说的我都想到了,我必须要去,我一定要去。争执到最后,国王F的声音都有些哽噎,谁不是父母生的养的?你们天天教育我要仁要孝,可我要尽一下孝心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阻止我呢?我多带衣物,多带侍卫,多带药品还不行吗?
不行。站出来的是相国。他对国王F说,自从你进得宫中,成为国王的那一天起,你就成了国王C的儿子,怀南王已与你再非父子,此后你是国王,他是臣民——我想教授你礼仪的老师早就讲过。本来,我是不准备讲这些的,可是,可是……你现在是一国之王,你不只是你自己的,还是天下百姓的,是苍生的……
“我不听!我不想听!我只想做一次儿子,尽一点孝心,之后我保证自己的所做全部符合礼!”那天,国王F有着特别的固执,显然这经过了深思与熟虑:“我已决定,后天出发。”
后来的事实是,国王F并没有成行。他是在第三天的清早起来了,然而,走出门口,发现门外空空荡荡:没有侍卫、宫女、太监,也没有放衣物、药品、钱币的箱子,没有车,没有马。除了一片两片的落叶,一直到宫门,显得那么空旷,这空旷里有一个隐秘不见的涡流。
国王F愣了一下,大约三分钟,他转身,自己披上一件长袍,然后移出一个箱子,将十一岁进宫以来自己房间里的一些旧物件一一收好,放进箱子里,锁上,然后一点点将它推出房门——
倚在门口,王妃哧哧地笑着。“像你这样,把这个箱子搬出王城怕也得十年。”
国王F没有理她,而是继续。不过,她说的确是事实,国王F缺少移动什么的力气。可是,那时,国王F已经骑在了虎上。
……略去国王F赌气的过程,他折腾到临近黄昏也未能走出宫门,侍卫们拦住了他,他们请国王F原谅,奉内务府命令,他们必须冒死留住国王,不能让国王F到外面去涉险。满腔怒火的国王F使用咒骂、拳脚、绳子和青铜如意,都无法令那些侍卫们退让半步,尽管有两个侍卫已经满脸鲜血……这时院子里一阵嘈杂,向后看去,平日跟随国王的太监、宫女被捆绑着,推搡着向后院走去。国王F急忙大喊,你们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凭什么要绑住他们?没人回答他的话。只有两个老太监跪下来,死死抱住国王F的腿:奴才们求求你,别闹了。事情已经够大了。你放过我们吧,我们不能不……
怒火难消的国王F坐在一棵银杏树下,坐在秋天的冷风中,身上的锦袍也被他弃在一旁。他像一块枯干着的木头,把黄昏里的黄一点点熬尽,昏越来越重,直到,这份昏也被黑暗一点点代替。坐在树下,国王F用力拽下一旁的草叶,将它们一一撕成极为微小的碎片。
在国王F的一生中,那是他唯一一次被记载下来的“对抗”,尽管虎头蛇尾,尽管很不成功。没多久,就传来他的父亲怀南王去世的消息。和前面的反应不同,当这个消息真的进入他的耳朵,国王F完全无动于衷,目光始终追随着乐池里一个跳舞的宫女。他说好,跳得真好。
头痛的病症又回到了他的身上,确切地说,是那些曾经休眠的虫子开始复活,它们比之前更为活跃,有了更锋利的牙齿。国王F痛得不能早朝,不过,到下午时分情况就会好转,见识渊博的太医们也无法解释这一病症的成因。在和国王F下棋后不久,大司马的病情也越来越重,他没有体力再来王宫探望,国王F也就避免再次饮用西域医师的怪药。有人说,如果国王F按照西域医师的要求喝足七天,他的病应当早已痊愈;还有人则保持怀疑,他们认为,国王F如果喝足七天,也许会严重中毒,成为那个年代第七个早夭的国王——谁知道呢。
那个年代,历史上它被称为多事之秋,似乎坚固无比的王朝在国王F在位的时候迅速崩塌,四处燃起不安的小火苗,而它们总能遇到干柴。大司马的病情越来越重,国王F过去探望,亲自为大司马煎药、喂食,像他亲生的儿子……临终的时候,大司马已经不能言语,他伸过手,把国王F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国王F也在抓着,他感觉,大司马的手一点点变凉,变凉,丧失了最后的温度。
那个被称为多事之秋的年代,国王F任命大司马的儿子担任大司马,这一任命遭到相国和一些大臣的反对,甚至爆发了直接的战争,一度,国王F不得不跟随大司马的部队四处逃亡,他的一个女儿也在逃亡的路上丢失,再无下落。好在,两个月后大司马在血战当中最终获胜,借国王F的口气,相国一家一百七十余口以叛乱罪被处凌迟。某地发生叛乱,某地农夫抗税杀进了官府,某地瘟疫,大旱……国王F的头痛病似乎越来越重,越来越频繁,没有大事的时候,不是他必须出现的场合,他就不再出现,而是由大司马负责。尽管累些,大司马似乎也乐得如此,真的,事实上,大臣们都不坏。
国王F的头痛病,一过中午,他的病情就会见轻、消失,总在屋子里待着实在无聊,于是,国王F开始醉心于书法、绘画、金石——这个兴趣并没有被坚持多久。后来国王F迷恋起养鸟,他请大司马和各地的官员给他搜罗各类鸟蛋,让母鸡孵化——这个兴趣也未能坚持多久,原因自然出于王妃的干涉:鸟们总在房间里拉屎,掉落羽毛,而且有些鸟蛋根本孵不出任何的鸟来,却弄得屋子里、院子里充满了恶臭……国王F也曾醉心过一段戏曲、歌舞,但,我们不能忽略掉他身侧那个随时出现的醋坛子。最后,被国王F坚持下来的是在王宫花园里的一出游戏,有时,王公大臣们也会参与,包括新任的大司马。游戏如此:
王宫的后花园,建起了两排相对简陋的棚屋,一到下午,厨房里的厨师,药房里的药师,宫女太监们,都换上市井百姓的衣装,模仿贩卖的商人,将自己的物品或刚刚采购来的物品拿出来卖。有时王公大臣会成为这个街市的顾客,如果他们不来,顾客就由国王F从太监宫女和侍卫中选取。这一游戏中,国王F极大地表现了他的经商天赋,太监们学来叫卖的吆喝只要当着他的面喊过一遍,国王F就会将它记住,有模有样。他最愿意扮演的是屠夫,将一个油渍渍的小褂套在身上,上面还有被虫蛀过的痕迹;你想要多少肉,他眯着眼,一刀下去,分量几乎一点儿不差。大司马总是来买他的肉,一刀,一刀。大司马总是多给几个赏钱,而屠夫,也俯首致意,谢谢客官关照。请你下次再来。
“你要是不做这个国王,而当一个屠夫……”大司马感叹。
国王F最终是否真的当上了屠夫不得而知,无论正史野史对此均无记载,似乎无人再关心那些琐事。不过,国王F很快就不做国王了,他的头痛病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显得昏庸、无能。第十三年,也就是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国王F的一再坚持下,大司马虽经多次推辞,最终还是成为了新国王。一个庞大过的王朝,坚硬过的王朝由此结束。
姜方亭去世较早,当时国王F还是国王,他甚至还没有经过那次不成功的“反抗”,所以《轻云集》对之后的事件没有记述——要是他知道国王F后来在王宫里进行商贾游戏,肯定会在死后起来再死一次,他见不得这些。《稗史搜异》对国王F的记述也只到“禅让”止,而据传为“兰陵哭哭客”所著的《聊经》,对国王F的禅让写得相对详尽:
一段时间里,国王F反复接到各地官吏斥责国王不尽职责、昏庸乱国的奏折,这当然是个苗头,不过一向迟钝的国王F并没有将它们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国王F没去早朝,愤怒的大臣们竟然涌进了王宫,一起跪在台阶下。怎么办?你们要干什么?
负责军机的大臣,走到国王F的面前,用很轻的声音将国王F唤进内室。很不好办。他们的怒气很难平复。你必须要有个交代。
——怎么交代?
那个大臣,直视着国王的脸。他一字,一顿:把,王,位,让,给,贤,者。
随后,他紧接着加上了一句,我这是为你所做的考虑。
只愣了半秒。对于这个结果,国王F仿佛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是啊,是啊。我也……我也想到了。我只是一直幻想,它晚点来,晚点来,其实这一天早该来了。
国王F如此痛快,倒是让这位大臣有些意外。你,你不再想想?
不用。国王F直起身子,他朝黑压压的头颅们看去,大司马并不在他们中间。“请你转告大司马,我今天下午就准备让位的诏书。今晚,还有最后的一个夜市。”
大司马是不会接受的。他很可能不会接受。这,只是我们的意思。
国王F并没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伸了伸腰:“我这辈子,过得提心吊胆,没有一天做过自己。好在,不用了。”
责任编辑 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