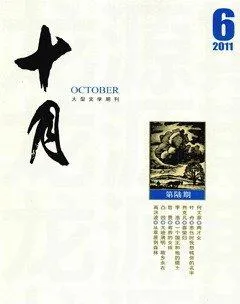黄鼠
苏莱曼阿訇是我们村上的执坊阿訇。他是和州人,深眼窝,高鼻梁,大胡子,和我们村的人长相不太像。他个子很高,不是一般的高,比我们村最高的人还要高出半个头。他的舌头好像有些大,嗓门也有些大,说出的话直撅撅、硬邦邦的,听着好像在跟人吵架。
实际上,村上谁都没和苏莱曼阿訇吵過架。咋可能吵架呢,他是村上请来的阿訇,村上的人都敬着他,见面要给他道色俩目,走路要把他让到最前面,吃饭要把他请到最上席。不光是对苏莱曼阿訇,对所有教门上的人,有知识本领的人,村里人都这样敬着。正因为这样,苏莱曼阿訇说的话,村上的人谁都听。弟兄妯娌之间有了家务争执,也都找他解决,他出面高葫芦大嗓子地说几句话,粗听着像是在嚷嚷,细听句句都在理上,谁都没法辩驳,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他的大嗓门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念礼拜呼唤词的声音非常洪亮。他站在清真寺邦克楼上念,村子里每个人都能听得见。听见了,男人们都到清真寺去做礼拜。谁要是不去做礼拜,苏莱曼阿訇可真的要跟谁吵架。他性子直,一点儿都不会拐弯抹角,见了面就质问,你为啥不礼拜?对方辩解说,下了点雨,着急去种豆子了;或者说,地里的麦子黄了,着急去拔麦子了。苏莱曼阿訇又问,谁家不种豆子,不收麦子?你说前世的光阴大,还是后世的光阴大?他问的话,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向对方射過去,他的长胡子也乱箭一样,一撅一撅地向对方乱射,弄得对方头上直冒汗。所以,村上的人都有些怯他。
苏莱曼阿訇把教门上的事看得很重。当然了,作为执坊阿訇,那是他的责任。他说,村里人做了错事,他也担着罪责呢。苏莱曼阿訇常做的不是职责内的一件事,就是看病。当然了,他并不是医生,他不看头痛脑热拉肚子那样的病,那有村医马有国去看。他看的是吐沫瞪眼、发疯撒泼那样的怪病。谁要是得了那样的病,村医马有国就没办法了,苏莱曼阿訇過去,打开经,念一念,对着患病的人吹一吹,那人有时还就慢慢缓過来了。尤其是小娃娃,魂魄还没有长全,得怪病的多,苏莱曼阿訇的一双大手小心地托着害病的娃娃,吹吹念念的,娃娃就好了。见過苏莱曼阿訇把那么大的牛羊都能宰了,我们小娃娃也都有些怕他。我们要是不听话了,大人们还拿苏莱曼阿訇吓唬我们,说叫苏莱曼阿訇把耳朵给割了去。但看到苏莱曼阿訇给娃娃看病的样子,我们就不怕他了。不仅不怕他,还愿意亲近他。他很喜欢小娃娃,看到了,就用一双大手托起来,托得老高,小娃娃咯咯地笑,他也呵呵地笑。大概是因为他的儿孙都在老家,经常见不上,才这样稀罕小娃娃。也有人说,他在老家那边根本就没有家,没有儿孙,谁知道呢。反正他很少回老家去,一直都在我们村上执坊,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在;我七八岁了,他还在。住的时间长了,村里人都把他当自己人了。而他说话、走路,连长相也似乎变得像村里人了,个头也好像没有那么高了,和村里人一般齐了。
只有一样没变,他的脾气还是那样大,比他的个头还大。不過,他一般不发脾气,发脾气一般是有人违犯了教规。那一年,村上有很多人犯了教规,苏莱曼阿訇的脾气也发得很大。
那一年是个灾年,春旱、秋涝,粮食基本上没有收成。秋涝過后,又是黄鼠成灾。村里人从来都没有见過那么多的黄鼠,那么大的黄鼠,简直就跟野兔子一样大,圆滚滚、胖乎乎的,成群结队在田野里、地头上跑。见了人也不害怕,还抱起前爪,立起后腿,站着看人,像是给人作揖打躬,又像是要跟人比个高低。人真撵到跟前了,它们才“铮”“铮”地尖叫几声,眨眼间就跑得没个影儿了。突然间出现那么多的黄鼠,看着叫人不舒服,但黄鼠是野物,最多拉点粮食,没有啥大的危害。所以,谁也没有在意。
往年也出现黄鼠拉粮食的事,但黄鼠很少,拉不了多少,人也不咋管,任由着它拉,都是真主造来的物儿,都得活。谁都没想到,黄鼠成了群,就不得了,几天时间,地里剩下的糜头子、谷穗子都被黄鼠拉到洞里去了。黄鼠严重地加大了灾情,村里几乎没有收成,一入冬就几乎断了顿。大冬天的,想找野菜草子也没有,想吃树皮树叶也没有。怎么办呢,人们开始打黄鼠的主意,挖黄鼠仓,抢回被黄鼠拉去的粮食。找到—个黄鼠仓,就能挖到好几十斤粮食,够一家人吃好些天。村里人靠挖黄鼠仓,度過了大半个冬天。
到后来,就找不到黄鼠洞了,找到了黄鼠洞,也挖不出粮食来了。有说是黄鼠仓都挖光了,有说是黄鼠把粮食转移了,谁知道呢。反正人都饿得头昏眼花的,但黄鼠一个个还肥嘟嘟的,有太阳的中午,就钻出洞来晒太阳,还是成群结队地跑,“铮”“铮”地尖叫,见了人还是抱拳打躬的。村里人看着牙痒痒,恨不得吃了它。可回民不能吃黄鼠,这在经典上有规定呢。
经典上还规定了,自死的牛羊也不能吃。偏偏村上的一头耕牛摔死了。一头牛死了,这在平常年景,谁也不会想着吃死牛肉,但在灾年,人都饿得不行了,村上很多人都动了吃肉的念头。动了念头,但不敢吃,去问苏莱曼阿訇。苏莱曼阿訇回答得很干脆,坚决不能吃。苏莱曼阿訇这样说了,但村里人还是把死牛肉偷偷地分了。又去找苏莱曼阿訇,说能不能叫娃娃吃,娃娃们快饿死了。苏莱曼阿訇还是很干脆地说,不能吃。苏莱曼阿訇还说,灾难是真主降下的,就是要考验人的心。灾难很可怕,但人心动摇了,比灾难更可怕。他要分了死牛肉的人家,都拿回来,扔在清真寺门前的一个大坑里,要埋掉。他亲自站在坑沿上看着一个个都把死牛肉拿来,扔进坑里。苏莱曼阿訇叫人们动手把牛肉埋了,可谁也不动弹,都眼巴巴地望着坑里的牛肉。苏莱曼阿訇就自己动手挖土埋,边埋边就发了脾气,声嘶力竭地大叫大骂起来,骂得全村人都低下了头,骂得村里的老人们都流眼泪。
村里人谁都知道是自己错了,谁都知道苏莱曼阿訇骂得对,但眼看着救命的牛肉被埋掉了,大家对苏莱曼阿訇还是有了一种怨恨,觉得他不近人情。要说不近人情吧,過后,苏莱曼阿訇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挨家挨户地送,边送边劝,说这是人心变坏了,才招来了灾难。在灾难面前,人心动摇了,还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村里人接過他手中的钱,也听了他说的话,度過了几天平静的日子。但饥饿却并没有远去,不几天又到了眼前。村里人又开始想尽各种办法,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凡是能吃的,几乎都弄来吃。打兔子、抓鸽子、逮麻雀,抓到了就叫苏莱曼阿訇给宰,苏莱曼阿訇就给宰了。经典上没有规定不能吃的,他不能拒绝宰。
马哈桑抓了一只黄鼠,要苏莱曼阿訇宰。苏莱曼阿訇说,黄鼠不能吃,他不能宰。可马哈桑说,他抓的不是黄鼠,是野兔子。苏莱曼阿訇仔细看了,大小毛色和野兔子差不多,但小耳朵、尖尾巴,明明是黄鼠。马哈桑不知是饿昏了,还是咋样,说他抓的就是野兔子。他还把黄鼠拎起来,对围观的几个人说,大伙儿看看,这是不是野兔子?能不能吃?马哈桑是个满脸胡子的壮汉,平日里就横些,围观的人谁也不说话。苏莱曼阿訇也对围观的人说,大伙儿说,他拿的是不是黄鼠?问了几声,围观的人还是谁也不说话。苏莱曼阿訇气得花白胡子抖了半天,踉踉跄跄地走进清真寺里去了。
马哈桑就拎着黄鼠走了,围观的人也散了。
過了不一会儿,马哈桑又跑到清真寺找苏莱曼阿訇。苏莱曼阿訇赶紧说,说啥他也不宰黄鼠。马哈桑说,不是要宰黄鼠,是要苏莱曼阿訇過去给他儿子看病,他的大儿子发疯了。
苏莱曼阿訇随着马哈桑跑過去时,马哈桑的大儿子已经被几个人摁住了,但他还狂喊狂叫地挣扎着,他刚刚二十出头,正是有劲的时候,几个饿乏了的人,都摁不住他。
苏莱曼阿訇问了情况,才知道是马哈桑的大儿子拿着菜刀要砍自己的弟弟,说砍死了要吃他的肉。要不是他妈发现,弟弟就被他砍死了。他弟弟是个四五岁的小娃娃,在母亲的怀里,惊恐地抽搐着,身上还流着血。还有几个大大小小的娃娃睁着奇大的眼睛看着。马哈桑家的娃娃太多了,大概有七八个。
待了一会儿,苏莱曼阿訇没有给马哈桑的大儿子看病,也没有给马哈桑的小儿子看病,而是对着马哈桑说,把你抓来的兔子拿来,我给你宰,兔子就能治病,吃了兔子病就好了。
马哈桑刚抓了黄鼠過去要苏莱曼阿訇宰,家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觉得都是自己招来的罪過,这会儿说啥也不敢再把黄鼠抓来叫苏莱曼阿訇宰了。他嗫嚅着说,那是黄鼠。苏莱曼阿訇嘶哑着声说,那明明是兔子,谁说那是黄鼠?你快拿過来,我给你宰。马哈桑又怯声说,我再不敢了,那是黄鼠。苏莱曼阿訇说,快拿来呀,你要看着人吃人吗?要看着哥哥吃弟弟吗?我说是兔子就是兔子,你快拿来呀。马哈桑拎来了黄鼠,苏莱曼阿訇念诵了一段经文,宰了黄鼠。对马哈桑说,这是兔子,赶紧叫娃娃吃吧。他还叫村上的人都去抓黄鼠,抓来了,他也都给宰。他说,这是兔子,放心吃。山上有那么多的黄鼠,村里人就靠黄鼠度過最艰难的日子,没有饿死—个人。不久之后,草木返青了,上面的救济粮也下来了,村里人度過了大难。人们想到了苏莱曼阿訇,苏莱曼阿訇却不见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