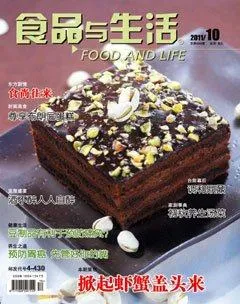一顿包谷饭
有句老话说,南人吃米,北人吃面。作为典型的南人,我每天只习惯于吃米饭。尽管我有时也会吃一顿馄饨、面条之类的面食,但倘若连续吃上两顿,就浑身不自在,特别想吃米饭。
大学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听说贵州人吃米饭,我就办妥手续,去了贵州。当时,我被分配到一个条件相对优越的县城。初来乍到,我们这些陆续抵达报到的大学生暂时被安排在县革委(县革命委员会的简称)食堂用餐。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贵州人盛行吃甑子饭,先将米煮过一道,滤去米汤,然后放在木制的甑子里蒸熟。甑子饭做起来颇为麻烦,而且于我而言,口感不及一次煮成的焖锅饭。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那段时间当地粮店向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有细粮和粗粮之分,细粮是大米,粗粮是面粉和包谷面(即玉米面),出售细粮时要按一定比例搭售粗粮。因此,我们早餐吃稀饭、馒头,中餐、晚餐吃用包谷面与大米混蒸而成的混合饭。因包谷面色黄、米饭色白,黄白相间,当地人俗称“金银饭”,我们则戏称“蛋炒饭”。不过混合饭里毕竟米饭多于包谷面,虽然不如纯米饭好吃,但我还不觉得很难吃。好在吃混合饭的日子不长,不久我们就吃上了米饭。
然而,那年月在偏远的山区农村,为温饱发愁的农民却不敢奢望米饭,只能天天以纯包谷饭果腹,能够在包谷饭里掺点米粒的人家已经算是小康了。一次下乡工作时,我还真吃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包谷饭。
那天吃过早餐,我跟随公社党委陈书记翻山越岭,步行许久才到了要去的山村。那里山峦起伏,山谷绵延,山高坡陡,山多地少。由于耕地大多为旱地且十分贫瘠,既耐旱又高产的包谷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包谷饭就成了村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主食。
中午时分,村支书带我们到一户农家吃饭。女主人做饭手脚利索、动作娴熟,说话间饭菜就摆好了。饭自然是包谷饭,菜也非常简单:一碗腊肉蒸腌菜,一碗米豆烩酸菜,一碗素白菜蘸辣椒水。那几个菜美不美味还在其次,关键是那金灿灿、香喷喷的包谷饭吃到嘴里如同锯木屑,嘴唇、胡须还会沾上包谷细粒,口感则和我小时候爱吃的爆玉米花判若两物。不过最难以忍受的是,吞咽时喉咙有强烈的戳痛感,简直无法下咽。我吃着粗糙干涩的包谷饭,不由想起松软可口的米饭,越想越觉得包谷饭太难吃了。我暗自叫苦不迭,无奈饥肠辘辘,又见陈书记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只得胡乱扒了几口包谷饭,努力咽下喉去了事,根本就没有吃饱。虽然这是我平生吃过的唯一一顿包谷饭,但它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忘。
饭后聊天,我才知道包谷饭的制作过程十分繁复,不仅耗时耗工,而且水量及火候不易掌握,技术不到家是绝对做不好的。包谷饭的通常做法是:用石磨将晒干的包谷粒磨成包谷面,用筛子筛去皮壳;将包谷面在竹编的簸箕里用清水均匀拌湿,水量以手捏包谷面不出水,手放包谷面能松散开为宜;用饭瓢将包谷面舀入甑子,把甑子置于铁锅中,锅里灌水,水不能太多;将包谷面蒸至五六成熟,蒸时火要大,热量要充足;将甑子端出,把还未蒸熟的包谷面倒入簸箕内,同时把甑子放回锅里预热;用饭瓢将包谷面捣散至互不粘连,然后用清水再次拌湿,水量须恰到好处,水多包谷饭太湿,水少包谷饭太硬;待包谷面完全吸收水分后复入甑子,盖上甑盖,旺火再蒸,熟透即成。
如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缺米吃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即便在昔日贫困的山区农村,尽管地里种出的粮食还是包谷,但农民都已改吃米饭,包谷是留着喂猪的。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专家对包谷多有溢美之词,称其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以及大量人体生长发育所需的支链淀粉和赖氨酸,营养价值之高为米、面等主食所无法比拟;粗纤维丰富,有利于增强消化道良性蠕动,从而有效减少发生肠道恶性病变的可能,等等。于是,一些吃腻了米饭的城市人又把目光转向包谷饭。包谷饭因而上了他们的餐桌,甚至进了一些上档次的饭店,还美其名曰“黄金饭”。不过,回想起当年吃包谷饭的情景,我仍然心有余悸,不要说吃包谷饭,就连再尝一口的念头也没有。
在各种主食中,我对米饭情有独钟,喜食米饭的饮食习惯将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