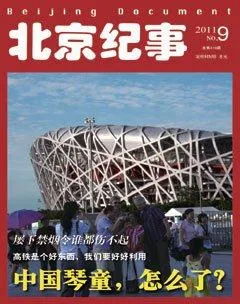薪火相传国粹生辉八
2011-12-29 00:00:00咪拉韩旭麻雯
北京纪事 2011年9期





北京京剧院名家荟萃、异彩缤纷,凝聚了很多京剧大家前辈的心血。1951年成立的北京市艺培戏校,便为京剧舞台培养了很多中坚力量,如老生李崇善、丑角黄德华,均出自艺培戏校。后来成立的北京京剧团作为北京京剧院的前身也是人才济济,如著名司鼓金惠武。从他们的人生中可管窥中国京剧发展历程,亦可见北京京剧院的一路走来。
天通苑的某栋公寓,面朝麦田,每天早上,李崇善都面向这片开阔的麦田练声。
年逾七旬的李崇善个头不高,但身板挺直,面色红润光泽,皮肤细腻,眉宇间可见年轻时的俊朗。作为谭门老生,李崇善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京剧演员,为数不多的几出戏却是划时代的精品——“文革”中最后一出现代戏《磐石湾》,“文革”后第一出传统戏《逼上梁山》,1981年新编历史戏《正气歌》,1995年现代京剧《圣洁的心灵——孔繁森》,获文化部颁发的第九届文华奖。1998年在新编历史剧《风雨同仁堂》中扮演大查柜,该剧获中国京剧节金奖。
谭门老生李崇善
艺培戏校的重点生
1951年,年仅11岁的李崇善报考艺培戏校时,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时候,上小学的李崇善早已是学校文艺骨干,话剧团、歌咏队都积极参加。当看到艺培戏校第一届招生简章时,李崇善想:一直喜欢看戏,再说学了戏就可以养家了,那就考一下试试。初试,一位老师招手叫李崇善过来,拿手当髯口往李崇善脸上一比划,再把眉毛一吊,说:“老生,合适!”后来李崇善才知道,这位老师是荀慧生的二儿子荀令文。复试,主考老师是王少楼,也是后来李崇善从事京剧艺术最重要最关键的老师之一。李崇善准备的歌曲《嘿啦啦》,是一首上世纪50年代的大众歌曲,唱了七八遍都没唱下来,忘词了。没想到王少楼老师竟然让他通过了复试,王老师看中的是李崇善宽厚嘹亮的嗓音。师徒二人多年的缘分也由此开始。
初进艺培戏校有3个月的试学期,就是看看这个学生从事京剧够不够条件,不够条件就退回原来的学校。李崇善1952年入校,到1953年,就跟王少楼老师学习并演出了《二进宫》《黄金台》《辕门斩子》等戏。那时候戏校的方针是:重点培养,普遍提高。先天条件优秀的李崇善自从入校便是重点培养对象,入校3个月就可以登台,11月份就去老长安戏院给北京市委领导演出了《黄金台》。李崇善记得演出完,每人奖励两块奶油蛋糕,“那是我头一回吃洋点心。”1953年,艺培戏校变成北京市戏曲学校,教学条件越来越好。艺培戏校坐落于一座破庙里,四周都是乱坟岗子,是原来京剧梨园公会的墓地。1953年成为北京市戏曲学校后,盖了两排平房宿舍,学生们就不用走读了,教学条件的改善让大家学戏更有劲头。然而,此时,李崇善却遭遇了学戏的第一个挫折。
晚上刚演完《黄金台》,第二天早上,李崇善醒来发现已经8点多了,9点上课就要迟到了,匆忙穿上棉袄,蹬上自行车直奔学校。到了学校,由于热身子受风,身上起了好多个风疹大包,这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痊愈后吊嗓子,发现高音唱不了了。没办法,王少楼老师就从老生二组把张学津调过来,让他接替李崇善唱正宫老生戏。学校为了不让他脱离舞台实践,除了每天上王少楼老师的课外,还让他抽一个课时去老生二组学习,跟花脸、老旦、旦角合作唱二路活,例如《姚期》里的刘秀、《凤还巢》的程晋、《岳母刺字》的岳飞等角色。到1957年李崇善嗓子恢复如初,这4年间,在二组也没少参加演出,并跟着王少楼老师学了不少出戏,例如《八大锤》的王佐、《洪洋洞》的杨延昭、《空城计》的孔明、《四郎探母》的杨延辉等正宫老生戏。说起自己的启蒙老师、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老师王少楼,李崇善说:“我一共跟王老师学了近40出戏。王老师的唱腔是非常规矩的余派,相当于学书法的楷书,给我打下了很扎实深厚的基础。”
谭富英的钦点弟子
艺培戏校首届学生毕业演出,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都来了。李崇善唱了《四郎探母》“见弟”一场的片段,被顺利分配到梅兰芳京剧团。首届共108名毕业生,只有15名被分配到梅剧团。那时的政策是私营公助,毕业生一年的实习金是32块,那时候一个月的饭费才9元,可以说待遇相当不错。梅剧团的演员就住在吉祥戏院。李崇善记得第一次演出的是《捉放曹》的陈宫“行路”一折戏,梅先生亲自来看戏。李崇善跟梅兰芳的亲传弟子李玉芙在戏校就是老搭档,到了梅剧团更是经常合作。梅先生最后一出大戏《穆桂英挂帅》,李崇善演金殿的大太监,还有末场点将的一个小兵,这是为数不多的跟梅先生同台演出的经历。还有一次是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梅先生的大轴,前面有两个戏,其中一个是李崇善唱的《定军山》。
在梅剧团不到一年,有一个北京市青年演员汇演,北京市戏曲学校组织了一场穆桂英主题的演出,共有10位穆桂英、3位杨六郎,演出非常轰动,得到了彭真市长的肯定。彭市长说:“他们有个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北京市青年京剧团、实验剧团?”就这样,1960年,从梅、尚、荀剧团挑选了一部分演员,成立了北京市戏曲学校实验剧团,李崇善也成了实验京剧团的一员,并排演了《赵氏孤儿》的赵盾一角。
1962年时兴大拜师,北京实验京剧团的演员基本都拜师了,而李崇善迟迟没有拜。当时陈竹新副团长对李崇善说:“你要觉得哪出戏好,你就说,团里派你去学。”李崇善就学了《赵氏孤儿》,没想到谭富英老师看了,就跟谭世秀说挺喜欢李崇善。谭世秀就把这话带给了实验京剧团团长,团长一听,跟李崇善说:“喜欢你,你还不明白吗?喜欢你就拜吧!”10月份正式拜师,之后因为谭富英老师正病着,李崇善跟他学戏不多。谭富英老师说余谭不分家,谭富英是余叔岩的学生,余叔岩是谭鑫培的学生,而李崇善的启蒙老师王少楼是余派的,所以有了余派基础再学谭派,对李崇善来说并不难。
李崇善记得跟谭富英老师学得最扎实的一出戏是《将相和》,师哥谭元寿先给他说戏,说完谭富英先生就把椅子搁在客厅门槛那儿,把院子当舞台,李崇善就开始给他演。谭富英先生一边看一边跟李崇善说着戏,师哥谭元寿就在旁边看着。这出《将相和》于1962年演出了,1963年就开始了现代戏的独霸天下。
从B角到第一主演
1969年,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来北京拍电影,需要两名B角演员。江青亲自指示把李崇善和张学津两人调到《智取威虎山》剧组,周总理签的调令。不承想,这一去就是8年零3个月。李崇善担任参谋长少剑波的B角,1969年5月,B组演员在人民剧场彩排。第二天一早,少剑波的A角演员沈金波来找李崇善,原来他嗓子水肿,没音了,让李崇善接下晚上的演出。“我不敢接,样板团的政治压力太大,江青同志讲:堡垒特别容易从内部破坏。质量要求特别严格。”身为B角演员,不仅仅是替A角试戏,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尽管压力很大,李崇善还是顶上了。头一天演出,效果很好,观众反应很强烈。第二天一早,沈金波的父亲来了,问李崇善是不是沈金波出了什么问题,被撤下了?在那个特殊氛围下,任何一点波动都会引来很多猜测,还好,李崇善出色的演出顶住了各方压力。从那以后,《智取威虎山》就变成A、B制,两组演员来回倒。李崇善跟童祥苓一组,张学津跟沈金波一组。
“那个B组真是B组,我们都特别努力刻苦,把整出戏都掌握了。”李崇善还记得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审查改编本,把《智取威虎山》的人物名字都改成近似音,比如“杨子荣”改成“梁志彤”。审查完头一天提了50多条意见,第二天接着审,落实了30多条,那天晚上的演出就是张学津演的。李崇善说:“我们B组就得这样,随时待命,说让你上你就得上。”
1971年李崇善接到任务,去崂山地区体验生活,准备排第二出现代戏《螺号长鸣》,主人公名叫鲁长海,1972年3月,排出了第一稿,后改名为《磐石湾》。
1974年汇报演出《磐石湾》,改了很多地方,“跳海”的戏要李崇善从蹦板上弹飞出洞,有蹿毛的技巧,从两米多高的台子上往下跳。李崇善就一个人刻苦练习,把跳高架子逐渐加高,把下面的海绵垫逐渐减少,练到后来终于能从两米多高的洞口蹿出,而下面只有一指厚的垫子,练那段可没少挨摔。1975年《磐石湾》定稿,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谢晋导演拍摄成彩色戏曲片,终于在全国放映。李崇善作为主演,该剧成了他的成名作。
1977年,李崇善从上海借调到北京,演了“文革”以后第一出传统戏《逼上梁山》。李崇善坦言:“乍接《逼上梁山》时有点担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批了多少年了,这回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我又是从样板戏过来的。”也许正是因为“文革”十年没有传统戏,《逼上梁山》反响非常好。对于李崇善来说,最后一出现代戏《磐石湾》、“文革”后第一出传统戏《逼上梁山》,这两出戏见证了一个特殊时代,也成为李崇善的代表剧目。
1977年10月,李崇善的户口从上海转回了北京,接连当了7、8、9三届北京市人民代表。李崇善谦虚地说,当了15年人民代表,也没干什么,还是只顾演好戏。1978年恢复北京市实验剧团,1981李崇善接排了《正气歌》,这是他调回北京3年后接排的第一出戏。戏中,李崇善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引起很大反响,在那个营销意识淡薄的年代,还出了小人书、四扇屏等周边产品。1984年,江西省电视台要为文天祥举办周年纪念活动,就把《正气歌》排成了4集电视剧,依然是李崇善主演。
1993年,李崇善成为北京京剧院三团团长兼业务骨干,1996年,排了现代京剧《圣洁的心灵——孔繁森》,该剧让他获得平生第一个奖项:第九届文华奖。1998年,李崇善在新编历史剧《风雨同仁堂》中扮演大查柜,该剧获中国京剧节金奖。
2000年,年满60岁的李崇善退休了,却并没有告别京剧舞台。2002年在江苏南京京剧团排了一个叫《胭脂盒》的戏,因为20多年的哮喘病发,影响了参加汇演的机会,由别人接替了。也是因为身体状况,李崇善没有收徒弟,却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已任教3年。李崇善保养得很好,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最关键的是心态很乐观,“一般人家说我:您今年有65了吧?我就说:谢谢您!人家纳闷:谢我什么呀?我说:我今年72了,坟地里的狗——假欢!哈哈……”
年逾七旬的李崇善依然坚持每天练声,逢年过节若是有演出,随时都能登台。今年刚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演出上唱了一段《磐石湾》的主叹“负伤痛冲破了千层巨澜”。李崇善说:“我这个年龄不练声不行,要不然遇到这种事情,现磨枪它不给你。唱《磐石湾》我还是原调门。这个年龄能唱这个戏,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吧。”
黄德华老师书房的柜子上面有一张照片,黄老师指给我看:最左边的是李长春,然后是叶少兰、谭元寿、张学津、尚长荣。“最右边的蒋干是我。”黄老师笑着和我说,带着老北京人的字正腔圆和丑角儿念白的一丝雅韵,“怎么叫《群英会》呢?‘众家群英’到齐后,我只去参加一个‘会’。我感觉和这些人一块儿演戏是一种学习、享受,因此就把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高高挂起了。”
黄德华:梨园名丑,德美艺华
希图上进的学戏生涯
1942年,黄德华生在宣武区粉房琉璃街。当时琉璃街住着很多的梨园名流,黄德华一家人和这些京剧界的街坊都十分交好。黄老师跟我说,祖父画画在当地小有名气,能画四个判儿(判官)坐在一起打牌,100多张麻将牌,祖父可以画得张张清晰可见。因此就有李万春和蓝月春,两位唱《战马超》十分出名的角儿慕名来找祖父学画。还有一位梅剧团的老人儿——韦三奎,也和祖父交情深厚,两人没事就一起去酒馆喝两盅。黄德华的父亲和梨园子弟的关系也特别好。父亲结婚时为母亲穿的新娘装,能从毛世来(四小名旦)那里借来红裙红袄。父亲酷爱京剧,爱听爱唱爱拉胡琴。他曾特意去杨宝忠(余派老生演员,后专工操琴)家里买了一把胡琴,而恰恰就是这把胡琴,引领着年幼的黄德华走进了京剧这博大精深的艺术之路。父亲先后教了黄德华《二进宫》《火烧博望坡》等经典的小段。他有时候带着儿子去澡堂子洗澡,就叫儿子在澡堂子里唱。黄德华声音甜美,回音在澡堂子里萦绕,来泡澡的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家里来人了,父子俩也要秀上几段,一个秀琴技,一个秀嗓音。
1952年初春,北京艺培戏校成立。学校对于学生的学费分文不收,学校的收入主要来自京剧工会。京剧工会的收入则来自当时京剧艺术家的义演。父亲第一时间把儿子黄德华送到戏校。学生入学前要有一个考试,考官们围成一个半圆,检查考生的素质如何。黄德华考试时唱的是《火烧博望坡》的诸葛亮,但他当时年纪小,只会唱却不知道自己唱的戏叫什么名字。拉胡琴的沈玉秋老师就跟他说,不知道名字没关系,你唱两句让我听听。黄德华张嘴一导板,沈老师的胡琴紧跟着就拉起来了。唱完了,又过来一位老师给黄德华“面试”,扶着小孩儿的脑袋,用大拇指挑起眉毛来看看面相,跟黄德华说:“你乐一个我看看。”黄德华就咧着嘴乐。“再哭一个我瞅瞅。”黄德华纳闷:怎么还叫我哭啊?其实黄德华不知道,老师是考查他的表演能力。而这位老先生就是著名丑角演员罗文奎——黄德华之后学习丑角的启蒙恩师。
黄德华顺顺当当地入学了。之后,每天早上练功、上午学戏、下午上文化课。练基本功的日子有点漫长:拿顶下腰前后桥……苦是苦了点,但黄德华喜欢这个,也不觉得累。不过学校老师很快发现,黄德华生性顽皮淘气,平时上课爱说话逗乐,好抖机灵,这和老生四平八稳、规规矩矩的风格不大相符。正赶上学校学习丑角儿的学生寥寥无几,老师最后决定把黄德华等几个学生送去学习丑行。黄德华转到丑行,发现加上师哥以及之后补充的学员,学丑角的总共才10个人。黄德华心里骤变成数九寒冬:“怎么叫我学这个啊?”他心下好生不乐。好在教他的老师罗文奎先生不仅技艺精湛,而且教学经验丰富,懂得因材施教,知道怎么哄这些孩子。罗先生认为,学丑行的小孩儿淘点、闹点不足为奇,甚至是好事。他在教学上给学生很大的自由,但他也有自己的方法。黄德华老师回忆,当年恩师喜欢冷不丁地抽查学生,上着课突然一拍戒方,跟课堂最闹的学生说:“来,背一遍《棋盘山》我听听。”学生一想词、一背词,精神一集中,再想闹都闹不起来了。
一转眼三个月试学期过去了。北京艺培戏校的新生在中国戏校汇报表演,实际上就让中国戏校的校长、老师看看这些孩子到底成不成;再检查一下北京艺培戏校老师的教学成绩。黄德华演的是《铁弓缘》四个小院子(家丁)之一,虽然台词没几句,都是接人的下茬儿,其实整出戏的四个小院子和石文都得会。这是黄德华人生第一次登台表演,对于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来说,他面临的挑战非同小可——如果演得不好,他的京剧艺术生涯会就此拉吹。好在黄德华天生就是戏里的虫,他登台毫不怯场,机灵劲儿眼力见儿都有——真应了马连良先生的那句话——“台上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黄德华的表演得到了老师的认可,他的丑角艺术之路就此打开。1953年,黄德华接到学校给的任务,为天桥剧场建设的工人出演《黄金台》的侯栾。演《黄金台》侯栾最大的难点在于上台后有一段很长的数板(类似曲艺的快板书)。演员说的时候不能快、不能慢,一定得跟上数板的节奏。这要求演员必须对这连篇的台词烂熟于心。黄德华为了演好这段数板,一闲下来就周而复始地背。老师罗文奎也费尽心血,看着心爱的弟子背词,看着排练、看着化妆……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演出最后大获成功,黄德华清脆悦耳的一段数板,余音绕梁,赢得观众热烈掌声。黄老师告诉我:“虽然丑角以做工和念工为主,但绝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就拿这个侯栾来说,搧扇子不可能像生活中那样。台上搧出来要美,到底该怎么搧?10岁的孩子不可能知道,全靠罗先生手把手教啊。”
“演员的成长分两类。一类像李万春先生,一出来就是角儿,学的就是领衔主演。”黄老师用手比划着,“我属于第二类演员,一步一个脚印,有那么一个清晰的成长过程。”1954年9月12日,黄德华迎来学戏生涯的第二次考验,参加一场学校正式售票的演出。一出《女起解》40多分钟,全凭两个人一唱一说。不过黄德华演戏里的崇公道时,游刃有余。只是他无意间睃了一眼台下,竟然发现第一排坐着的父亲。黄德华心中一紧,父亲怎么没打招呼买票兀自来了?黄德华心里琢磨,这么多年,父亲倾尽全力支持自己的京剧事业,他也许今天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孩子演得怎么样,送进学校后是不是学有所成?儿子明白父亲的心意,自然演得更加有板有眼。可黄德华没想到,一个演出事故正如影随形地悄然逼近——此时,崇公道身后背的包袱皮儿压着的公文纸袋摇摇欲坠,眼看就要掉地上了。台下的父亲为儿子捏一把汗,他趁与儿子眼锋相交的一刹那,用手使劲指了几下自己的后背,黄德华旋即明白其中的含义。但见台上的崇公道,很自然地把背后的公文往上托了一下,借着整理胡子的动作,再把包袱皮系在胸前的扣紧了一紧。两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避免了各种倒好的出现。
黄德华入学三四年后,他和师兄弟们相继进入了青春期,到了变嗓子的阶段。老师告诉他们“子弟无音,客无本”,一定要保持嗓子的状态,在倒仓(变声)阶段,一定要注意嗓子的保护和锻炼。为了保住自己的戏碗,黄德华天天摸着黑起床,因为怕搅了别人的觉,所以他到学校墙根练嗓子,先等起床铃响。待这起床铃一响,校园紧跟着就飘荡起“咿——啊——”练嗓子的声音。黄老师说,他学戏的时候觉得自己天资并不优秀,始终把勤奋装在心里,在学校7年半,一直是以勤奋力补天资。
演戏,在实践中悄然成长
1959年7月,黄德华毕业后到梅兰芳剧团报到。剧团给他8月1日和2日各派了一场戏,分别是《白水滩》和《乌盆记》。黄德华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乌盆记》不用说,是一场文丑戏,可头天给派的《白水滩》是一场武丑戏啊。甭说,这肯定是派戏的人想考验一下黄德华。黄德华琢磨,他必须得应,他不能让人说北京艺培戏校毕业的学生刚报到就让人“闷”回来。好在黄德华是有这个金刚钻的,他在学校虽然学的是文丑,可私下里也没少偷着练武戏,一没事儿就夹着练功鞋去草地和刨花地(用刨子挫木头留下的木屑)里翻跟头。因此从学校到社会这一关,黄德华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此后,黄德华在梅剧团生活和工作,发现这里的成长环境无与伦比。首先剧团的丑角老师众多,像李庆山、薛永德、罗小奎经常带着黄德华在梅兰芳、刘连荣、姜妙香的《霸王别姬》戏里扮演四个更夫,四个丑角三老一少,经常一起合演《凤还巢》《四郎探母》等戏。老艺术家带着年轻演员演出,艺术不知不觉地往下传承;其次,剧团一个演员一个月最少演24场戏,大量的舞台实践丰富了黄德华的演出经验。
1960年4月21日,梅兰芳先生在人民剧场演出《游园惊梦》,萧长华老先生来看戏。在后台,姜凤山老师跟萧老先生说:“先生,咱们这儿新来的学生,明儿有工夫您得给说说。”
萧长华看了看面前这个小伙子,说你唱什么的?
“我唱丑行的。” 黄德华赧然道。
老先生一听道:“哎,那咱们是伙计啊。”
“伙计”这个词,丑角在表演时会经常提到,话外之音就是咱俩是同行。黄德华顿时感到眼前这位80多岁的老人特别地平易近人。他讪讪地说:“那,明儿您给我说说,我……我刚毕业。”
“那有时间上家去吧。”萧长华当面允诺。
自此,黄德华没事就去萧长华老先生家登门请教。
黄老师回忆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4月12日,到萧老家里聆听萧老与姜妙香先生说戏,对《连升店》的戏词,准备电台录音。真是受益匪浅。”
1961年,黄德华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剧团由年轻的演员组成,因此创新能力特别强。剧团排了很多新戏,像《雏凤凌空》《白蛇传》等,让观众耳目一新。1962年,黄德华正式拜孙盛武老师为师,主攻萧派方巾丑。
“用一锅老汤炖出新肉来”
“文革”结束后,传统戏回归,黄德华重拾旧艺。演出有一些因年经月久生疏的地方就向恩师孙盛武请教。孙老师告诉黄德华,演员的水平有两种,一个是理解水平,是指你能把演出的角色理解到什么程度,在理解的基础上,才是你的表演水平。1985年,恩师孙盛武故去,黄德华勤勉上进,又向萧盛萱老师虚心学戏。1995年,梅兰芳剧团恢复建制,仪式在北京饭店举行,其间袁世海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和黄德华说,你是一个很知自强的演员。这是对黄老师艺术生涯的肯定。自此,黄德华与梅葆玖、张学津、叶少兰、谭元寿等经常一起合作演出,并在音配像工程里贡献力量。
对于艺术,黄老师认为关键在于继承和发扬。而京剧的传承,黄老师主张剧团应该像家一样。家里有爷爷、儿子、孙子,剧团也应该老中青,三代俱全——年长的有经验,年轻的有体力,在演出和实践中,艺术自然而然得到传承。所谓用一锅老汤炖出新肉,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的黄德华已退休在家,但他还是经常去京剧院给学生说戏。这两天北京京剧院正在排《画龙点睛》,黄老师又忙碌起来了。黄老师说:“学津(张学津)曾在病床上特意嘱咐我,咱们一块得给学生好好说说。《画龙点睛》作为北京京剧院获得首届文华大奖的经典剧目,把它传下去,我责无旁贷。”
40余年,弹指一挥间。锣鼓点响起,骤时如马蹄踏踏、落英纷纷,疏时若流水潺潺、微风习习。一面板鼓,两片檀板,凝聚了金惠武一生的激情和爱。绚丽多彩的舞台演绎着悲喜人生,其幕后的文武场面亦流淌着无尽的故事。岁月更迭,金惠武对司鼓的体悟也在不断累积和升华。
鼓师金惠武:华美舞台上的幕后英雄
拳拳师徒情
金惠武与京剧结缘,受家庭影响颇深。他的六姨黄咏霓,艺名雪艳琴,曾是一代名伶,享有“四大坤伶”之冠的美誉。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父亲便让金惠武开始学习小锣,由程砚秋剧团的杨老师为其开蒙。
就这样一边上学一边学小锣,从未间断过。1959年,当金惠武14岁时,雪艳琴托北京京剧团李德山先生和著名作曲家陆松龄为介绍人,将他领进了北京京剧团(北京京剧院前身)学习京剧打击乐。北京京剧团实力雄厚、人才济济,汇聚了众多优秀的琴师和鼓师,金惠武便是在这个得天独厚的良好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起来。
“打击乐是由大锣、铙钹、小锣这三样组成的,演奏过程就像说话一样,由鼓师带领,表现大小、上下、软硬、快慢,完成舞台的伴奏。”金惠武解释道。一年小锣,三年铙钹,一年大锣,经过5年的学习和实践,1965年金惠武升到了司鼓的位置。
恩师王和义先生对金惠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令他受益良多、感激终生。王和义文戏为程派青衣李世济司鼓,武戏则为大武生黄元庆司鼓。金惠武非常尊敬老师,每逢老师搬家,金惠武从不惜力。其中,印象最深的细节便是糊顶棚——“纸特别薄,一沾糨子就湿了,绝对不能拿手呼噜。左手一撮,右手拿炕笤帚一扫,一张一张全都给糊好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让老师家能吃到肉,金惠武通过亲戚关系,经常跑到南苑大红门屠宰场,灌上满满两大瓶子酱牛肉原汁给老师送过去。
王和义待他也如亲生孩子一般,教授起来极为用心,金惠武学到了老师的不少私房本领。成语“一板一眼”“有板有眼”均得自京剧中的“鼓板”。司鼓时,右手拿鼓楗子,击打小鼓中的眼心,俗语为“眼”; 而板,就是指鼓师手中的两片檀板。看似简单的“板”,打起来却大有讲究。王和义老师传授的“板范儿”至今仍是金惠武的一大绝活。乐器店老板曾跟他抱怨:“我这儿有上好的紫檀板,来货的时候请您给鉴定了,打得又响又亮又好。可是有的客人来买,打不响这板,说我这板不好。”金惠武笑了,“这便是打小从老师那儿学到的本事啊!尊师爱徒,吃水不忘挖井人,成功不忘老师恩!”
另一位老师杜永发也令金惠武念念不忘,在学习打铙钹期间,金惠武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铙钹的技巧非常多,难度比较大。除了音色问题、技巧问题,身体也必须好,因为演奏时直接震心脏,对本人有很大影响。铙钹的演奏方式有打、搓、揉、挤等。其中最难的就是揉和搓。”杜永发老师当年曾给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名家打铙钹,技巧非常炫目,“揉起铙钹像揉球一样,那么溜,那么好看”。他尽心尽力地将“真能耐”传授给金惠武,“手把手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诸多老师的指点下,金惠武的进步有目共睹,演奏技巧日臻成熟。
为赵燕侠团长司鼓的往事
青年时,金惠武曾立志“要为马谭张裘赵司鼓,北京京剧院所有的主演都要‘打’一圈”,这些理想终究都实现了。从工作之初为李世济老师司鼓,到谭元寿、马长礼、张学津、杨淑蕊、阎桂祥、陈志清、王文祉、谭孝曾、杨少春、叶金援、赵葆秀等艺术家。面对不同的演员,金惠武格外强调司鼓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遇到马派,按‘马’的表演方式打。剧情、人物及演唱的感觉,要求锣鼓快慢起伏、软硬变化,都要准确鲜明地体现出来。这就要学习谭世秀先生的演奏方法,这是捷径。为赵燕侠司鼓,学刘玉泉先生;为杨淑蕊司鼓,就按金瑞林先生的演奏方法……在这个演奏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水平、条件、理解能力,来‘化’,来演变,让他们感到满意。”每场演出结束后,演员跟观众一一谢幕。大幕合拢,演员走到场面上来,说一声:“金子,辛苦了啊!”这一刻,金惠武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其中,与赵燕侠的合作是金惠武司鼓生涯中重要的一笔。60年代初,赵燕侠带领燕鸣京剧团并入北京京剧团,担任副团长并领衔主演。在金惠武眼中,赵燕侠已然是高高在上的大艺术家了。十多年后的偶然一日,赵燕侠突然把金惠武叫到位于西四北二条的家中。一拉开抽屉,大约是十多出戏的录音带,好几十盘。“小金子,拿走,好好听。我跟李慕良老师商量,看中你了,好好听听,好好作准备,不定什么时候让你打。”金惠武受宠若惊,这可是平素想都不敢想的美事。
机会不期而至。80年代初,赵燕侠在全国率先实行体制改革,在北京京剧院一团组织了部分演员和乐队,金惠武也在其中。当年,演出的票价定为2元,而全国同时期最高的票价也没有超过1.2元的。尽管如此,演出票提前一星期售罄,场场爆满,有的城市甚至需要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
1981年,巡演到了武汉一站,一天下午,金惠武正在宿舍睡觉,同事把他推醒了,“院长和团长找你。”忐忑不安的金惠武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火急火燎一路跑了过去。“今天晚上演出,赵团长的《白蛇传》你一定要上。刘玉泉老师病了,打不了了。”救场如救火,金惠武急忙要来剧本,一边向刘玉泉老师请教,一边抄写提纲。晚上演出,“脑袋顶着雷就上去了”,尽管有刘玉泉老师在一旁指点,可金惠武一来紧张二来手生,勉勉强强应付下来,给自己打个60分。因为同一出剧目要连演三天,金惠武第二天一大早便起来练习、琢磨,并请刘雪涛老师为自己说戏。三天之后,赵燕侠一句话:“小金子,行。”如此这般,金惠武为赵燕侠司鼓的日子开始了。
“那时候,条件有限,根本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在排练厅里排若干次,全靠平时的努力观察、积累。”金惠武回忆。《白蛇传》有一场武戏叫作《盗仙草》,金惠武先找到武戏指导老师请教一番,心中有了轮廓。演出前,金惠武来到赵燕侠的化妆室:“赵团长,您再给我说说《盗仙草》中您的具体动作。”赵燕侠正对着镜子画脸,一回头,“小金子,你好好看着啊!”说罢,拿着画笔,比划若干回合,亮相。“会了吧?”金惠武也不敢说不会,下来赶快请指导老师到台上示范几遍。“晚上至少要打到8成对。”
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为赵燕侠率团体制改革作了专访,金惠武清楚地记着上面有这样一句话:青年鼓师金惠武通过实践,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得到如此肯定和承认,金惠武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司鼓,一生的学问
“司鼓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鼓这个行当,需要学到老,练到老,舞台伴奏司鼓46年,不断接触新剧目,不断跟新演员合作。每个人的表演方式、舞台的节奏感觉、派别都不一样。鼓呢,总是两根鼓楗子一块板,完成伴奏。而合拍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金惠武总结道。
“鼓”作为打击乐,跟琴师比较有很大限制。琴师的演奏技巧越好越能感动人,通过不同的西皮二黄乐曲,演奏不同的唱腔过门,让观众直接得到音乐的享受。而鼓是单声乐器,通过单手、双手不同的点儿,用不同的演奏技巧来完成与其他乐器的合作。因此,鼓的敏感性、灵活性、适应性要强。在多年反复的研习中,金惠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我带领打击乐有三项要求,京剧中打击乐必不可少,一要齐,二要好,三要美。把打击乐的弹性打出来,根据剧情的需要,灵活掌握,强弱适当,不吵不闹。扭转枯燥的感觉。我常常跟学生说,司鼓过程中要动脑子,不要傻使劲,只有把演奏技巧化为伴奏技术,才是最终的目的。”金惠武真心实意、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与心得传授给青年人,可以说,北京京剧院大部分青年鼓师和打击乐手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指导。
关于司鼓,金惠武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站立起来,要有筋骨、有血有肉。京剧音乐,也就是文武场,以鼓师为首的打击乐,相似于人的筋和骨;以琴师为首的弦乐,相似于人的血和肉。只有血肉没有筋骨,人是瘫软的;只有筋骨没有血肉,人是空洞的。缺一不可。
在与知名演员的合作中,金惠武始终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上下求索。“很多同行只跟乐队老师去请教如何演奏,而我常常跟主要演员去探讨。如果把您的舞台经验直接告诉我,鼓是乐队的指挥,演员内在感情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戏曲一方面是戏,一方面是曲,曲是托着戏的。演员来完成戏的表演,音乐来完成演员的包装。我认为演员就是像礼品一样,我带着乐队,就是包装的过程。你越美,我包装得越漂亮,就会达到完美的效果。”
为谭元寿、马长礼等艺术家司鼓的时候,金惠武经常登门拜访。他们亲身给金惠武掰开揉碎了说戏,金惠武认真聆听、整理剧本。回到位于花市的小平房后,他支上鼓,就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将一出戏从头至尾来回研究。不知不觉,夜已深沉。
在创新方面,金惠武也有独到的思索和研究,参加了许多新剧目的创排,从现代京剧《杜鹃山》到大型交响京剧《赤壁》,完成了设计锣鼓的工作。1999年,由北京京剧院编演、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总导演的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一二本开始排演,金惠武被选为创排鼓师。创排当中,导演为金惠武提出要求——锣鼓一定要新,一定要跟剧情贴合。金惠武顶住巨大的压力,打开思路,将鲁剧、现代戏、梆子等元素融入到锣鼓的设计中。甚至连秦腔里的小黑锣及排鼓都使上了,“因为《宰相刘罗锅》是喜剧,非常适合这种表现形式”。该剧推出以来,好评如潮,并荣获了文化部文华大奖,金惠武心中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此外,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形下,金惠武参与设计锣鼓和司鼓的《风雨同仁堂》《画龙点睛》也先后摘得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大奖。
“我一生的司鼓工作取得了小小的成就,离不开领导的关怀和支持,离不开各位艺术家的提携和帮助,离不开我一生合作的三位大琴师——燕守平、王鹤文、李祖铭,我们在艺术方面彼此互补。另外,还有五位恩师是我一生难忘的,中国京剧院的庚金群、王德元,北京京剧院的谭世秀,上海京剧院的张鑫海和中国戏曲学院的阎宝泉。”回顾一生司鼓生涯,金惠武心中充满感激。在北京京剧院建院30周年之际,金惠武获得了院里颁发的突出艺术成就奖,一生司鼓,载誉而归。
鼓师,无疑是京剧舞台上的幕后英雄,但肩负重任。繁花落尽见真淳,金惠武用心用情书写着自己的艺术生活。铿锵有力的鼓点声遥遥响起,每当这一刻,金惠武便会浑然忘我。一面板鼓、一副檀板,简单至极、朴素至极,却令他魂牵梦系。
(编辑 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