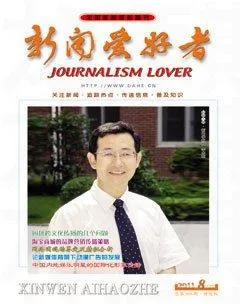《复活》中主人公精神复活的艺术
细致的心理描写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复活》的一大特点,小说通过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细致具体自我矛盾的心理戏剧性的演变、描写,艺术地展现了男女主人公的精神死而复生的艰难曲折过程。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的灵光如两道起伏跌宕的股指曲线,牵动着读者的心弦,这种表现方法,不仅强化了主题,强而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俄国当时的各种社会制度,形象地反映了贵族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也使小说更具特立独行的艺术魅力。
聂赫留朵夫的复活透视——上帝就在我心中
小说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是莫斯科地方法院的陪审员。一次他参加审理两个旅店侍役假手一个妓女谋财害命的案件。不料,从妓女玛丝洛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认出原来她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于是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聂赫留朵夫眼前: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他善良,热情,充满理想,热衷于西方进步思想,并爱上了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玛丝洛娃。他们一起玩耍谈天,感情纯洁无瑕。三年后,聂赫留朵夫大学毕业,进了近卫军团,路过姑妈庄园,再次见到了玛丝洛娃。在复活节的庄严气氛中,他看着身穿雪白连衣裙的玛丝洛娃的苗条身材,她那泛起红晕的脸蛋和那双略带斜眼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次体验了纯洁的爱情之乐。但是,这以后,世俗观念和情欲占了上风,在临行前他占有了玛丝洛娃,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
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怕被玛丝洛娃认出当场出丑,内心非常紧张,思绪纷乱,感情复杂,怜悯中感到羞愧,厌恶中怕被揭发,逃避不能,承认不敢,又是烦躁,又是担心。这一系列惟妙惟肖的情绪纠结和变化,都是通过出神入化的心理描写来完成的。这发人深省的、深刻的审判在聂赫留朵夫的心灵中不间断地进行着。他逐渐感到他是造成玛丝洛娃不幸的第一个罪人。“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
托尔斯泰写到此,并没有停下来挖掘聂赫留朵夫的心灵世界,他更握紧了手中的笔,把敏锐的视觉透视到了聂赫留朵夫的心灵深处最阴暗的地方。犀利的笔触,触到了聂赫留朵夫心里最脆弱、最敏感、最不敢碰触的地方,也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叛逆腥味的文明贵族的那一点善良和柔软。正是这一善良和柔软,使聂赫留朵夫回到家中后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聂赫留朵夫怀着复杂激动的心情按约去米西(被认为是他的未婚妻)家赴宴。本来这里的豪华气派和高雅氛围常常使他感到安逸舒适,但今天他仿佛看透了每个人的本质,觉得样样可厌:柯尔查庚将军粗鲁得意;米西急于嫁人;公爵夫人装腔作势。他借故提前辞别。他发现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母亲生前的行为;他和贵族长妻子的暧昧关系;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这一切都是在对玛丝洛娃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第二天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东西,辞退仆役,搬出这座大房子。这样的转变对一个出身贵族血统从小到大都养尊处优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心灵世界的惊天大逆转。
聂赫留朵夫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法官、陪审员也都心不在焉,空发议论,结果错判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等聂赫留朵夫搞清楚他们失职造成的后果,看到玛丝洛娃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律师告诉他应该上诉。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分散土地,奔走于彼得堡上层,结果上诉仍被驳回,他只好向皇帝请愿,立即回莫斯科准备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途中玛丝洛娃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为了他的幸福,同意与尊重她体贴她的西蒙松结合。聂赫留朵夫也从《圣经》中得到“人类应该相亲相爱,不可仇视”的启示。
人性的善恶是同时存在的,聂赫留朵夫起初是一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在部队他染上许多恶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把她抛弃。十年以后,他作为陪审员在审理案子时,认出了自己侮辱过的女子玛丝洛娃,这时候“精神的人”觉醒了并占了上风,使聂赫留朵夫想为自己赎罪。上帝在他心中复活。
原文是这样描写的:“他做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清除他身上的一切的污垢。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存在于他心中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觉醒了。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趣,而且感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他都能做到。”上帝在心中的复活,让人有了精神的归宿。聂赫留朵夫为自己灵魂里的变化而不断欢呼:“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