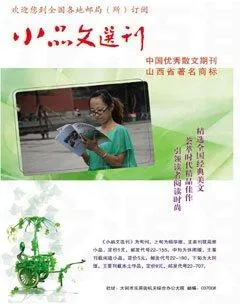幸福而美好的记忆
很多东西只有在回忆的时候,才知道拥有是最幸福、最美好的。当你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看大浪淘沙,看水天一色,那些记忆中最幸福、最美好的东西就会像浪花一样跳跃在眼前。
1978年,是个极其普通的年份,但对我这个山里娃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我迈出了人生旅途中极其重要的一步。而这一步,却是决定我一生前程、命运最光彩的一个拐点。
那一年,已经当了民办教师的我参加高考,又荣幸走进大学校门,成了当时很为人羡慕的大学生。虽说我们是后来被补录的,录取通知书接得迟了点儿,但毕竟圆了大学梦。这在当时我们这些山里娃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清楚地记得,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不只是我家,就是我们村,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我是全村第一个恢复了高考后通过高考择优录取的大学生。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对上大学这光彩事儿,过去我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呀!而那录取通知书,却实实在在送到了我的家里。我的父母反反复复端详着那录取通知书,似乎不相信是真的一样。父亲一生不识几个大字,就让我反反复复念给他听。全家人都乐得合不拢嘴,激动得一夜合不上眼,睡不着觉。村干部还特意提了瓶酒来到我家,与我们共同庆祝了一番。
那年月,我那个家实在太穷了。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和哥哥在地里干活儿,每天早上做上一点儿饭菜,连受苦力的父亲和哥哥都不够吃,我和母亲只能喝点儿稀汤,吃点儿锅巴。逢年过节,为了能吃上顿好饭,父亲可谓绞尽脑汁。尽管父亲东挪西借,但我们每年至多也只能吃上一顿除夕的油糕(隔年糕)、肉馅儿饺子(隔年饺子),还有一顿初五的肉包子,之后就又照旧了。吃的姑且如此,穿的就更不能提了。不怕人笑话,高中毕业前,我都没弄清穿没穿过一件新衣服,从头到脚几乎全是父亲哥哥替换下来或亲戚朋友接济的,且已经补丁压补丁,而那补丁也是兰一块黑一块,让人无精打采,不好意思立在人前。那年参加高考,我虽已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但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年终才结算工钱,家里连我赴县城赶考的钱都拿不出来,是我的班主任黄国鹏老师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资助我,才使我到了县城,进了考场,有了金榜题名的机会。所以,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家里人就又为我上大学的钱发了愁。最终,父亲抹下老脸到亲戚家跑了一天,抓挠回了70元钱,才送我上了求学的路。70元,却是我那个穷家对我三年大学生活的全部投资。我用那钱付了路费,买了上学必备的洗漱用品,此后再没向父母要过钱。因为那年头不像现在,上学期间的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虽说每月只有不足20元生活费,但节俭着花,还是够的。我那时花钱,真的是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的。比方说进城,我大多是走着去,走着回,即便是坐公交,也只坐到离学校不远的十里店村那一站,然后再走回到学校,因为再坐一站到学校就得花一角五,少坐一站就只花一角钱。省上的这五分钱,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可是十分珍贵的钱哪!
大学三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难以忘怀的岁月。感谢所有的恩师,是他们带领我们走进知识的殿堂,赋予了我们最有意义的收获,使我们对事业、对生活如此执着。感谢所有的同学,是他们赐予我包容和理解,使我明白了什么是真诚,什么是真情,什么是纯洁和坦荡。
师生情是一杯醇香的美酒,愈陈愈厚重,愈陈愈绵长。三年间,我们换了很多老师。虽然每一位老师都只带一门课,时间也不长,但都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教现代汉语的刘淳老师治学特别认真,从汉字的发音到语词的运用都有板有眼地教我们,但我这位山里娃自小儿没学过普通话,自小儿说的都是家乡话,所以刘老师怎么教,我都校正不过来,到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了,大家都在使用微机工作了,而我五笔字不会打,用拼音操作也拼不准,整个儿一个“当代文盲”。教我们文学概论的龚协老师、文学创作的李青山老师和外国文学的翟纲绪老师都是高音教学,声音宽厚而宏亮,内容详实而有条理,我们都非常爱上他们的课。听他们讲课不迷糊,不走私,绝对有精神。教古典文学的王穆之老师年岁大了,据说“文革”中受过冲击,至今还没恢复过来,所以记性不好,讲着讲着就不知讲到那儿了,然后就问我们:“讲到哪儿了?”,我们就告诉他,他也很不好意思地跟我们笑一笑。不过,王老师的分析特别有条理,大家还特爱听他的课。还有张瑞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张老师的课备得特充分,特详实,我们也听得特投入。我记得,鲁迅先生有一篇散文《秋夜》,开头一句是“我家门前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这一句话,张老师就给我们整整分析了三个课时,我做笔记做了近二十页。后来的现代文学课由马文忠老师和崔聚才老师给我们带。马老师一生致力于方言研究,在这方面特别有建树,生前及死后还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他给我们讲的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非常有情趣,能将《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三仙姑的形象活生生再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崔老师讲课虽有些照本宣科,但始终讲得特别认真,尽管我们对这样的讲法不感兴趣。不过,他的这份认真劲儿,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大有裨益。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李青山老师。我现在是我们班唯一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的,虽说现在的位置是杂志社总编,但我上学时也只能说是初通文字,根本没想着以后当总编,就是在报刊上发一篇“豆腐块”也会激动十来天,但那时连一个“豆腐块”也发不出来。是李青山老师点燃了我文学创作的火焰,引导我敲响了文学殿堂的大门。李青山老师不仅教我写作技巧,帮我修改文章,还为我的习作《堵不住的路》专门组织了一次作品研讨会,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走文学创作之路的信念。后来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也始终坚守文学创作,从一篇小消息、小通讯写起,最终写出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专著《风情如画》、《白登之战》和学术专著《中国小品文概论》,还两度获得了山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并最终走上了《小品文选刊》总编的领导岗位。近几年,我又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我的大同民俗研究丛书《年俗》、《节俗》、《婚俗》《食俗》,兔年春节,我还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参加了大同广播电视台的《免年春节联欢晚会》。还有张兴华老师,张老师给我们带《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本来很枯燥,但张老师讲得有板有眼,形象生动,竟然使我对政治经济学有了兴趣,以至于一度钻进学校藏书不多的图书馆,找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埋头读了起来。给我们教体育课的贾志东老师非常严谨严肃,我自小儿身单力薄,虽重视体育锻炼,但跑步跑不快,投蓝进不去,做俯卧撑做不了三五个。不过,每次校运会我都会报名,尽管根本取不了名次,但我决不计较这些,也不管人笑话。态度是好,但贾老师铁面无情,连毕业考试也没给我弄个及格。幸亏当时体育不及格还能拿上毕业证,要不然全班因体育成绩不及格毕不了业的肯定有我。还有一位姓潘的老师(原谅我记不得他的全名了),给我们讲心理学,其中讲到条件反射,他三番五次地讲“一拉铃就给狗吃东西”,后来讲的时候,他刚说“一拉铃”,我们就接下说“就给狗吃东西”,紧跟着嘻嘻哈哈大笑起来。
同学情是一曲共鸣的乐章,是人生路上的回首和继续前行的相依。人一生中有许许多多同桌的你,同窗的你,只要不停地学习,同学就会越来越多,但记忆最为深刻的却是大学同学。我们班学生不多,39个,且来自四面八方。有太原的,临汾的,忻州的,还有河南的,但更多的是大同、雁北的。有结婚生了孩子的,还有高中刚毕业乳臭未干的。班里女同学特少,本来有两个,开学三个月又转走了一个,最后就剩下了“一朵花”,后来我们班便被人戏称为“光棍班”。不过,我们这朵班花,虽来自城市,却并不像“骄傲的公主”。她朴实而憨厚,平素也很少说话,那时也就十七八岁,长着一张像洋娃娃一样美丽动人的脸,她的眼睛黑而清澈,眉毛弯弯的像一片柳叶儿飘在清澈的湖上。平素很少笑,一笑,一口雪白的牙齿就露了出来,一颗一颗像晶莹的珍珠,而她的鼻翼在笑的时候轻轻翕动,又像是蝴蝶的翅膀。“物以稀为贵”。全班同学都非常喜爱她,呵护她,还有几个同学暗里明里追求她,至于表白过没有,我不知晓。等到工作了之后才发现花落他家,这朵鲜花被我们低一届的同学给摘去了。我们中文班才子多,我当时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当时经常写东西的有孙裕、徐依武、王玉田、李国计、李奉戬、王志华、白菊生、张力、刘阳、宋忠文、徐志祥、邓纪林等好多同学。学校办了一份校刊《百草园》,编辑、插图、刻蜡板的大多是我们班的,其中,韩正明同学负责刻蜡板、插图。这份校刊在学校很有名气,我还在《百草园》上发表了不少习作,像《一个巴掌拍不响》、《登西岩山》、《老师办公室的灯光》等等。那年,徐依武同学写了首悼念张志新烈士的诗,发表在我们班的后黑板上,我至今印象很深,但记不清写什么了。王志华同学写了好多诗,写出来就朗诵给我们听,但他的家乡味太浓,到毕业时我们都听不懂他说什么。大学三年,同学们都非常关心我,呵护我。费泽民同学是土生土长的大同人,每个星期日都回家,剩余下来的钱票、粮票都接济了我,让我在学校的小日子过得还不赖。郝虎、赵永平同学是从运城地区来了,每次来都拿上一口袋干馍片,但拿到学校就成了公共食品,同学们想吃就吃,一点儿也不拿心。来自大同县的李培涵同学见我的被子一年多了一直无人拆洗,就乘星期天把我的被子拿回家,让他娘给拆洗了,然后再拿回来。如今,我常在闲下来的时候想,虽然我们全班同学来自四面八方,但有幸同在一个教室里,同学习,共成才,真是一种福气。一想起在大学的美好时光,想起与同学们在一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温馨。同学之情如泣如诉,如歌如咏,玉壶冰心。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挖空心思争名夺利的杂念,没有绞尽脑汁谋取私利的浊流。逆境中,同学是一把火,燃烧你的激情,教你屡败屡战,永不放弃;顺境中,同学是一块冰,劝你头脑冷静,宠辱而不惊;风雨中,同学是相携相扶的臂膀,患难同当,休戚与共;阳光里,同学是蓝天飘荡的白云,以诚相待,纯洁透明。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长的老师已经渐渐故去,但同学间那美好的深情厚谊却始终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情感点缀。于是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也罢,就让那幸福而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