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线
2011-12-29 00:00:00
文史月刊 2011年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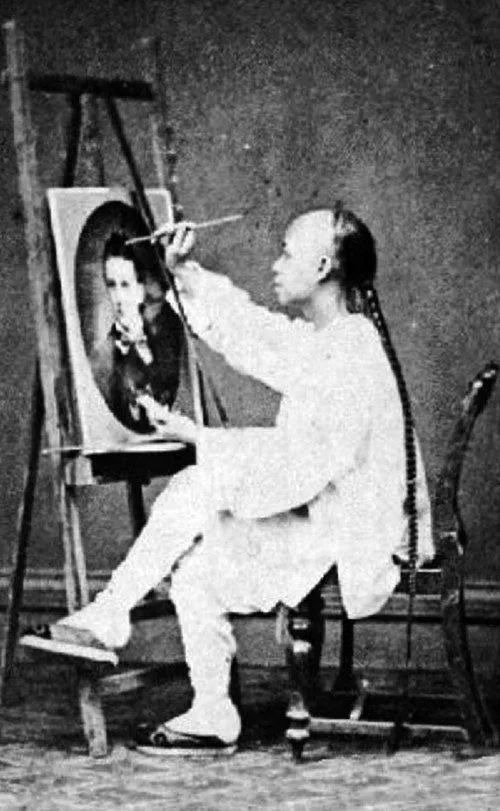
一、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线,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在清朝预备立宪的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
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是晚清权贵,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议题。其实,就算是晚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除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权者的最佳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
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所以,尽管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更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
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独生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甚了了。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二、革命党人不要立宪,他们要的是民主共和制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成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规模比较大的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1908年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以及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在皖浙这次半流产的起义中,安徽巡抚被杀,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惊。1908年和1909年安庆和广州新军起义,成建制的新军发难。各地小规模流产的起义,简直不胜枚举。
这些起义暴动,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预备立宪有关。1905年,由光复会暗杀团精心组织的暗杀五大臣行动,直接就是冲着立宪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迅速实行立宪改革。
三、正是晚清的亲贵,给了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恰是这一系列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即使决策的西太后和光绪死了,接班的满人亲贵,在揽权、收权方面相当积极,但却一点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他们的唯一失策在于,这些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居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立宪,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
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以及资源的控制上。
事实上,在清政府认真推行立宪准备的这段时间里,革命党的起义和暴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知识界和新军的部分人士,对清政府都答应立宪了,革命党还不依不饶坚持暴动相当不解。
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不可谓不卖力,但对清政府的威胁却并不大。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统帅黄兴亲自指挥发动了广州起义,居然一败涂地。
清政府最终雪崩似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
正是晚清的亲贵,给了作为第三者的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