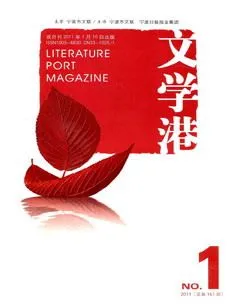以河流的流淌方式进行
《黑暗来临》这本小说集积攒了我四五年时间,换句话说,我四五年来写的小说就这些,我可能再多也写不出来了。这几年来都很稳定,工作生活之余,我每年写五万字左右,多为一万字左右的短篇。我也能感觉得到,这五年来,我在慢慢地入门,然后一点一点地成长,而在这个阶段能把这些并不成熟的作品出版了,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小说走进我的世界是在读高二的时候,我的高中学校不差,但重理科、轻文科,学校有种不好的氛围,认为文科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人才去读的,我事后仔细想了想,这种观念应该源于某些理科老师的灌输。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选择了理科,当时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无论文理科,语文都是公共课,大概理科也能报考大学的中文专业的,一直到高考结束,老师告诉我,理科是不能填报中文专业志愿的。我苦了三年,到填报志愿那天,失望透顶,我还记得爬上公交车回家的时候,我一头靠在椅子上,随车颠簸,仿佛力气一下子从某个地方逃走了,浑身提不起半点劲。
高二那年,也许是学数理化太枯燥了,我找了本小说来看,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后来我想这是我耍了小心思,因为那套书全部是世界文学名著,万一被老师抓到了,我可以讲一个堂皇的理由,哪个老师能否定世界文学名著呢?果然,后来我的班主任看到我在看小说,他敲了敲我的桌子,说看闲书啊?我把封面翻给他看,我敢肯定,他是绝对没有看过这书的,因为他是个上了年纪的数学老师。他拿起那本书,几乎一字一句把封面上的字念了一遍: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然后他愣了很久,最终看着我走开了,这等于是默认了。于是我大模大样地看完了那本《巴黎圣母院》,感到非常的满足。后来又陆续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笑面人》等小说,再后来就是译林出版社其他的文学名著普及系列,它们把我带进了小说的世界。我想这跟高中艰苦的学习生活有一定关系,如果没有每天做不完的试卷,我是体会不到文学的美妙的。
高中读完,没有中文专业,我后来填了微生物专业,上世纪90年代有个响亮的口号: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于是我有了这个选择,去大学报到的时候有点像参军,感觉这是报效国家去的,想一想就热血沸腾。只是很快我对这个专业失去了兴趣,真正接触到“病理学”、“微生物学”这些课程,是非常枯燥的。我们长时间耗在实验室里,分离污水样品、从一排排的试管间添加试剂、做组织培养,或者在油镜下测量那些只有几个微米大小,却长得奇形怪状的微生物,并且一直重复着,我彻底感到了厌烦。大学好就好在有大把的时间,这里你可以对微生物不感兴趣,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来做,这里看小说不再受到老师的监控和打压,你想看多少就看多少。我第一次看到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个文学书库,像见到了亲人。
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是我校友,小小年纪满头白发,我们当时一起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对文学社的事,我们都把它看得比自己专业重要。我们开始聊天,从他的谈话里,我感觉他是一个读了大量小说的人,其实这一点,从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他的头发暴露了他。他跟我说,你应该去迷恋余华。于是我找来了余华的小说,果真迷恋上了他,后来通过余华的介绍,我也迷恋上了卡夫卡、布鲁诺·舒尔茨、福克纳等人。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存在主义的那些伟大作品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也模仿着写了很多荒诞离奇的小说,其中有对疯子的痴迷,我几乎把每个疯子都写成了神明,或者异化的生命。其实后来我才发觉,疯子大多数也在过平常人的生活,他们也渴望爱情,甚至有的也娶妻生子,并且尽自己的能力在帮助自己的孩子。只是我当时被那些“先锋”迷住了,追求形式上跟“先锋”的步调一致,大约这也是一种时髦。
从大学到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寻找小说创作的入门途径,后来逐渐才弄明白,传统写作不能因为读了几本现代主义的作品而被丢弃,其实存在主义放在今天来看,已经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被继承了,我没有理由因为喜欢现代主义的作品,而忽视传统写作,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东西。其实好的作品,不管是什么主义,都是深刻入理,并且震撼人心的。我回过头来发现自己那些编织出来的荒诞故事,其实都是缺乏内在逻辑的,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能量让人信服。就像造一幢楼,根基不扎实,建得越高,就越危险。根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人性,对人性的准确描摹,才是一个小说成功的关键。大概从意识到这些后,我的小说才慢慢开始老实起来。我不排斥故事,因为听故事是人的天性,我发现很多读者看小说其实都在关注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于是,我总努力地把一个故事尽自己的能量把它讲好,当然作为小说作者,故事仅仅是小说的壳,如果一个小说,故事讲完了,什么也没了,这肯定是失败的。小说应该把眼光放在故事的更深处,除了展现小说人物的生存境遇以外,更应该有一种悲悯和宽容的情怀在支撑。所以写《小二》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个被自己亲生父母遗失了几十年的孩子,回不了自己家的感受;在写《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一个被医生判了将要成为瞎子的人的焦虑,尤其是当初为了娶一个能为自己生孩子的妻子,到最后妻子彻底不能生育的时候,他所承受的悲痛。
还有,我觉得写小说不仅要留意生活,留意那些打动你内心的东西,还需要大量的阅读。阅读是最好的老师,我现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阅读,尤其是国外好的作家,比如:奈保尔、保罗·奥斯特、莫拉维亚、麦克·尤恩、艾丽丝·门罗、雷蒙德·卡佛等作家,他们不仅教会了我怎样写小说,还能不断地启发我,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发力了,什么时候又要慢下来了,哪些细节不该被忽略掉等等。
再说说我的故乡,我觉得故乡对我写小说显得尤其重要,虽然我只在那里待了不到二十年,从读高中开始,我就只能偶尔地回到那里,住不了几天,又得离开,我心里充满依恋,却不得不背着行囊远走他乡。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外面生活,也许让我回去,我又会不知所措,准确地说,我习惯了寄宿他乡,而遥望故乡的状态。
我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不是很偏远的乡村,我们村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却被四分五裂地分成四五个小部落,彼此相隔几百米,各自密集地生活在一起。我在村里读的小学,那个学校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民办老师,一年级和二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大家坐成两排,老师上完一年级,再上二年级,我五岁开始上学,在那个学校里读了三年一年级,结果把二年级的课程也全部听会了。老师常常凶我,那时候我觉得这是因为她是上庄人,我是下庄人的缘故。我觉得我们的村太大了,尤其是村口还有那么大一个水库,那个水库,在我年幼时就是一个大海。我后来慢慢地大了,每一次回去,我发觉我的村越来越小了,原来几百米的距离,一个厂房就可以连接在一起了,那个像大海一样的水库原来是一口池塘。只是那些大叔大妈们仍旧跟我小时侯一样,脸上长满皱纹,他们似乎一开始就那么老了,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唯一的变化是他们其中的几个头发白了,或者有的还没等我看出变化,就走了。我每次回去,以前是祖母告诉我谁走了,现在祖母也走了,我母亲接过了她的活,从母亲的话里,我能感觉到这个悄无声息的村子在经历着一些变化,像村口的那棵大树,不断地黄了,又绿了。
回忆像一缕扭曲的烟,总是能带给我各种形状。我离开故乡那么久了,却常常在想那片土地以及那里的人们,它们像一个巨大的宝藏,不时地向我敞开大门,让我从里面拿走一粒玉石或者一串珍珠。
我很多小说都发源于此,通过一个模糊的村庄,我发现了似曾相识的人,这些人也许如今也离开了那里,像我一样到了别的地方谋生,但他身上都带着我们村的烙印,像一股特定的气味,我能从人群中辨认出来。
我始终觉得我是最了解他们的人,就算那些走了的人,我也能从记忆里把他们复活。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就应该代代相传,一个人一辈子的记忆里装满了足够美好的东西,就看你怎么去发现。我有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父亲,他是纯正的农民,他经常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前不久回去,他跟我说起了一个刚过世的人,那个人曾经在文革时做过生产队的队长,但没有文化,文革时一次搞运动,面对整个生产队,他第一次站上大礼堂的讲台,带头喊口号,口号的完整内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他喊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剩下的就忘了,大家知道他是个文盲,料到他喊不完整,就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看苗头不对,就添了两个字“万岁”,结果下面笑疯了。这种鲜活的形象,我觉得是具备流传的品质的,它常常从我父亲的口中被披露出来,他说得是那么随意和自然,仿佛这个人还活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怀念,就像某个潇洒的民族,他们在人死后,生前的亲朋好友都不哭,而是围坐在他的周围,一起谈论这个人生前的种种,比如他喜欢喝酒,喝酒喝醉了喜欢吹牛等等。这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我于是把他们也写进了小说,这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很显然,这种方式的迁徙还在进行之中,我希望他们能都住进我的小说里,并且在那里生活得丰富和精彩。我始终不能离我的故乡太远,我也一直保持着小时候的品性,我觉得如果忘记了自己是谁,可能跟那些底层的人们就远了。我如果能做一个代言人,我也希望发出的是那些人的声音。
我为什么讲到了一条河流的流淌方式?因为前两年,我去过一趟陕西,被黄河源头深深地震撼了,从壶口瀑布那里奔腾而下的黄河一直在广袤的大地上绵延了几千里,最后汇入大海。在飞机上,有时候也能看到某条不知名的河流在大地上冲刷出了蜿蜒曲折的图形,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确实,一条河流的流淌方式决定了它究竟能走多远,同样,一个小说作者对小说的认知也决定了他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走得尽量远一些。■
责编 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