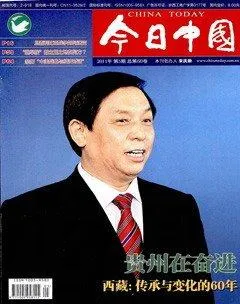“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总量”
媒体把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年轻时用200元台币开米店形容为贫苦,当年的200元真的贫苦吗?日据时代,台湾的铁路便当什么样,有排骨吗?虽然不是学者,但是台湾媒体人陈柔缙在《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里,透过“地毯式”搜寻数据,旁征博引,穿针引线,嗅出日据时代的台湾气味,勾勒出一幅幅日据时代台湾庶民生活史。
有历史作家曾经在电视节目上质问,台湾史只有短短400年,绕来绕去都在同样的题目里打转,有什么好研究之处?陈柔缙可谓“侠女”,以一己之力,所谓“一人考古队”,出八于史料的故纸堆中,纵横古今,详尽展示了台湾这个日本统治将近50年的殖民地生活。
比如世人谈起王永庆创业传奇,无不以他16岁时仅以父亲手中得来的200元,贫寒起家为美谈。陈柔缙比对许多传记和报导中当时的国民所得以及其它企业家创业之资本后告诉我们,实际他父亲资助他的200元,并不是小数字,而相当于一般职业(如警察、教师等)将近一年的薪俸。
虽然得了许多奖,但陈柔缙还是勤跑图书馆,从报纸、史料和访谈中搜集资料,并以通达平实的笔调爬梳日治时期的台湾史,从一本本即将湮灭的《台湾日日新报》旧报堆中,陈柔缙挖掘出很多“宝贝”,有些甚至需要实地走访去核实,颇费人力脑力。陈柔缙的资料挖掘,再现了一段活生生的台湾历史,火车上日式便当的清甜爽口,味精从日本传到台湾后被仿制,这般微小的细节,让人过目不忘。她还特意记了这么一笔,身着制服、操纵电梯的小姐们,成为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当时的少年仔去百货大楼并非热衷购物,而是为了争睹“明星”般的电梯小姐。
其中有一篇《台湾人殉情记》给人印象深刻:无论在日本还是台湾,因爱情受到阻挠,恋人携手赴死者不在少数。当时的殉情“圣地”为台南一条将近3.8公里的运河,运河开通不到四年,就有数十人跳河自杀,后来为防患此类事件,河边多设有路灯,立了一尊地藏王菩萨像。可还是起不到劝退作用,仍有痴男怨女相拥而去。
另有一篇《怪怪小偷和大盗》则令人忍俊不禁。有位嘉义“怪盗”,半夜闯入一栋日武建筑,正与女主人撞个正着,“怪盗”礼貌地提出想借些旅费去满洲,女主人遂将钱和手表送上,怪盗提醒她,若报警需两天后,不然就杀死她。临走还留了张字条给当地警署,上面写道:初到贵地打扰,非常抱歉。
再比如电影《海角七号》里,花边照片、格子西装,却不是当时可能出现的着装。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都难逃陈柔缙的法眼。
当时的这些“社会新闻”看似‘叭卦”,经过时间荡涤及横向纵向的对照,就凸显出历史的价值。在大背景下,台湾沦为殖民地、四百万人沦为异族是国家民族的大悲大恸,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改写几代人的一生。很多影响与变化正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悄然发生——所谓当时的“时尚”。
对于历史的解读,大部分著作都是宏大叙事,充斥着利益集团的争夺,个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然而,陈柔缙认为,“情境和故事才是历史趣味的核心”。她极为赞叹张爱玲所说的,“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在她眼里,“时代不专属于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记忆不能只靠几座古迹和英雄书上的几个人来填充,故事不计大小,都值得流传。谁又能料到哪个故事会在哪个心灵中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