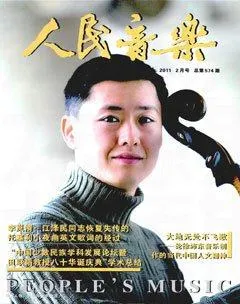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储望华的钢琴创作
1960年到1965年,中国的社会文化、人文环境都发生着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望华本人在此期间的人生经历,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所有这些时代的、个人的变化都在他的钢琴音乐创作中得到了不同形式的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钢琴艺术事业的发展产生着影响。1963年储望华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留校在指挥系担任钢琴伴奏,不久便随校师生先后到北京郊区海淀四季青人民公社及通县刘庄生产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在指挥系任职期间,他接触了不少交响乐、歌剧、大合唱等经典名著;1965年调入钢琴系,专任(中国钢琴作品)教材编写创作工作。
一
据不完全统计,1960至1965年间,储望华创作和改编的钢琴作品有:《江南情景》组曲、《变奏曲》(以上创作于1960年),《筝箫吟》、《隔江相望》、《摇篮曲》、《小白菜》主题变奏曲,《八度练习曲》,《练习曲“风雨归舟”》,与郭志鸿等人合作的钢琴协奏曲《蝶恋花》(以上创作于1961年),《解放区的天》(1963年)、《翻身的日子》,与殷承宗合作的双钢琴《农村新歌》(以上创作于1964年),《日夜想念毛主席》、《歌唱咱的公社好》、《越南组曲》(与郭志鸿、殷承宗合作),钢琴叙事曲《贫农弟兄吕传良》(以上创作于1965年)。
1960年,19岁的储望华可谓是“风华正茂”,他的钢琴演奏专业,在导师易开基教授指点之下,步入了艺术、技术全面提高的阶段。同时,他又一头扎进图书馆、唱片室、音乐会,潜心研修作曲,去阅读、聆听有关作曲方面的任何可能得到的资源。这是一个独特的学习过程,由于出身不好,储望华没能接受正规、系统的作曲理论技术课程的教育,只能采取这种自学的方式。这对于既有作曲才能又有较好钢琴基础的储望华来说,是不公平的和深为遗憾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当时这一切。如果想要改变历史及命运的安排,只有储望华本人,通过他巨大的努力,执着的理想与信念,以及勤奋好学善学善行的实践,用他自己的头脑心灵双手,去挖掘探索追求,在钢琴上发出他要说给这个社会和民众的心声。
1958年未能进入作曲系,1960年起储望华在钢琴系利用课余的时间学习写作。若干年中唯有的一次,是比他年长的作曲系同学关迺忠对他有过一次指点帮助。所幸他初试牛刀,钢琴处女作《江南情景》组曲及《变奏曲》被推荐到了文化部召开的“全国高等音乐院校教材会议”上,不久交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各地音乐院校钢琴系(科)教学中广泛使用及演奏。一时间,一位青年“业余作曲家”,一个尚是二十来岁的在校生,便在业内声名鹊起。试想,如果储望华进入了作曲系,和其他学生一样攻读作曲“四大件”,不是去专门从事钢琴作曲,他日后乃至一生的音乐创作道路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二
从上述列举的储望华钢琴作品中,读者们不难发现两个有趣的、却是引人深思的现象:
(一)60年代初期,原创作品多,改编作品少。
和一切作曲家一样,储望华深谙“作曲作曲,创作乐曲也”。原创的重要,其意义不仅对于一个作曲家,也对其所投身的领域(钢琴、器乐、声乐、交响乐等等)最终业绩的成败得失至关重要,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谓原创或创作,并不排斥从传统和民间汲取养料;恰恰是在继承传统、汲收民族民间素材营养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逐渐不断地创作出新鲜的艺术作品。我们看出他在1961年以前的全部作品,以《筝箫吟》为代表,是创作的,属原创作品,其中有对西方钢琴艺术的借鉴,又和中国民族民间及传统文化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储望华的作曲起步于此是值得关注的。即使在一年前发表的《江南情景》、《变奏曲》,前者取用了他本人1957年夏天到江苏江阴地区所搜集的原生态民歌作为素材,在成曲方面,素材的筛选、组合、发展、对比,以及和声、织体、结构等手法方面,已不是停留在改编、编曲的层面上;后者虽沿用了他人的主题,但放手发展引申,作为变奏,已是一首创作型而不是改编型作品。这里,储望华沿袭和继承了很多欧洲作曲家进行音乐创作的一贯手法,即仰仗民间,且有出新和发展。
从上述60年代初期储望华所创作的钢琴作品中,我们听到虽然是比较微弱、尚欠成熟但真挚动情的心声——个性化的旋律主题、特有的和声、织体等音乐语汇,初步形成了储望华早期钢琴作品的个人特性。
其实,从1950年代中期,储望华主修专业从钢琴转为理论作曲的那一天起,他的心里就不知道“改编”这一说。他弹过的钢琴曲——巴赫、克列门蒂、车尔尼、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哪一首不是“作曲”,就算是中国钢琴作品,丁善德、贺绿汀、廖胜京、汪立三……,又哪一首不是“作曲”(虽然其中不乏用民歌作为素材)。“改编”,在那个年代还真不风行。储望华真正的“处女作”是一首二胡独奏曲《村歌》,发表(公演)于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这也是一首彻头彻尾的原创作品,并且在这之后,他的十余件不成熟的习作,如木管五重奏、长笛独奏、钢琴独奏《序曲》、二胡独奏《欢中愁》等,都清一色为自创旋律——他从来未曾想过用什么“改编”这一招来“作曲”。
但是在1963年之后的若干年中,愈来愈多的“改编”曲出现在储望华名下,久而久之,储望华的钢琴曲便似乎与“改编”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储望华逐渐偏离了他自己在60年代初的创作轨迹。对此,本文下面将专门探讨。
(二)在60年代初期,作品题材广泛,立意自由,思想内容上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的政治面貌。
仅从作品的标题,即可窥得储望华钢琴曲其内容题材之端倪:《江南情景》、《筝箫吟》、《隔江相望》、《摇篮曲》、《小白菜》、《练习曲“风雨归舟”》、《变奏曲》等等,乐曲的基本音调旋律风格明朗向上,乐观积极,绝无政治性的意味。
在这时,储望华以“学习、尝试、探索”这六个字作为自己创作的原则,不随大流不跟风。他初生牛犊,无人为师,单干独打,“小打小闹”,从短小结构的乐曲入手,在60年代初期这几年当中,“组曲”“变奏曲”“前奏曲”“练习曲”等形式和体裁,成为储望华钢琴创作的主要方面。但是,这些短小的乐曲,却反映和表达了当时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的人文情怀、内心理念、艺术趣味,从这些作品的感情和内容中,凸显了一位青年作曲家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的民族风格的探索和追求。
大环境在不断的变化中,社会上愈来愈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些有悖于此的文艺创作思想和艺术作品,动辄被上纲到是“资产阶级”的,遭受批判。中央领导人号召音乐作品要“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从此,“三化”成了音乐界高举的旗帜和创作准则。对于“大右派”出身的储望华来说,他所肩负的沉重的家庭包袱和压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963年秋天,刚从大学毕业的储望华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他于1963年和1964年连续改编了两首钢琴独奏曲——《解放区的天》和《翻身的日子》。这两首乐曲,是响应“三化”之作,也是“三化”的典型产物。耐人寻味的,正是这两首钢琴“改编曲”,使他在普通老百姓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它们迄今仍是在中国久演不衰和深受演奏家及听众欢迎的曲子之一。而在1999年,储望华自己却写道:“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冲涤,面对那些粗糙的、幼稚的东西,竟不禁令我汗颜!《翻身的日子》和《解放区的天》这一对‘姊妹篇’至今有人仍然沿用,在此我对演奏家及听众的厚爱表示谢意!……在我自己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又到了国外进修专业作曲多年后,从思想到艺术上稍微成熟了一些,再来看这两首钢琴独奏曲,虽然觉得十分幼稚,肤浅,但它们毕竟也是自己曾经走过的一段路矣!”(见《钢琴艺术》1999年第3期)
对储望华来说,这是他人生道路、特别是艺术创作生涯的一个“急转弯”!当时,连上海女钢琴家顾圣婴的演奏曲目中也加入了《解放区的天》,这一切只能说明,在那个年代和环境中,任何人不可能超脱、回避政治,你别无选择。对于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只有在自己的业务理想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谋求一个生存点、平衡点、发展点。
此后,在储望华的创作改编艺术实践中,不少题材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密切相关。储望华的钢琴艺术,就在这样的大气候、大背景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变革。
三
改编《翻身的日子》的成功以及他的同行、同学殷承宗等人对这首乐曲的推崇,让储望华不得不深入思考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这一切又将何去何从?他终于意识到,捕捉听众的“喜闻乐”之情,迸发出民族之声,是成功的根本。储望华找到了自己钢琴音乐的“知音”,而这些“知音”并不是以前在学院内几个同有此好的志士仁人,或者是一些亲近的、志趣相投的“哥们儿”。这些可都是些寻常的老百姓们啊!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以前熟悉过钢琴音乐?
为着让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听懂钢琴、喜欢钢琴,在1961年到1962年期间,作为钢琴系学生的储望华,率先提出号召并邀集组织了一些钢琴系的同学,不辞辛苦地抬了几架钢琴,自发轮流到北京首都、中央电影院,在每场电影放映之前观众入场的空隙间隔时间里,给电影观众们“送货上门”地义务演奏钢琴作品。如此用心良苦,只为让中国的听众们听懂钢琴,喜欢钢琴。在钢琴已经相当普及的今天,钢琴音乐在中国青少年中有着成千上万的听众。可是在1960年代初期,广大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文化和物质都极度贫乏,要想在中国打开钢琴艺术听众的市场,其难度有多么艰巨,不是过来人,很难体味其中每一步之艰辛滋味!
接踵而至的是1965年的《农村新歌》组曲(此曲原名《社教运动搞的好》,后经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建议,易名为《农村新歌》)。这是储望华和殷承宗首度正式成功的合作。双钢琴的形式,几首清新活跃激动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四清”之后中国农村的“新面貌、新气氛”,乐曲还加上了朗诵、表演、打击乐。殷、储合作协调密切,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了很好的搭档。殷任第一钢琴,边弹边唱;储任第二钢琴。连当时钢琴系的青年教师鲍蕙荞、潘一飞等都登台助阵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周恩来听此曲后说“这是我第一次听钢琴受到了教育”。这固然是对作品成功的鼓励,也再三强调了搞“三化”,乃是钢琴音乐在中国的唯一出路。饶有趣味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这首《农村新歌》改编的42年之后,以郭品文为首的一班香港青年钢琴家在香港舞台上演奏《农村新歌》,受到了香港听众的热烈欢迎。该曲作为压轴曲目在200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正式庆典音乐会上奏响,欢庆回归!其情其意,早已大大超乎于1965年创作《农村新歌》者的初衷!可见,成功、优秀的艺术作品,远远超脱于意识形态的樊篱和预想。
有了《翻身的日子》等乐曲艺术实践的尝试;有了和殷承宗《农村新歌》的成功合作,使储望华的人气渐升,在业内有了一定影响,也使他和殷承宗等人在“文革”前夜有了共同的“钢琴革命”的语言和志向。这一切,为了日后(1969—1970年)储望华有机会参加《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全部创作过程,做了思想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使他能成为《黄河》创作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主力。
另一位在60年代初期和储望华钢琴创作有关联的人物是郭志鸿。在这六年期间,他们之间是三年师生关系,三年同事关系。储望华在当学生时,弹过郭志鸿的《喜相逢》、《春到公社》等作品,从中学习受益。他十分景仰郭先生的才气,欣赏他在钢琴和声、节奏等手法中的鲜明个性和大胆尝试。1961年,郭老师邀集储望华等同学,一起创作了钢琴合唱交响诗《蝶恋花》,由殷承宗钢琴独奏,刘秉义领唱,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队和合唱队演奏演唱,黄飞立指挥,在北京、天津成功公演。1965年,郭志鸿、储望华、殷承宗三人又一起合作创作了钢琴独奏《越南组曲》。
在这些岁月中,作为储望华的主科老师,系主任易开基教授始终鼎力支持储望华在课余从事创作活动。正是他,于1961年向参加文化部教材会议的全国各地音乐院校同仁们介绍了储望华的钢琴作品。钢琴教研室正、副主任朱工一和周广仁两位教授,多年来也一直爱护鼓励储望华的钢琴创作。而作为政治领导的钢琴系党支部书记崔静媛以及院长兼党委书记1GcJETe+4zlM8JXpQKUO7A==赵沨,更是本着扶持爱护人才,发展中国钢琴音乐事业的宏大目标,对储望华关爱培育。如果没有赵沨的果断,储望华1958年不仅难入学钢琴系深造,1963年毕业也不可能留校工作。
1965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了“政治部”,进一步强化和加紧在学生中“大抓政治思想教育”,“大学解放军”。储望华在这年改编了一首“钢琴诗朗诵”叙事曲《贫农弟兄吕传良》,演出效果不错,有一定的感染力。院政治部王主任表扬储望华说:“这一首钢琴曲很有教育意义”。当时,让钢琴发挥教化功能是钢琴作曲家不可推卸的职责,中国钢琴创作的方向、方式以及内容、题材,正在沿着一个业已形成的政治格局和方向前进。到了1965年底,即使有人对这个方向迷惘不清,或不能认同,但十分严峻的形势和生活,已经出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学钢琴的人难找出路;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被发配去干“打幻灯”的杂活。1963年,储望华同届的钢琴系学生中,有好几位已经“改行”当了电工或营业员,“亡琴论”之说,不绝于耳……中国钢琴音乐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究竟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热爱钢琴艺术的人都在思考和观望的问题。
带着这一个历史的问号,时代的列车便一声长啸,急匆匆地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开始了一个历史的新进程。
四
60年代初期,储望华所“创作”的钢琴曲流传于一部分音乐院校的琴房课堂之中,作为“中国作品教材”,它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教学。但是在浩如烟海的欧洲钢琴文献面前,和包括这些作品在内的中国钢琴教材只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其真正的教学作用、学术意义和艺术品质,因为其本身的不成熟、缺乏艺术的深度和分量、发挥钢琴高级技巧的不足等原因,实在是在整个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效果等方面都显得有些稚嫩疏弱、微不足道。它们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和以后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是“中国的”,是钢琴文献中的第一批“MADE IN CHINA”,是以贺绿汀《牧童短笛》为标志的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所走过道路的沿续、传承和发展。
这种薪火相传的光芒仍然微弱……
就自己的创作或改编而言,储望华深知其水平不高,更遑论与那些欧洲经典名作相提并论。“可是,总得有人去做吧!”“中国钢琴音乐之路,是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出来的”,他总是这么说。而他自己却更愿意把这一切看成是,为了将来中国钢琴艺术大厦建造中的一撮土、一块砖。
储望华从专注“作曲”,到热衷“改编”;从题材的“非政治化”,到内容的“泛政治化”,在艺术上,这是进步还是倒退;在储望华的人生道路上,这一切是偶然还是必然,固然是见仁见智,但这所有的思考和评估,判断其是非得失,都不能离开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
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钢琴文化环境,没有听众和市场,没有整体意义上的、成熟的“中国钢琴作品”。这一点,和同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有着天壤之别。储望华在初始创作钢琴乐曲时,着眼和兴趣所在是追求一种“小我”中的气氛、情趣和声音,表现“自己的想法”和对于生活的“自我感受”,并没有更多地想到听众。换句话说,多少人能听懂他的这些音乐,这并不是他所主要关注的。随着他的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他经常到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去演出(如国棉二厂、顺义怀柔农村、西单茶馆等等),他独奏的钢琴曲目包括了《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火祭舞》《马刀舞》等等,他觉得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喜欢看“热闹”的。他开始一点点地去尝试和开拓新的曲目,并逐步熟悉和理解听众们的爱好,他的创作与演奏实践有了某种交结和融合,创作中逐渐注入了“他人的感受”、“民众的想法”和“社会的声音”。比起学生时代,他潜移默化中少了一些清高不凡的君子气味,少了一些在象牙之塔内闭门造车的理想主义情调,少了一些纸上谈兵好高骛远的空谈。生活使他必然经常面对这些朴实可爱的普通听众,想他们之所想,爱他们之所爱,并尽量在钢琴上发出他们的声音,弹些他们喜欢的调,既让他们听得懂,又要加上充分发挥钢琴的技巧特点,要有演出效果,把欧洲古典、浪漫、印象、现代的经典钢琴技巧,尽可能地都吸收融会到一部部“中国作品”中来,让这欧洲的“洋”乐器钢琴,也说说咱们的“中国话”。让大众喜欢听钢琴,使钢琴终将有一天能变成是“他们的”乐器,变成是“中国的”乐器——这是储望华的DREAM(美梦)。他是从文化的、宏观的、战略的、前瞻的历史高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的。
在此之后,“喜闻乐见”便成为储望华创作或改编钢琴作品的核心目标。创作或改编的过程,就是把他多年来学习借鉴欧洲钢琴经典作品的心得,他演出实践的体会,他心中确立的钢琴曲的“可教性”、“可弹性”、“可听性”熔于一炉,体现在每一首乐曲中。他力图每一首新作中,在旋律、和声、织体、节奏、风格、布局、演奏技巧等方面之中,哪怕只有某一个方面的一点点新意和创新。首先是自我的突破,使自己从“人”到“曲”,更多几分“平民化”;并且不间断地探索、追寻,在这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自己。他深知,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些“雪中送炭”之功,是在做“普及”工作,他甘愿做这铺石填砖的工作。储望华以他本人的自身经历、自身特点、自身弱势和自身优势,终于找到了他的自身价值、自身定位、自我追求和自身奋斗的目标……。
1966年以后发生在储望华身上的事情,并不包括在本文叙述的时间点和内容里。我们可以简要地了解一下:在“文革”爆发前的1966年2月,他与刘诗昆、郭志鸿等人去了陕北体验生活搜集民歌;“文革”第一年的8月,他曾被作为“埋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给揪了出来;父亲“失踪”,女友离去;第二年(1967年)夏天,他扛起了手风琴,和学院的一帮师生们到了武汉、成都、天津、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演出。“事业”这一条线,几乎没有停止和中断过,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在沿续,增加了的是社会生活和艺术实践的进一步积累;他又改编了手风琴独奏曲《白毛女》等;也改编了《甘洒热血写春秋》等钢琴独奏曲……
历史选择了《黄河》这群作者(改编);历史注定了这班人的归宿和命运。终于,在1969年,储望华历经磨难、全力以赴、热情饱满、日以继夜地投入了《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组的工作中……。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