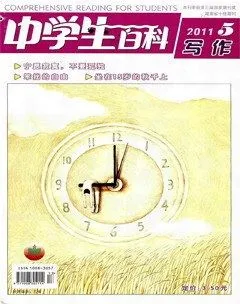像阳光一样寂寞
在樱庭镇的十八年里总有那么些故事无法遗忘,而那些人至今已不知身在何方。也许我可以将他们写下来,纪念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那些萌动的青春与激情。
A
我的高中在樱庭中学,一个不算大的示范中学。它对外号称“创省重点的樱庭中学”,进来后我才知道,那个“创”字代表这所学校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争取成为省重点”的状态。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只能安心地在这所学校混下去。说“混”也不太准确,我没有像个混混一样闲来无事吸烟旷课打架,我只是不务正业——对于理科生来说,看课外书和写小说绝对是不务正业,况且,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事上面。所谓课外书,也并非女生热衷的言情或其他男生喜欢的玄幻,而是很正常的文学作品。当然,对于这所学校,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的处境异常艰难。
我唯一的同盟者就是阿寂。我们在高一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时认识。考试当天,我正为一篇难产的小说苦恼,所以胡乱地做了考卷,然后提前出了考场。
出去之后我依然苦恼,决定出校采风,却又看到门卫异常凶猛的眼神,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学校天台吹风。天台很安静,只有两个人,一个在练街舞,状似抽风,另一个趴在围栏上向外看,似乎是在看着外面的世界,想着未完的故事。
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转过身,看到一个陌生人。他一边说这什么鬼题啊这么难,一边随着校外车子移动的方向转动脑袋,然后说,这车也敢开这路,他不怕把底盘磨没了啊iJruLi4bGXY2ZkLOUyTpPnSKQBN4g15qYVe2yPQ1L0I=?这于我很突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百度搜索软件安装在大脑里来想起此人,以避免现在的尴尬。他也注意到了,挠挠头,尴尬地说,你好像还不认识我,我叫袁寂,叫我阿寂就行了。我看着这个叫“圆寂”的小子,以及那个频频往地上撞的家伙,突然很想笑。
B
上课时老师们总爱说,你们是高中生了,学习要靠自觉,自习课要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我在自习课上奋发图强,争取年内从鲁迅看到余秋雨。后来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文人多,抛开没名气的,著名作家就有几火车:中国人又好以辈分来排次序,要做著名作家,就得写到老,因此作品无数,而真正好的作品却不多。问题在于,书的好坏要一本本看过去;结果是:之前的任务就成了大海捞针。
我捞了一学期,自我感觉颇丰,就开始写稿子,然后投稿。稿子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后来我知道阿寂是个诗人,这让我惊诧无比。他说,其实也没啥,就是看那特别美的散文,然后自行仿造,再把仿造品拆散了随机组合就行了。我说,这样都行啊?他说,那当然,很多人说我的诗好。我说,那倒也是,这说明你找到了诗的真谛。
有一次我看杂志居然看到阿寂的诗,内容就不转述了,免得负文责。诗的后面有他的段话:我觉得写诗就是要认真,要把自己真正融进诗里,让诗成为自己更真实的面,至于那些不懂诗的人,就让他们不懂好了,好的诗是不需要人懂的。
我觉得“是不需要人懂的”太写实了,因为如果有人看懂了,那这个诗人就混不下去了。所幸没有人能看得懂,包括诗人自己。那些吵着“好诗好诗”的人估计就是因为没看明白才叫好:如果明白了,就像知道大名鼎鼎的芦荟或龙舌兰就是油葱样,没有美感了。
为这个事我没少嘲笑他,不过他说,就是闹着玩玩而已,好歹我也进行了深加工啊,比那些直接搬别人的书说是自己作品的人强多了吧。我说,那也是。不过还有更次的,就是自己写了东西,说是名家的,拿到书市去浑水摸鱼,具体情况你逛一下书店就可以了。
C
高一下学期开始的时候天出奇的冷。我搬出了寝室,和阿寂一起租了房子。除了他写诗这事外,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尤其是需要掏钱的时候比较豪放。至于他写的那些诗,我没资格说他,我毕竟只是个发表过一些豆腐块的、俗称“豆腐干文人”的外围人士,而他好歹还小有名气,虽然手法比较低劣。倘若我看不起他,就有些像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话说回来,这中间还差着五十步,那是我的底线。写诗可以投机取巧,是因为写诗的人大多数都在投机取巧,但写文章不行,太容易暴露了。
当初想着住校没什么,后来发现这是个极不明智的决定。所以当阿寂提出合租房子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另一个让我毫不犹豫的原因是,他提出承担三分之二的房租。
搬东西的当天,我发现自己上了这小子的当。他出三分之二的房租是没错,可其中一半的钱是另一个租客出的。在我和那人沟通后,我知道阿寂对他也是这么说的。我暗自感叹这家伙真是不简单,城府估计都扎根马里亚那海沟了。另一个租客暂且叫他“学者”吧,他的名字太大众了,说出来我怕引起公愤。
基本上我们能看到他的时间里他都在看书,那是相当正规的教科书。他架了一副高度数的眼镜。阿寂曾经试图通过亲自实践来搞清楚具体度数,没成功的原因是他刚戴上就莫名其妙地从床上滚下去了。“学者”震惊我们的另一大特点是他的呼噜声。他的呼噜声能与海浪声比分贝,搞得我感觉住在海边。而且他不睡则已,只要倒在床上,立马打呼噜,这很讨厌。以前我总是在梦里看草原,后来就只能梦到大海了。看海的心情和在大海上漂泊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反正也就那么回事,也没怎么计较。其实这和住寝室差别没多大。阿寂搞了个电饭煲,下晚自习后就在锅里煮大杂烩,什么玩意儿他都敢往里扔,让人意外的是煮出来的东西味道都还不错。这导致我和“学者”经常趁他上厕所的空当把锅里的东西扫荡干净。他发现后气得跺脚,然后又往锅里扔东西。我们怀疑他是东北人,因为听说东北人擅长这个。
此外,我搞了些瓶瓶罐罐和花草种子,一个多月后把房子搞出了生气或者说妖气。“学者”从家里拿了吉他来,我们以为这家伙是高手,经他的手在弦上一点拨,我们就明白了,他和吉他生生世世都没可能的。然后我们禁止他碰吉他。不过,我们常常会趁他不在的时候拿来弄一会儿,收获是周围邻居的伴奏:“谁家在装修啊?小声点也不会死吧!”
D
高一下学期的第一次月考后我突然很想转去读文科,没有什么正式的理由,属于脑子一时“烧”了,第二天就“烧”进了文科班。晚上回租房,阿寂看到我,说,你小子脑子有毛病是吧?学得好好的怎么说溜就溜,溜也不打个招呼,好歹我还能给你参谋参谋吧?
我说,你就当我有病吧,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躺下后竟然没有听到熟悉的“海浪”声,一时不习惯,折腾着爬起来。我问阿寂,怎么没看到“学者”,他去哪儿了阿寂说,参加个什么竞赛了,说是拿了奖就能保送个什么大学,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说,那我怎么办啊!没有他的呼噜声我还真睡不着,恨当初没有给他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阿寂转身提起了吉他,我一看他这架势立马冲过去把吉他抢了下来,跟他说,你想死也别拉我陪葬,白天拉都像挖了别人祖坟似的,这半夜三更的你不怕别人扔俩手雷过来啊?
转到文科班后的生活依旧无聊,投出去的稿子像扔在沙漠上的种子,天知道地球发生多大的变化才有机会萌芽。阿寂的诗倒是持续不断地发表,我每次看到他的诗就会猜原材料是谁的文章,竟能够猜得八九不离十。这让我更加相信现在的文学只是表面的景气。
有一天阿寂说,你可以把诗又整回散文嘛,这叫回归自然。我说,算了吧,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况且我现在还没混出名,这么早把名声毁了多不划算。
然后阿寂说,我以前也挺热爱文学的,后来我知道文学不爱我,这没办法,我只好爱稿费。热爱文学的人要么移情别恋要么悲壮殉情,真正幸运的没几个。
我不置可否。其实我不是热爱文学,只是有倾诉欲望而已,无奈编辑们大多不喜欢听我喋喋不休。我很无奈,我觉得写作是个人的事,可编辑们回信说你应该写写光明面歌颂一下嘛。我只好说,不好意思我另投高明吧。可我至今没有投到高明。
E
日子过得像流水,这是阿寂说的。我说日子过得像流水账。我在文科班混得很勉强,估计勉强上个二本,所以我决定继续读下去,毕竟现在也没事干。阿寂说他毕业后绝对不写诗了,受不了文友们的酸话。最没疑问的是“学者”,他已经拿到了保送名额,现在在学校装个样子,时间一到就去南方某个温暖的城市。
我开始为以后的路担心。人就是这样,在时间充裕的时候不会担心以后,能居安思危的只是极少数的人。高中的前两年大家都肆意挥霍时间,想着反正以后时间还长,可这高三冷不丁就要结束了,于是不得不想条退路。我想如果考个二本就去读,再混个三四年,然后混个工作再去混日子;考不上就去打工。总能有条路吧。
阿寂说我没有追求,怎么就没想过当个作家,写字养活自己。我说,你以为我不想啊,可那是天路不是退路。更何况我现在只是个路人甲,只在些杂志上跑过龙套。不过就算有一天成了作家,还是小有名气的,我也不能把写作当作职业,我怕把激情耗空,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
高考前两个月,阿寂在杂志上写了绝笔——不,封笔之作,据他说这首诗真是自己原创的,算是报答文学的,兼和稿费分手。阿寂此后勤奋了不少,后来那本杂志还专门给他做了期告别专题,还说“我们不会将你遗忘,你永远在我们心里”,看得我快要含笑九泉。
考试前几天,我和阿寂约定一起去云南旅游,算是对青春的告别。这个时候“学者”已经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去参观他的大学了。他走的时候把吉他留下了,说想他了就拨弄两下。
考试的时候我所在的考场晕倒了个,另外没什么可说的。以前总是听别人说高考有多恐怖,考完后我发现真正恐怖的是不知道考完后还能做什么,好像这辈子就剩个高考似的。
考完后我在学校发了很久的呆,回到租房,阿寂的行李已经搬走了。他留了张字条:本来想等你回来跟你告别的,现在没时间了。小子你要给我活得好好的啊,要是哪天再碰到你一定试试你的抗击打能力。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先胡乱走走吧。还有,那把吉他留给你独享了,要是真不想活了就拉着玩玩儿。
我自言自语,阿寂你个笨蛋,吉他是拉的吗?
F
我去云南旅游了一趟,一个人。行李之类的被我留在了租房里,房东说九月份之前必须搬出去。路上我想了很多,其实青春就这么样,有的人能活得光芒万丈,有的人始终是灰灰暗暗的。但这些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了,以后的路长得无法估计,谁知道能不能一路开心地走下去。反正拥有过就好了,起码已经够本了。
这一趟我走了很多不是旅游区的地方,一个人背着背包,走在别人的大街小巷。在一个不知道是哪儿的街头,我碰到一个弹吉他的年轻人。他弹得很起劲,然后弦断了,他停下来叹口气,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拦住了他,递给他纸和笔,让他把地址写下来。他疑惑着写了。
第二天我走到了玉龙雪山下,准备了些东西,然后往上爬。由于上山时已是傍晚,就在半山的旅馆住了一夜。半夜睡不着,又爬起来翻书。凌晨时我退了房,背上东西借着微光继续走,走了一会儿停下来准备看日出。
山上的空气还不算稀薄,可是冷,尤其是周围很远都看不到人的时候。一会儿,太阳慢慢从地平线上扎出来,有些刺眼。我掏出手机打算告诉谁我现在在玉龙雪山看日出。手机显示没有信号。
从云南回来,打开租房的瞬间,我错觉自己打开了被封闭很久的时间,就想这房间里的时间一直停留在我离开的时刻。这种感觉令人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悲伤。我把“学者”的吉他寄给了在云南碰见的那个乐手。那些已经快枯死的花花草草被我一一搬到了外面,任其自生自灭。
现在我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写着无法出口只好内销的小说。有些事情早已结束,可另外一些才刚刚开始,一如每日清晨升起的寒冷的寂日。
编辑/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