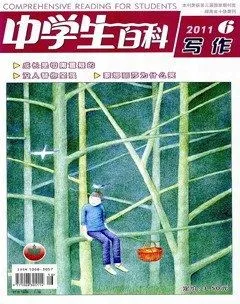黄昏孤灯等故人
我喜欢怀旧,喜欢老上海斑驳的影像,喜欢上个世纪30年代的贴画和旗袍,喜欢午后阳光泛起的唱片音响。那浓郁的复古气息与场面,都免不了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或是一道晦暗的光影。那时光穿梭在转瞬即逝的片断里,蛊惑迷人。
我喜欢那照片里昏暗的灯,带着些过时的颓废、固执的守旧以及自赏似的哀伤气息。我喜欢夜色深重的江面上,渔船里昏黄的灯,丝丝缕缕地透露着渔家生活的简单与安宁,那浓缩的温情时时装点着诗人感性的梦境。如果说照片中的煤油灯,是徐志摩笔下“新月”派必有的道具,而幼时母亲在周庄为我买的烛油灯,却是我曾提着它走过粼粼水乡幽幽深巷的唯一纪念。想象中那个身着旗袍的我,提着灯走在水岸,仿佛就是正去码头接父亲回家的邻家女孩。脚上沾湿的尘土,不小心打扰了小桥流水间的宁静,却全然不知。
我曾一度寻找令我真正向往的那盏灯。那是一种让人怦然心动得顷刻间失神的缘分。然而正像那句诗写的那样:“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看过许多地方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我寻找的路上,一直没有这盏出现在恰当时间的灯。
我没有再次为刻意寻找而踏上旅程。与之相反,我回到了故乡。我不想再寻找那盏灯,那抽象意义上的名词根本概括不了我的整个梦想与人生。
我回到父亲三十年前成长的地方。几经颠簸与周折,我们终于在黄昏时分踏上了故土,也许是这种热爱在作祟,我对黄昏时分的故乡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
几天前的大雨,使这通往家乡的路,变得泥泞不堪。迟到几小时回家,父亲有些烦躁,有些急切不安。公路旁这次没有爷爷的身影——我们没有事先通知他。他这会儿应该正和奶奶在吃饭吧。我们不想打扰他们。我们一路说着旧事,一路迎着飞速更换的夜幕,向家的方向驶去。
我们终于到达了家门口的院坝石坎下,用剥落的石块砌成的石阶,已经长出了青苔——家里只有两位老人,走的人大概很少吧。抬起头的瞬间我看见了家门,看见了那盏灯,橘黄色的灯光从门缝和窗户里透出,暖暖地把周遭的夜色晕染得温馨起来,家的轮廓模糊在弥漫着炊烟的夜色里,所有的故乡情结都浓缩在那盏灯光里。此刻我渴望的心,仿佛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睡梦中见到的美丽房子
般温暖。在冗长的寻找之后,蓦然回首,在离我的心最近的地方,我见到了那盏让我心灵湿润的灯光,原来它来自亲情最浓的家。
家里的门虚掩着,不时传出碗碟碰撞的声音,那声音伴着夜幕下各种生灵的低吟浅唱,更增添了乡村的安宁,如一曲人与自然和谐的小夜曲。
我终于看到了梦寐已久的那盏灯。我惊诧于黄昏下的孤灯竟没有想象中的悲伤与颓废,而是呈现出一种祥和与平静。我终于明白,灯还是一样的灯,那样的氛围,却是因灯下的人有颗祥和平常的心。所有的疑惑都消失在我抬头的那一瞬间。
门缝渐渐变大了,我看见了爷爷和奶奶两人对坐在堂屋间,说着话,吃着饭。显然对我们的到来,他们还没有察觉,我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惊喜,我突然感到鼻子一阵发酸。门没有关紧,仿佛在等着什么。
我走近寻找已久的灯光,泪已打湿了眼角。我知道推开门的我,笑容一定会很甜。
编辑/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