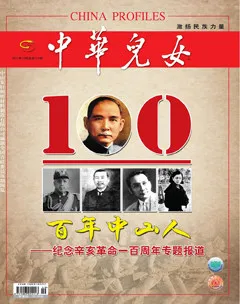“个人”发现需要文化重建
2011-12-29 00:00:00单士兵
中华儿女 2011年19期

经常会听到一种感叹,叫“人生苦短”。人生苦不苦,每个人体验不一样。但是,百年人生,只能在有限时间中生活,确很短暂。对一个人来说,遇不对彼此喜欢的人,会很苦。而对社会来说,错过一些人,同样会滋生出一种沉重的苦涩。
这意味着,“人的发现”,始终是重要的事。郁达夫当年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己而存在了。”近百年的历史尘烟飘散,如果用心去寻迹捡拾,还是会发现,有无数值得敬重的个体生命,处于被深深湮没的状态。
屠呦呦这个名字,最近走进公众视野。如果不是因为她获得拉斯克奖,很多人对这位年届耄耋的老人会依旧陌生。拉斯克奖在业界向来被看作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很多获得这个奖项的人后来也拿到了诺贝尔奖。屠呦呦得到这个奖,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获得的最高级别国际大奖。然而,此前她在国内寂寂无闻,头上也没有两院院士的耀眼光环。
拉斯克奖是对屠呦呦“迟到的承认”与“迟到的感谢”。屠呦呦的科学发现,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做出了,她从青蒿中发现青蒿素对疟疾的显著疗效,给全球无数患者带来福音。屠呦呦之所以长期未能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足够认可,原因则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作出关键发现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个人署名的文献报告不被鼓励。”
“特殊历史时期”是值得玩味的时间概念。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种常识。它提醒我们,看到历史局限固然重要,能让今天在未来的历史中少一点遗憾更重要。今天的世界发现屠呦呦,并向她致敬,算是屠呦呦一个人的幸运,但这种幸运无疑铺着太多苍凉的底色。因为像屠呦呦需要被发现与致敬的个人,其实还有很多。
在我看来,需要被发现、感谢与致敬的“个人”,未必一定是在某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体。从某种意义上,我更认同龙应台那样的表述:“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毕竟,我们首先要作为个人存在,其次才谈得上其他社会身份属性。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有太多普通人的人性,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关爱,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总有一天,会被冠之以“特殊历史时期”这样的标签来注解着其中的幽暗与沉沦。重新发现“个人”,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切,也需要以文化重建,去形成相应的土壤。就像当年俄罗斯作家基于起码的“人道主义”立场,以人类大爱去引导人们关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一样。
前些天,在9·11事件十周年纪念仪式上,2983名遇难者的亲属逐一读出亲人的名字,以慰哀思。这场耗时极长的“生死朗读”不止让美国总统奥巴马被“深深打动”,也让全世界无数人为之深受触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你只是一个人;对于我来说,你却是整个世界”,遇难者家属这样深情地说。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从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个人原本就是最重要的基石。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人主义始终会成为一种强劲的政治文化模式的深层原因。
人生纵然苦短,但今天无数踏进社会的人们,仍在以个人奋斗为精神支柱。个人的利益、权利、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障,对于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来说,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在《易卜生主义》中,胡适借易卜生之口喊出了“世界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孤立的人”的口号,同时强调,“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现在,面对“个人”曾经得不到鼓励,屠呦呦终于得到国际学术界迟到的承认,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如何为发现“个人”进行社会文化的重建。
责任编辑 曾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