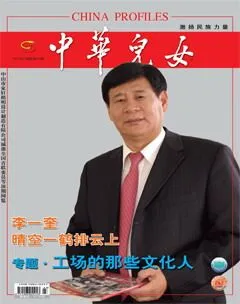做就要做得最好
北京的金秋,注定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10月中旬在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世界展示了古老中国迈向“文化强国”的雄心壮志。
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央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从首都北京发出的“文化兴国”的强烈信号,迅速在神州大江南北回荡,引起强烈的共鸣。
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对公众而言,其文化特色的地位与功能更具“圆心”吸引力。这里,不仅汇聚了中国第一流的文艺团体,文化资源、艺术人才,同时也营造了全国最具备文化发展繁荣的大环境。
在这个大环境中,有备受保护的代表国家水平的文化院团,有明确政策扶持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有完全靠自身能力顽强发展的文化力量。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以自己不同的生存方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大环境的气候和水土,百花齐放,各显异彩。如此现象,被人们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泾渭分明的阵营。
中央作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宏大战略,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通过“手术式”的变革,填平体制划分的鸿沟,打开各种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通道,形成文化兴国的巨大合力。
机遇,总是留给有着充足准备、并且持之以恒的那些人。如今,体制改革的强劲东风,会让那些长期依靠体制庇护而慵懒消极的人感到风雨欲来,也会让那些才华横溢特立独行于体制外的人看到天边的晨曦。
本期专题,我们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所谓“体制外”的文化人,了解一下他们在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历史创造中,做好了哪些准备。
提起“体制外”文化人,很自然令人想到汇聚于北京宋庄那些漂泊的艺术家和遍布京城林林总总的文化工场、工作室;眼前会浮现起那一个个自由自在、打扮另类、桀骜不驯的民间艺术家形象。他们之中很多人属于“北漂一族”,具有高学历、高智商、高志向;他们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被排斥在体制的大门外,或者不满于体制的沉闷束缚勇敢地脱离。于是,他们与一些志同道合之人落脚在郊县的农舍、市区偏僻的胡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史。
借助于北京文化中心那无与伦比的地位,植根于京城肥沃的文化土壤,他们将自己的才华在一间间简陋的工作室、怪异的工场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将一些体制内文化单位捕捉不到或不敢涉足的文化地带,搅动得风生水起——独立电影、先锋话剧、创意雕塑、街头艺术、“票儿”音乐、嘻哈相声、前卫画作、虚拟动漫……五花八门、闻所未闻的许多文化创意,从一个个工场打造出来,又流向不同的市场,成为文化消费的宠儿、公众生活的惊喜。市场与公众按照自己得到的享受,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于是,一条条以生产、需求和消费为纽带的产业链条形成了,它们构成了京城独特的文化市场。
这些工场、工作室的经营者,没有官场级别,没有专业职称,更不会得到来自政府部门授予的各种桂冠,但他们很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文化人”。因为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展现文化人的理想抱负、人格风骨、创造欲望;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艺术天赋和运用自己的谋生本领,为自己打造一块真正容身于此的事业,开创出一片昂首挺立的天地。
在这样一片天地中,要想生存发展,“唯有创新”,这是记者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四个字。简单的四个字告诉人们其在选择此业时要有多么坚定的信心和痛苦的抉择,回答了在每创作出一个艺术品时需要付出多少的血汗与煎熬,道出了多少在困惑中“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苦闷。“做,就要做得最好。”对于体制内的文化人来讲,也许只是一句豪言壮语。可对于这些“工场主”而言,是别无选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都是走投无路的落草人,是斩断了一切后路的创业者。在这个行当创业,做不到最好就要被淘汰。”正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背水一战,所以那些看似单薄的个人和团队中才会隐含着一触即发的力量,创造出常人意想不到的惊世之作。
本期我们在北京采访的几位“工场里的文化人”,清一色的年纪轻、清一色的老成相。在这年轻与老成的创造经历中,一定能让你听到别样的故事。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