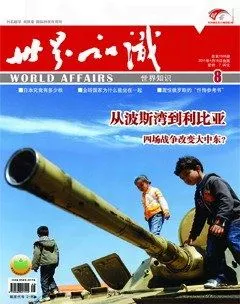积极塑造环境 防止战略冒进
近年来,随着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中国的国际作用不断增强,但所遇到的困难似乎也有增多的趋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恶化,呈现出最近30年来最为复杂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有理论上的必然性,这是我们所无法左右的。从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看,现实主义者与生俱来地对任何大国的崛起表示关注,不管对方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这种由于实力的增加而带来的安全困境,是任何一个崛起大国都必须面对的。但另一方面,也和我们自身的作为有关。安全环境是由国家间互动形成的,它的严峻化必然反映了互动能力方面的缺失。我们是否对自己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否存在操之过急的心态?这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都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既要积极地塑造环境,又要注意克服战略冒进。
具体来说,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工作。
通过主动作为来化解猜疑和担忧杜绝外界胡乱猜测的最好办法是主动作为,应出台一些类似国外《国家安全战略》之类的文件就战略意图等进行澄清。同时,要使这种解释具有说服力,还必须采取通用的国际规范。“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提法没能打消外界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会怎样和如何行事”的种种担心,韬光养晦又被曲解成规避责任。因此,还需探究外界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表达方式。其实,在国与国的对话中,国家利益是最有效的沟通工具。阐明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考虑到别国的利益,反而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另外,主动作为还要求我们加强整体筹划,在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前,应首先评估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从而早做预案,充分准备,塑造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反应,争取正面效应的最大化。
通过调整外交战略重点来寻找战略伙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中国加大了对美外交资源的投入,但却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考虑到我们的国际定位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我们的战略重点应该回归亚洲周边国家,同时还应加大对非洲、伊斯兰世界和中南美洲的投入。因为这些区域是我们在国际较量中战略力量的源泉,在此我们可以找到朋友,找到可以借重的力量。在具体的发展手段上,军援和军售都是可以考虑的途径。
以解决国内问题带动国际环境的改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有时候国际上紧张局面的根源其实在国内。转变过去那种高能耗的发展模式,也许是化解外界对中国不满的最直接途径。同时我们还应加大力度建设和谐社会,反腐倡廉,缩小贫富差距,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只有有了良好的国内形象,才能借此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利用经济优势发挥在周边的影响力和其他大国相比,经济是我们发挥对周边影响力的一大优势。在日本遭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件后,中国的区域经济优势将更加明显。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利用经济手段,谋求战略优势,重点推动加快东亚一体化的合作步伐,防止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占据区域优势。
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偶发性冲击过去,湄公河下游水资源问题以及缅甸政府与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冲突引发的跨境难民问题,都给我们的安全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处理类似问题时,我们应加强国际合作,防止非传统领域的问题引发安全环境的恶化。
实施以上策略时,还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统筹。要充分认识到一国的安全环境是一个大的系统,其中某一个环节上的变化都会影响另外的环节,而一个事件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会大干或小于该事件单独对安全环境的影响。
第二,在软和硬之间寻求平衡。在面临“中国强硬论”的指责与捍卫我们国家利益必须加强实力这一“悖论”上,软和硬的把握尤其重要。我们既不能盲目示强,也不能盲目示弱,既要努力化解周边国家的猜疑和担忧因素,又要勇敢面对遏制实力的阻挠。要区别不同情况,软硬兼施。
第三,既要承担国际责任又要防止自信心过度膨胀。在国际责任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越来越高,对此中国已无法回避。我们要做的是思考如何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获取更多的权力。同时,在目前国家崛起的关键阶段,一定要注意吸取历史上英、美成功崛起的经验和德、日、俄崛起失败的教训,切不可自我感觉过度良好。要认清我国还有许多实际困难的现实,防止战略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