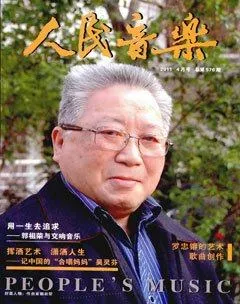批评视角下的歌剧史脉与历史视角下的歌剧批评
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所著的《作为戏剧的歌剧》一书,是一部集学识、睿智、趣味为一体的经典性歌剧论著,它兼有歌剧史、歌剧欣赏和歌剧美学等多种属性,然而它又是一反常态的,以一种全新的笔触阐述歌剧的真谛,揭示歌剧中的戏剧意义——“戏剧需要揭示人对动作和事件做出反应的特定性质,歌剧在它进一步强化这种揭示时才成为歌剧”。科尔曼在评论歌剧的戏剧意义时,直截了当,毫不妥协地提出自己的疑议,对其评论也是包罗深广、耐人寻味,充满着挑战口吻,意在寻求艺术的真伪价值。对于旧版的“过分尖刻的批评”,新版中科尔曼“期盼从公众视野中消除这些‘年少无知的错误’”,以其更能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此书的中译本(杨燕迪译)已于2008年4月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在专业圈内影响广泛,但在专业圈外却鲜见论及。考虑到本书所具有的多重文体属性及广泛的适用对象,特撰此文以期引发更多读者的关注。
一、历史通览及审美解读
本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对歌剧诞生至今的400年光景变迁做了附带性的历史回眸,从中选取了各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与作品,清晰简洁地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文笔犀利、干练,思想深邃,眼光独到:
从《奥菲欧》的“新古典的憧憬”开始了歌剧历史的游历,文艺复兴思潮促使文艺界的有识之士充分调动起了自己的灵感。并最终完成了16世纪下半叶意大利艺术音乐的表现历程和方向——从抒情走向戏剧。
随着歌剧快速发展和人们对歌剧演唱的狂热追捧,歌剧的表现走向了一个极端,科尔曼称其为“黑暗时代”。“歌手们肆无忌惮地将炫技这种自信变成了对歌剧有计划有系统地摧残”。戏剧动作被完全抛到了脑后。“音乐、诗歌、景观的大胆融合;华美的戏剧套路;铺张、辉煌、毫无节制的剧场效果;尖锐强烈的感情单一性;出没在芭蕾舞中的活动布景——所有这一切以特有的夸张姿态总结了巴洛克时代的壮志抱负”,科尔曼如是说。
这种黑暗结束于格鲁格的登场,他举起改革的利斧挥向了这些盲无目的的炫技,大胆摒弃了机械的已成声音符号的咏叹调,将其恢复到抒发感情的层面上,赋予其戏剧的尊严,并使乐队得到生机。他的《奥菲欧与尤丽狄茜》中的分曲“世上没有尤丽狄茜我怎能活”承载了深刻的戏剧动作,歌剧原初的精华品质重新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科尔曼对莫扎特的歌剧分析是最花费笔墨的,例如关于莫扎特对于奏鸣曲式的运用,对于音乐连续体问题的解决等。科尔曼认为,莫扎特不仅完善了新的歌剧剧作法,而且在风格上不断求得发展,他的《伊多梅纽》将意大利风格被推向极致(指其中对抒情分曲的应用),科尔曼从戏剧的角度予以广泛地展开,从而使读者在更深的层面上了解和欣赏此剧。《费加罗的婚礼》展示了莫扎特独特的戏剧手法,充分挖掘重唱的戏剧力量。科尔曼认为这部歌剧超越了达·蓬特的戏剧,说“《费加罗的婚礼》中最终的戏剧家是莫扎特,而不是博马舍或达·蓬特”。
对贝多芬歌剧《菲黛里奥》终场的分析,显示了科尔曼教授扎实的音乐理论功底。他的观察细致入微,通过分析其调性转换的色彩对比和情绪以及速度的变化,揭示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科尔曼再次示范了分析戏剧立意对于歌剧鉴赏的重要作用,这是本书对歌剧批评方法论方面的建设意义。
及至19世纪,“音乐连续体”——相对于古典时期的“分曲”歌剧而言——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虽然这种形式在巴洛克时期已露端倪,但它真正走到前台却是在19世纪。威尔第的《奥赛罗》、《法尔斯塔夫》等都表现出了作曲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更是瓦格纳的理想境界,“连续体歌剧”、(“无终旋律”因能保持戏剧的完整性,故而在19世纪乃至以后的时期里大受青睐。分曲形式对剧情的冲突具有表现力,对于刻画细节独具魅力,它能够突出抒情的至高点,使得剧情能够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具有向前的、十足的动力感。而连续体歌剧则具有文学性质,讲求音乐进行的整体连贯性,带有自然主义色彩,代表了19世纪在歌剧题材方面的趋势和要求。威尔第虽然也积极探索了这一新趋势,但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意大利歌剧传统的分曲形式,以期更好的为戏剧目的服务。
19世纪歌剧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动机性”音乐的作用日益清晰起来。这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音乐片段在蒙特威尔地的《奥菲欧》中就曾出现,在莫扎特的时期得以发展,并在威尔第和瓦格纳的手上达到了顶峰,这就是威尔第的“主题再现”和瓦格纳的“主导动机”。
瓦格纳的乐剧在歌剧史上非常重要,科尔曼从精神层面入手对之作了解析,说瓦格纳的歌剧结构庞大,构思复杂,主导动机充斥其中,在《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里,人性的本能被润蕴在音乐的流动中。瓦格纳模式——两个庞大的对称回环——揭示了人性的生命意义,也带给人们诸多思考。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在科尔曼眼中是一部极为独特的音乐戏剧,他建议我们去感受音乐中强烈的不稳定状态,“零碎的动机、等待的和弦、安详的片段”,仿佛使人置身于世外桃源,与世隔绝。此外,作者对普契尼的《托斯卡》、贝尔格的《沃采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浪子的历程》等几部歌剧的优劣评析,也鲜明地体现了科尔曼教授独特的视角和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犀利的言词和对本质问题决不姑息的态度。
二、体裁本质探问
Opera一词(在汉语中找不到与其对等词汇,“歌剧”这一译名也曾受到过质疑)到底是何意,这是一个难于说清却又不能回避的问题。科尔曼坚定地认为,歌剧是用音乐承载的戏剧(Dramma per musica),其中的音乐必须“进入动作”。如果看过歌剧《奥菲欧》会感觉到它的动作比较简单,唱段也还是带有牧歌的痕迹,其咏叹调也不是那么饱满,但科尔曼教授看待这部歌剧的态度却是非常宽容,因为在他看来,这部剧的问世完成了以音乐来表现戏剧的使命:“在这里,作曲家就是戏剧家”。我们可以通过个案来证实这个观点的正当性:
蒙特威尔第和格鲁克对同一个神话故事《奥菲欧》用音乐进行了诠释。他们对同一个戏剧动作赋予了不同的美学观念:在奥菲欧用歌声感动冥王以后,把自己的妻子从冥府带向人间的过程中,违反了中途不能回头看他妻子的规定,使得尤丽狄茜再一次死去。对于这一戏剧动作,蒙特威尔第把奥菲欧描绘成一个过分自信的、冲动的放大了自己音乐之神的力量的人,把曾经的承诺抛之脑后,直至违反了禁规,再酿悲剧。而格鲁克笔下的奥菲欧却是理智的,由于妻子的悲悯和执拗,无奈地作出了这一举动。他们不同的戏剧立意,直接反映在他们的笔下。格鲁克所描绘的奥菲欧在此是那么的绝望和无奈,悲剧再次发生后,“世上没有尤丽狄茜我怎能活”表现出的顿足捶胸之感将奥菲欧带到感情体验的高峰。而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此时表现的却是极度的懊恼。他们不同的音乐处理刻画出不同的人物内心情感,而音乐在此时的表现力恰恰是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可见,戏剧动作的进入使得音乐被赋予了生命。
对于格鲁克而言,戏剧至高无上,音乐是陪衬。而对于莫扎特而言,戏剧存在的目的是给音乐以机会。音乐彻底吸收、完全重塑了戏剧。科尔曼对莫扎特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中,其独立表现戏剧冲突的能力甚或超过原作。他的《伊多梅纽》、《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等无不体现着戏剧动作在音乐中的流动,他的重唱尤其擅长于此。《魔笛》则达到了高峰,其中的戏剧进行被安排得清晰、顺畅,并分别用不同的音乐形式来解释戏剧当中不断出现的冲突,如维也纳的民谣、德国风格歌曲,还有意大利喜歌剧的风格、格鲁克风格和意大利正歌剧风格等集各种体裁于一身,且运用娴熟。在现实中承载着各种重负的莫扎特,在他的歌剧作品中却颂扬着“大同世界的完美理想和善德终将战胜邪恶”的思想颇具赞赏价值。这种崇高思想和纯熟的创作技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威尔第、瓦格纳时期的歌剧创作处于博弈时期:作曲家既与自己博弈,也相互博弈。他们的创作历程实际上是个思索的过程,这一点在他们的早、中、晚期歌剧的不同风格中得到了印证。威尔第与瓦格纳同年出生,却代表了两个不同风格各自的巅峰状态。意大利的歌剧风格被威尔第推向了有史以来的顶峰,瓦格纳却将德国歌剧带入了后继乏人的状态。两人共同探索并完善着关于歌剧的连续性问题。一个是将主题再现运用到音乐的流动之中,一个则是将主导动机丰富到极致。威尔第在沉寂了十几年后推出的《奥赛罗》一反之前的风格,重拾传统的意大利歌剧模式,注重旋律性和人声的表现力,使得一些分曲大放异彩至今。瓦格纳及其追随者们对意大利风格不屑,仍继续将无终旋律的实践进行到底。这种创作风格自《漂泊的荷兰人》开始渗入,一直持续到《尼伯龙根的指环》。尼采称瓦格纳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说他的音乐是“野蛮的、做作的”。
三、有关批评策略的讨论
科尔曼对歌剧的欣赏和批评有个最根本的原则,即,对歌剧的探索和研究要遵循一定的审美标准,要有健康的、客观的态度。高远的戏剧立意,应是以剧本为基础,通过音乐来进一步强化揭示人对动作和实践作出反应的特定性质的过程,歌剧不应仅仅是咏叹调、宣叙调、重唱。至此读者可能会感到,站在戏剧的立场上欣赏歌剧会发现歌剧的空间十分广袤。
除上述观点外,作者还对歌剧评论中出现的片面观点予以批判,比如“纯音乐”的观点和“纯文学”的观点。首先,持文学性观点的评论家将音乐的功能极端化。如美国戏剧评论家和导演埃里克·本特利就强调音乐不能对事物的概念加以界定,不具备实际应用的功能。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作者对此进行了反驳,说:音乐可以围绕着文学或诗歌对事物的“指称”,“自由地施展它最细微的联想和表现力”,音乐可以作到文学语言所无法达到的境地,比如音乐对恐惧的摹拟,音乐对欢乐的诠释,远远高于文学或诗歌语言所能达到的极限。当然,另一种强调“歌剧的结构是一个先在的纯音乐体系,将其缩减为一个和声终止式——Ⅰ-Ⅳ-Ⅵ-Ⅰ”的观点当然也是不合适的。作者对这一观点也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并列举一些评论家对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的推崇音乐至上的、片面的评论来说明其极端的程度,例如竟有观点认为莫扎特曾利用G大调对于D大调的从属关系来确定伯爵对其妻子的支配权,科尔曼对此进行了辩驳,倘若如此,那是否也可以说七级音对主音的倾向性可以理解为子女和父母的关系?这只有去问莫扎特了。普契尼的《托斯卡》由于缺乏正当的戏剧立意,被科尔曼抓做把柄,借此对持纯音乐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科尔曼主张,即使最完美的音乐也必须和崇高的戏剧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这样才能使其发挥出耀眼的光芒,否则音乐将是空洞的,戏剧将是苍白的。作者在书中对《托斯卡》与《奥赛罗》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托斯卡》在音乐的创作方面有很多《奥赛罗》的影子,但前者在戏剧的层次感上不够顺畅,由此科尔曼将《托斯卡》称作歌剧中的劣品,这也说明音乐的优劣并不能取代戏剧的内容,脱离戏剧的音乐将是没有生命力的。
最后的裁决毋庸置疑在于音乐,但却不是纯音乐、也不是纯文学。现代人理解歌剧,既要怀着一颗包容的心,尽量从多角度来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真正的意图,也要了解它们所处的时代文化,并充分发挥想象力,换言之,要“使用今人能够理解的术语去重构作曲家的观念”,这才是积极可取的态度。
四、更待深思的问题
这本书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可以带给读者很多思考,促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歌剧这种戏剧形式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此举要如下:
其一,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和瓦格纳的歌剧改革有什么异同(或历史意义)?格鲁克的歌剧改革是在当时的歌剧走向极端,咏叹调泛滥,歌剧中的戏剧意义几近为零的情况下,对歌剧进行了改革,使咏叹调和宣叙调的应用趋于合理,提高了乐队的功效,丰富了合唱在歌剧中的作用,并对舞蹈和舞台布景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而瓦格纳的歌剧改革则是建立在一种精神上的,为了获取某种掌控权利的一种自我强大的精神力量的自然流露,他的歌剧力图表现精神、政治、社会以及哲学的内容,因而从题材到风格的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与传统的意大利歌剧割裂开来,形成了他的歌剧——乐剧,这对后世的影响堪称巨大。
其二,如何认定瓦格纳的歌剧改革?与其说它是对前期歌剧的改革,莫不如说是他在重新整合了之前的诸多音乐形式并产生了他的独具风格的新音乐体裁——乐剧——更为合适。
其三,关于《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中音乐和话剧的“鸡”和“蛋”关系。《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是德彪西唯一一部歌剧,梅特林克的《伊里亚斯》带给作曲家灵感,作曲家又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赋予原作以灵魂,其结果是,似乎没有独立存在的脚本。如科尔曼所说,“音乐给这部戏剧以支持,使他更加清新,更加生动,也更加可信”。
其四,可从歌剧的几次大型改革看歌剧的演变过程。如,蒙特威尔第的歌剧形式的建立;梅塔斯塔西奥对于意大利正歌剧的影响;格鲁克的歌剧改革;莫扎特对歌剧的创造性地发展;威尔第对歌剧的改革或完善(虽然他本人并不如是说);瓦格纳乐剧的建立;德彪西、贝尔格的歌剧新观点,等等。
其五,对普契尼歌剧的优劣评述。意大利歌剧在经历了威尔第的巅峰阶段后,由普契尼再续辉煌。与威尔第相比,普契尼的戏剧动作略显寡淡,但它的旋律的歌唱性和抒情性却是近现代作曲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普契尼歌剧备受喜爱和能够成为保留剧目的原因之一。
其六,威尔第作为歌剧史中的巅峰人物的这一历史地位。他赋予了歌剧以高尚、丰满、旋律流畅、戏剧性强的内涵,使得歌剧成了人们喜爱的诸多戏剧种类之一,并牢牢占据着历史舞台。
其七,歌剧中“歌”的作用在哪里?
其八,台本作家对歌剧创作的影响,也即台本作家和作曲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问题。如下几对是颇有趣味的典范:格鲁克—卡尔扎比吉;蒙特威尔第—斯特里吉奥;吕利—基诺;莫扎特—达·蓬特;威尔第—皮亚韦、博依托;德彪西—梅特林克。
其九,威尔第的“主题再现”和瓦格纳的“主导动机”技巧之间的异同问题。威尔第的“主题再现”意在加强回忆,而瓦格纳的“主导动机”则寓意深刻。
综上,读者通过本书所能取得的收获是非常丰厚的,故而我们应向其作者科尔曼教授,以及中文译者杨燕迪教授致敬。也望有更多的人受到此书的震撼。
赵丽萍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