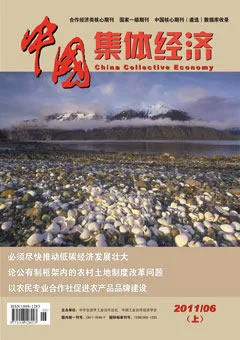我国社区增权的脉络分析
摘要:文章沿着“社区-社区旅游-社区参与-社区增权”这样一条主线,论述了社区增权产生背景及概念、社区增权的方法等,并提出我国社区增权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等,以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社区增权问题。
关键词: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增权
一、前言
社区、社区旅游、社区参与在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成熟。近年来,这些概念和相关理论不断地被引入到我国并进行研究,但由于中西方之间社区参与旅游的“社会意义”和“利益点”不同,结果存在差异。在我国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因此,社区増权作为一种概念提出并进入实质性的研究。
二、社区、社区旅游、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
社区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认为,社区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1887年出版的《Gemeinschaftund Geseuschaft》 《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最早提出的。目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社区指的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有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们的活动区域。社区必须有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必须有一定的地域条件;要有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要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社区既具有诸如地缘、友谊、亲情、认同、共生互助等传统内涵;也包括磨合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处理公共事务的运作模式、确立适合本地域生活方式等现代含义。
社区旅游是指从社区的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以社区的互动理论指导旅游区的总体规划和布局,通过优化旅游社区的结构提高旅游流的效率,谋求旅游业及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和最优化。从这一认识来看,社区旅游当中的社区界定就较为明确,即参与旅游的社区。
社区参与是近年来乡村生态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社区旅游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并在此后的国内外旅游研究和旅游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社区参与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旅游继续被开发商、政府所控制而不是社区利益所控制”,“这种参与只不过是一种对公共关系的虚饰。它仅只允许当地社区对即将实施的规划、计划、建议和发展在很小的范围内做出反应”(Macbeth,1996)。诚然,社区参与的理论不足和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转而分析其原因和问题的所在,继而一部分学者转向对社区増权进行研究。
三、社区増权研究进展
(一)社区増权概念的提出
增权理论(EmpowermentTheory),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1976年,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出版了名为《黑人增权:被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的先驱著作,从种族的议题率先提出了“增强权能(Empowerment)”这个概念。
1999年,斯彻文思(Scheyvens)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
2003年,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在《增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empowerment for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
左冰、保继刚(2008)年认为:增权(empowerment),是由权力(power)、无权(powerlessness)、去权(disempowerment)以及增权(empowering)等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其中,权力或权能(power)是增权理论的基础概念,增权是整个增权理论体系及其工作实践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
(二)国外研究进展
自1985年墨菲(Murphy,1985)正式提出“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community-driven tourism planning)”或“基于社区(community-based)的规划”方法以来,社区参与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旅游发展研究中。
阿克马(Akama J,1996)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
1999年,斯彻文思(Scheyvens)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他明确指出,旅游增权的受体应当是目的地社区,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四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是目前较成熟的理论成果。
(三)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学者王宁(2006)率先展开了对増权理论的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分析和研究,以及把増权理论应用于具体的领域分析。对中国期刊网应用主题词社区増权进行搜索,共查到六篇相关文章,只有两篇具体谈到了旅游増权。其中,左冰、保继刚(2008)具体分析了西方旅游増权的具体理论研究。他们指出:由于社区参与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足,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在他们的文章当中,提出了増权理论的概念及方法。认为:增权是通过个体、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共同实现的。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个人增权(personal empowerment)、行政性增权(empowerment through administration)和政策性增权(empowering through policy)三种形式。旅游增权首先必须聚焦于发展居民个人的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即个人增权应先于社区增权。只有稳定的个人权利得到足够保护,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才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和限制。同时指出:西方的旅游増权主要集中在信息増权和教育増权两个方面,我国学者王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増权的必要性。
保继刚、孙九霞(2008)从实证情况下讨论了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的雨崩村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社区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治增权的案例。但从整篇文章分析,社区増权在该地区还未真正落到实处。
(四)我国社区增权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国外和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社区増权问题的研究要在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立足我国的国情,进一步地研究和分析。
1、我国政府在旅游的发展当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旅游发展规划,一般由当地政府结合规划单位,再由开发商进行开发、运营。旅游产品的最终形式是政治家、社区和商业伙伴之间权力互动和合作程度的展示。与政府的强制力和开发商的资本力量相比,社区居民更多的是处于弱势地位而非平等的协商者。加之在我国旅游开发中,一开始就面临着资源所有权问题的约束。旅游资源所在地往往是当地居民世代从事生产、生活和栖息的地方。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资源国有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集体”究竟是什么含义不甚明确,哪种实体可以行使土地集体所有权也模糊不清。这种模糊状态导致了权利真空现象,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谁拥有土地及其资源,因而当地居民也就不知道可以凭借什么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2、我国当前社区建设面临着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缺乏组织性、社区活动流于形式以及社区归属感淡薄等问题。社区居民在思维上的主体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参与性都还不够。除了对社区进行教育増权和信息増权外,我国学者王宁提出了制度増权。在理论上似乎能够确保社区的能力建设,但在实际的应用和操作中,往往事与愿违。特别是在我国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社区开发了旅游,促进了当地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按理他们在能力建设上的培养应该逐步得到加强。但是,根据调查和相关文献的了解,这些地区往往陷入了一个“既然通过旅游能够挣到钱,我们就去搞旅游;通过旅游挣了钱,有了钱,我们又何必去学习,去接受教育?”的怪圈。这并不是教育和信息乃至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民素质的问题,社区能力建设必须顺势而上。
3、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由于我国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民主化进程、旅游发展阶段等的不同,在我国开展社区増权问题的研究,要比西方社区复杂得多。不管是对社区参与还是社区增权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关注我国的国情。
参考文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