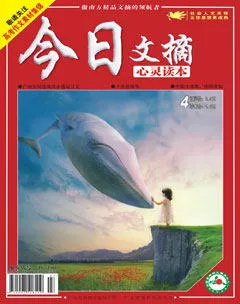中国大堵车:刚刚开始
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北京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才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得进入这种状态。”
陆化普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5年后会有750万辆车。“那会真的瘫痪。所有城市功能会瘫痪,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数,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甭说700万。”
“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了一下,说:“那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2000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没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我们有多道防线,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这让我很意外,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3年前他是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时还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当拥挤发展到了某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中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为何要为此付拥堵费?”
“这个不对。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你是造成堵车的一个贡献者,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噪声等,所以就应该支付经济成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考虑这个城市。”
“那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你看香港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就不堵。”
“香港公交分担的交通压力是89%,也就是说,只有11%的人才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出行,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我们的城市交通就会好很多。”
“有人会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吗?”
“我们不能剥夺你的购车权,但必须要保护全体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只能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新加坡现在全方位全智能化地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超过20公里,再放行。如果这样的方法也遏制不住,那就用这个办法——尾号管理,严厉一点,就是单走双禁,双走单禁,车自然去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像单双号禁行以后将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
也许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坐地铁试试。
陆化普约我转了一次。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走下去……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还说,他某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吧?”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地铁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长的通道,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到这里。”
“协调一下有这么难吗?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嘛。”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还存在利益分配的协调。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
我突然想到,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13号线,想到买车,可是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一天折腾下来,到家就只剩下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城市结构问题。大家工作都在市里,离得远,回家只剩睡觉时间了。轨道运输能力有限,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原因,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大家要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那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继续建设的?”
他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形成拥堵,这不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说:“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后面产生的拥挤,大家不会认为是那一任修了大宽马路而拥堵的,而会说现在车多了。缺乏事后评价让我觉得有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的小汽车主导方式有一个反思: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道:“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中国城市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环境破坏,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了。”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我总是期待,什么时候能写本《交通教训案例集》,可能对大家理性化思考有好处。”陆化普说。
(路仕鹏荐自《长江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