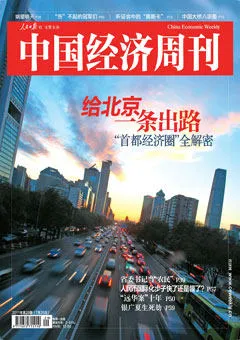给北京一条出路
2011-12-29 00:00:00王红茹
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29期



历经半年,“首都经济圈”终于从一个概念进入到了规划制定阶段。
在此之前,“京津冀一体化”始终停滞在“设想”的层面。为改变大都市与贫困县区隔墙而立的现实,“环渤海”、“环首都”各种规划层出,却在推进中遭遇种种困境。
从世界城市发展规律上看,伦敦、巴黎,再到东京、首尔,那些世界级的大都市,均以都市圈的形式出现,成为了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区域经济中心。
无例外,中国的“首都经济圈”今年初也在官方最高规格的规划中惊艳亮相,并被上升为国家战略。
经济圈中的核心——北京,正积极回应。这个致力于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正在被过度膨胀的人口、拥堵的交通、居高不下的房价所拖累,饱受“大城市病”困扰,北京正迫切需要与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强力支撑世界级城市发展的空间,从“虹吸”效应逐步转化为“溢出”效应。
毗邻的河北一直致力于为北京解忧,无奈,却得不到北京的积极回应,直至“首都经济圈”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并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这一回,河北不再一厢情愿。它辖下的那一片贫困县即将迎来蜕变的机会,确切地说,已经看到了蜕变的迹象。
另一个主角天津,在多个“首都经济圈”空间划分研究方案中,均据重要位置。这个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的直辖市,在圈中当然不可或缺。
在各方的积极互动下,“首都经济圈”的综合发展已然进入了规划制定的关键期。
然而,摆在制定者面前的问题依然如旧: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如何定位各区域的功能?如何打破体制的制约和区域的壁垒?如何均衡各方的利益博弈?如何解决首都北京交通拥堵、人口过多、创新力不足、生态环境不佳等等问题,从而实现向“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腾飞?
这一切仍然悬而未决。
从北京城区经京津塘高速41公里,开车约40分钟,便是河北省廊坊市。
宽阔的大街上,偶见大学城的学生们吃过午饭在树荫下三三两两地散步。渐进市区,车辆和行人陡然多了起来,但道路依然顺畅,街面整洁。
看到北京的车牌,路上发小广告的人拼命将广告往车里塞。只要你接下,他们便会热情地招呼你说:我带你去这个楼盘实地看看吧。
跟随“小广告”而去,售楼处的火爆委实让人难以置信:售楼处停车场,是壮观的清一色北京车牌,销售楼里,近10批次准业主正在排队等候买房。
廊坊东方大学城,这个地方的房价在这一两年内已经以火箭的速度增长到了近万元每平方米,实现了翻番。
房价是一个侧面:河北——北京,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因为一个几经预热的概念——“首都经济圈”开始了越来越亲密的接触。
今年3月,正式亮相的“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
“目前我和同事正在做相关工作,已经把打造‘首都经济圈’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首都经济圈怎么建设、怎么规划,正在谋划之中。”在不久前河北廊坊召开的“2011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的发言并不详尽。不过,这已经是他接受记者采访的底线。
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有关“首都经济圈”的言论。此番表述,让多年来停滞不前的“京津冀一体化”有了新的盼头。
的确,首都经济圈的建设需要一个精细的规划,一个建设周期,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多方了解,目前北京、天津、河北都正在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之后将分别提交国家发改委,届时,国家发改委将根据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制定的规划经协商和专家论证之后,制定出首都经济圈的综合发展规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个综合发展规划中,经济发展是首要,除此之外,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空间结构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也会在规划中体现。
但规划无论如何制定,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首都经济圈的空间范围如何界定。
这是真正的核心,也是争议的焦点所在。
“2+7”方案或将落定?
“京津冀都市圈”方案夭折的原因在于强调了“平等”,缺乏轴心。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并不契合。
无论身处北京还是河北,当你问当地人是否听说过 “首都经济圈”这一概念,没有人会说“不”。但被问的人十有八九是将这个名词跟去年河北省出台的“环首都经济圈”混为一谈了。
两者虽只差一字,身份却大相径庭。
随着“首都经济圈”写入‘十二五’规划,其规格自然比河北的“环首都经济圈”超出一级。
首都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并非一个新名词。历史上,国都周围地区称为京畿,由主管京师的官员管治,承担支援和服务首都的重要职能。自辽代起,北京成为国都,至清代,其首都圈范围越来越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北京为中心,半径300~400公里的圈域,圈域内包括保定、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等一批重要城市,这些城市以其特定职能(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服务于首都,保证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与文化中心职能的发挥。
历史证明,河北毗邻京城的那些城市曾经是首都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京,毫无疑问是首都经济圈的核心。但因为朝代的更迭,这一段首都经济圈的发展史也因此戛然而止。
相隔近百年之后,一位区域研究学者在一份代表着强烈官方色彩的研究报告中再次系统地提出了首都圈的意义、概念、划分与战略。他名叫杨开忠,是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他所主持完成的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持续首都:北京新世纪发展战略》。他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北京要建设成世界级的城市。
彼时,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经从地理上的概念跃升为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各领风骚。然而,以首都为核心的周围城市经济一体化进展却相当缓慢。
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但时至今日,这一等待了7年之久的规划一直未能获批。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十一五”时期提出的“京津冀都市圈”夭折的原因在于强调了三地的“平等地位”,缺乏轴心。京津冀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仍有不同,尤其是北京、天津这两大直辖市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难度很大。
由此,“首都经济圈”开始浮出水面。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目前学界有关首都经济圈空间范围的界定主要有“2+5”、“2+7”、“2+8”、“2+11”等多个方案(见“首都圈空间划分的几种方案”)。但哪种更切合实际,仍需要科学的研究论证。
李国平,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也是今年北京市首都经济圈规划的起草人之一,多年来致力于首都圈的研究。在他看来,“2+7”方案最具可行性。
“2+7” 方案是在综合采用交流强度、断裂点、引力模型和场强模型分析经济联系强度的计算公式后,由杨开忠领衔完成的《持续首都:北京新世纪发展战略》得出的首都圈范围,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唐山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等9个城市。
“2+7” 方案与当年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区域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该区域范围是“2+8”,比“2+7”多了一个石家庄市。
“石家庄和北京并不连接,中间有一个保定市,这样石家庄和北京的联系也就不那么直接紧密了。如果是京津冀都市圈,可以有石家庄,因为它代表了河北;但如果是首都经济圈,应该是以首都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2+7’是比较理想的。”李国平说。
给北京一条出路
人口和城市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潜力,北京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需要更广阔的腹地。
“环首都经济圈”的主角是河北,而“首都经济圈”的主角毋庸置疑是北京。
在李国平对“2+7”方案提供的详尽数据分析中,首都圈各城市实力高下立分:
2009年,“2+7”的9城市总人口(户籍人口)7012.21万人,总面积16.67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56.97%。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城市有7个,其中张家口、承德均在3.50万平方公里以上,保定约为2万平方公里,北京1.64万平方公里,从面积上,北京位居第四。
从人口来看,北京、天津、保定人口过千万,分别为1755万人、1228.16万人、1101.66万人,其余4个城市均介于200万~500万之间。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北京(85.00%)和天津(61.80%)超过全国46.59%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其余城市均位于首都圈的平均水平56.97%之下。
从生产总值来看,2009年,首都圈地区生产总值3.05万亿元,人均GDP为4.86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72万亿元,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5.1:40.7:54.1,为“三、二、一”模式(如下表所示)。
9城市中,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首位,占首都圈总产值的39.81%,其次是天津和唐山,分别为24.64%和12.49%。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北京人均GDP高达7.05万元,是天津的1.12倍,唐山的1.38倍,保定的4.49倍。
人口和城市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潜力,城镇化是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
在此理论框架下,李国平认为,首都圈各城市在人口、城市面积、城镇化水平等方面差异非常显著,综合而言,9个城市中北京优势最为明显,拥有最大的人口规模和最高的城镇化水平。
“毫无疑问,北京是首都经济圈的绝对核心城市,其中心地位十分明显。”李国平说,首都经济圈具有的战略意义之一,就是将首都经济圈打造成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支点,这样有利于平衡全国的布局。
北京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当然也需要更广阔的腹地。当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这个需要也越来越迫切。
“首都也面临着发展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视角,从高的基点上研究、规划,最后加以解决。”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必然涉及并提出化解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有首都经济圈,如东京大都市圈、伦敦大都市圈、巴黎大都市圈等,这些地方不仅是各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国际经济、金融、商务、文化及信息交流的中心。同时,依托首都经济圈建设促进首都城市国际化进程,并使之成为首都迈向世界城市的重要空间基础。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相当部分的首都经济圈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到整个国家的1/3以上。而从京、津、冀三省市目前的总和来看,2009年GDP合计为3.66万亿,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0.9%。同在2009年,“2+7”的GDP总和为3.05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10,同期北京的生产总值为1.2万亿,换而言之,“2+7”方案中的城市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再造三个新北京。
当然,与发展已相对成熟的另外两大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相比,首都经济圈更具特殊性。长三角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是上海,珠三角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是香港,但首都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是首都而非一般意义的大都市。首都是一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比一般大都市具有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职能。
“也因如此,首都经济圈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处理好经济中心跟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关系,特别是跟政治中心的关系,要确保政治中心功能的有效发挥。”杨开忠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基于首都经济圈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其构建和发展具有更加重大和特殊的意义。
天津的“小算盘”
三方的表态耐人寻味:河北相当积极,北京较为中立,天津则显得动力不足。
首都经济圈的界定范围无论是“2+5”、“2+7”方案,还是“2+8”、“2+11”方案,天津都在列。
130公里,这是北京与天津两个直辖市之间的直径距离。这也是世界上两个超大型城市之间最短的距离。然而,两个城市之间心理上的隔阂远远超越了地理上的距离。
随着200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提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失落了数十年的天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身份。
而在政治的号召和政策的倾斜下,资源、资金和项目也迅速地向这个新兴的发展高地集中,急速地转化为了GDP。
2010年,天津以黑马之势超越了GDP增长八连冠内蒙古,拔得头筹。曾经沉默的天津又重拾了往日的辉煌,恢复了信心,甚至野心。
但如今,首都经济圈的出现,无疑会使天津人产生其“北方经济中心”地位或将会被弱化的忧虑。
这从今年5月18日召开的“2011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上可见一斑。三方的表态颇耐人寻味:河北表现得相当积极,北京较为中立,天津则显得动力不足。
在峰会上,河北首次推出了“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规划展,主动表明了其借力首都经济圈建设,加快发展进一步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愿望。河北省副省长赵勇的态度颇为主动和热情:“要为大局服务、为首都分忧、为河北发展添活力。”
北京的表态也颇为明朗。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助理姚飞表示,“希望早日看到京津冀都市圈能发挥像长三角、珠三角一样的作用,以三足鼎立之势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侯一民说:“天津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地区,我们会竭尽全力做好我们的工作,拥护中央的决策。同时我们觉得首都经济圈是空间上的部署,天津滨海新区的开放,作为这个地区的重要引擎,我们把它做好,就是对首都经济圈最大的贡献,也是重大的推动。”
天津的表态表面看上去无懈可击,但仔细再回味,似乎也不算什么表态。
如果以北京为核心打造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就会与天津现有的华北经济中心的定位相冲突;而如果天津要成为华北经济中心,就意味着北京要把经济功能让出来。
但后一种可能性似乎不大。
“首都经济圈肯定是以北京为主,天津为辅,天津是首都经济圈的一部分,要配合首都经济圈。”河北省委省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薛维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基于此,有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天津最主要的注意力并不是争取发展的问题,天津要的是地位,是“中心”。
两个经济中心的关系该如何协调?
记者采访天津发改委等部门,相关人士对这个问题缄默其口,这使得天津的态度更加扑朔迷离。
“实际上,首都经济圈一定是多核、多中心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型的城市群也都是多中心的。”杨开忠说。
多年以来,北京与天津的关系极其微妙。例如,天津港的特殊地位无可替代,北京进口的车都来自那儿;再例如,京津城际高速铁路,30多分钟的距离,商务往来完全一体化。
“首都的对外交往职能,首都的很多物资,包括工业产品的进出口,都要通过天津港,它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如果天津排除在外,至少在经济功能上是不完全的。” 李国平认为,从职能方面考虑,如果不把天津算在内,并不合理。
“‘2+7’是比较理想的方案。”李国平建议,不要因为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影响首都经济圈的完整性。
破除区域壁垒要靠中央
“京津冀的关系,说到底,不是三方关系,而是中央与京津冀四方的关系。没有中央参与,游戏失去主角,结果就很难预料。”
在中国区域经济的成长中,区域壁垒的弊端相当明显。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16个城市的市长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协调会;现拥有32个成员市的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该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举办一次。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京津冀地区也成立了一个环京经济协作办公室,是环绕北京市的八、九个城市共同组织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能主要是“经济协作和合作”。后由于职能所限,收效甚微,也就不了了之。
2004年,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组织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最后达成加强区域合作的“廊坊共识”。
然而,由于受制于行政体制,以及包括税收、财政等涉及利益分配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再加上北京、天津、河北省行政级别相同,很难让谁说服谁,以往达成的共识并没有真正上升到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和谋划,颇受局限。
历来,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层次主要表现在定期举办的会议和比较小的项目合作上,在薛维君看来,“就是在闲人和闲组织之间干的一件事”。
“应该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院下属的有关部委以及京津冀三方政府参加。如果由国务院办公厅召集起来,这件事就有点意思了。”薛维君说。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结构,也是导致行政上无法统一规划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结构中,除了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主两副”,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和南京为城市副中心,三大城市融合发展,而珠三角和京津冀均是“双中心”发展结构,珠三角以广州、深圳为中心,京津冀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外围城市环绕发展,这种结构容易造成行政上无法统一规划发展,前者幸好有广东省统一协调,而后者呢?
薛维君直言:“体制造成的障碍需要改变体制才能够破解。”
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认为,“京津冀三地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一定要打破行政区划僵化的制约,真正做到区域一体化的协作。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机构,仅靠三地的行政部门各自来做事是比较困难的。”
河北省副省长赵勇建议,在国务院层面要形成一个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成立专门办公室,最好设在国家发改委,协调三方政府共同行动;还应由权威机构牵头,组建一个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院,站在宏观和第三方角度研究区域合作与发展的问题和规律。
“京津冀的关系说到底,不是三方的关系,是中央与京津冀四方的关系,关键是有中央参加。没有中央的参与,这个游戏的主角是缺席的,结果就很难预料。”薛维君说。
京津冀一体化大事记
发起
(1986年—2003年)
1986年,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倡导下,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
全面启动和实践
(2004年—2009年)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市发改部门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 “廊坊共识”。
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已从构想、探索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实践阶段。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唐山市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
2008年2月,由天津市发改委倡议和发起,经过京津冀发改委共同协商、酝酿的“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在天津召开。京津冀发改委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
加速推进
(2010年至今)
2010年10月,河北省政府《关于加快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提出了在规划体系、交通体系、通信体系、信息体系、金融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等6个方面启动与北京的“对接工程”。
2011年5月,首届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