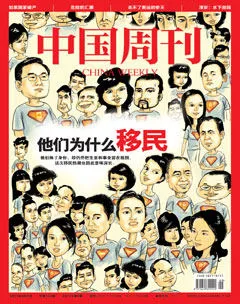音与字
2011-12-29 00:00:00徐戈
中国周刊 2011年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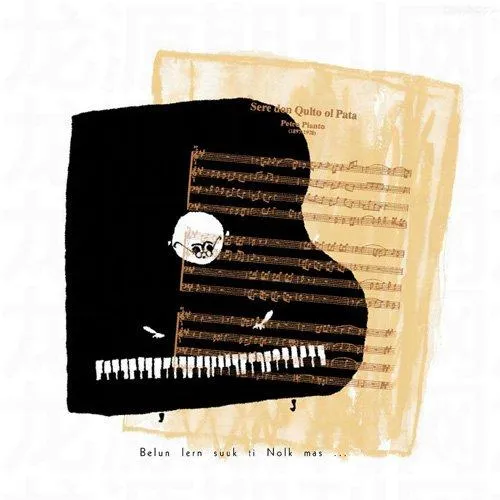
我一生不断受到谴责,说我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其他危害社会的倾向。
涅克拉索夫对这个要求的回答好极了:“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
我愿意在这句话的后面签上我的名字。
——肖斯塔科维奇
似乎总乐于在乐谱中留下某些注脚,再经回忆的文字设立悖论。
这些藏匿的机关,注解和质疑着音与字的背景,以至于某日相互作为对抗时,依旧显得如此虚妄和意味深长:
《第八号弦乐四重奏》,隐藏个人黯然夙命的安魂曲,四重奏的主题是D.Es.C.H.(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缩写。肖对友人说:有时我这样想,如果我在某时一命呜呼,未必有人能专门作曲来寄托对我的哀思。因此,我决定为自己先写这么一首乐曲,这部《四重奏》的虚假的悲剧色彩是这样产生的:我在谱写过程中所流出来的眼泪,跟一个人喝了大量啤酒之后的撒尿量一般多。
《d小调第五交响曲—革命》,肖斯塔科维奇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与分裂,称这部作品是“一个苏联艺术家对于公正批评的实际的、创造性的回答”。而实际上是以传统模式的作曲技法,挽救当时政治高压下作曲家自己命运的‘赎罪之作’;以贝多芬NO.5交响曲“命运”的引申共通,暗释作者本人自我沧桑的人生转折。
《第十一交响曲——1905》, 谱面诠释是“为纪念1905年1月9日在俄罗斯帝国沙皇时期圣彼德堡武力镇压革命游行群众事件”,而实际乐曲的人性设定却将最大的悲伤留给独裁者的牺牲者,肖氏为他的乐曲辩护着说:“其实这是沉重谱写斯大林坚冰时期东俄现状的悲怆华章。俄罗斯人民总是这样——他们相信、相信,后来突然一下子不相信了。不再为人民相信的人,都落得了坏下场,但为此必须流很多血……”
众所周知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一直以来是音乐史上的传奇和反法西斯赞歌: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危城遭围的1941年7月末,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本交响曲的大部分草稿,总谱由飞机空运到炮火弥漫的城区,电台向全城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活着的乐手前往登记。
在肖氏描写的“战事带来的巨大悲伤,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人民,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必将胜利”的音乐诗篇中,无数眼泪和爱国热情,在列宁格勒这个属于自己的城市中孕育凝聚,战争中的人们用切身的体验和爱国热情,全力奏出担负的苦难和经历。这部交响曲的初演,作为前苏联的一项 “国家大事” 来对待。本曲题献给“列宁格勒”,并获得当年“斯大林奖”首奖。
然而《见证》回忆录和287封给友人格利克曼的《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再一次验证了作曲家的跌宕人生—— “我的每部交响曲都是一座墓碑”。 在谈到《第七交响曲》时,肖斯塔科维奇为人们不了解这部作品的真正意图,而简单将其看作是战争与胜利的音乐史诗而伤心不已,他说:《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它的主题不可能源自于希特勒的进攻。这个进攻的主题,和希特勒无关,我在创作的时候,是想着人类的敌人,我想着希特勒是个罪魁,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是……我对被希特勒杀害的人们怀以无限哀伤,同样,也对在斯大林命令下惨死的人们更感悲痛,我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曲》题为“列宁格勒”,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描写被斯大林所破坏、被希特勒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交响的澎湃乐音终抵不过黑字白纸的另一种诠释,就像植根于大屠杀的那些艺术史,是音乐还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