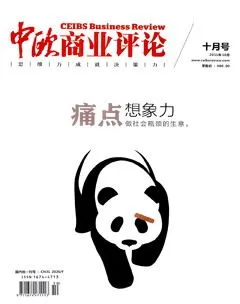痛点想象力
不断爆发的食品丑闻,企业偶像的倒掉,表明此处商业竞争尚处极低段位。相比十年前,中国仍然是一个满布“痛点”的国家。“痛点”不是普通的消费需求,而是那些具有社会普遍性、长时间得不到很好解决的社会之痛。
既然“痛点”孕育着需求,那么如何使这样的需求变现?既然“痛点”会持续为“痛”,意味着个中的需求满足起来障碍重重,那么如何具备“消痛”的独特能力?如果企业一开始并不是针对“痛点”而去,但在经营中突然触到行业或社会的“痛点”时,又该如何应对?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知道“痛点”是怎么来的。
“痛点”是怎么来的
西方有位学者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让人疯狂:权力、酒精和匿名。权力排在第一位。中国企业的竞争行为,最后总能归结到一个词——权力。比如“价格战”。这么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并且已经从传统产业向互联网产业蔓延。一个典型代表就是京东商城。它的思维方式就是:先融很多钱,亏本卖,依然能够活着。有了钱,就可以把其他人都耗死了,行业里就剩我一个人,有了权力,就可以制定规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中国,一个企业拥有这个行业的绝对权力之后,必定会迷失。黑格尔有个“时代精神”的说法,大意是历史的某一阶段,其时代特点由那个时代的一群英雄的精神和气质决定。如果这么看,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精神和气质值得一提。从一开始允许一部分人经商,一批人先富起来,他们有了钱以后有了权力,有了权力之后就“晕菜”了。他们肆意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自然也会忘记一些东西。一个时代的精神跟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们都这么疯狂了,时代自然也就很疯狂。
从阶段相似性来看,我们的这个时代和美国从南北战争至20世纪20年代那一段很像。那段时间是美国发展最快的时候,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快速发展带来很多问题,新闻史里常说的“扒粪运动”就出现在那个时候——因为商人们做得太过分了,民众吃的食物里有苍蝇、虫子之类的东西。这和现在的中国很像,但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和民众对这个事情是很积极的。
有人问作家福柯:“为什么现在写好书的人太少?”福柯说:“不是的,只是因为好读者少了。”为什么在中国,同样的事情发生以后,没有人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因为传统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伦理”二字,就是“相与之情厚”。中国人讲伦理,不是说你对我怎样,我才对你怎样,而是说我应该对你怎样。甲和乙,乙和丙,大家全都这么想,这个世界就平和了。
为什么传统没了?根子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因为“好人无几”。黑格尔还说过:“去哪里找我们自己?到历史当中去找。”可我们没有历史,或者说我们的历史是错位的。从哪里找你自己?1840年、1919年、1949年、1978年,哪些是时间节点?你会发现自己像一团烟雾一样,一会儿在这里出现,一会儿在那里出现。
社会在“痛”,所以“消痛”便成为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需求。即便痛之根源以企业一己之力无法消除,但也能在力所能及之处给社会和消费者一剂良药。
三种疼痛
分解开来,有三种疼痛让我们感觉最为揪心。一为“制度之痛”,二为“切肤之痛”,三为“心灵之痛”。当然,更多的疼痛属于“并发症”。
制度之痛它指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利益格局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痛。比如贷款难问题,无论中小企业还是个人,人们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因为银行既无动力,也无必要关注他们。加之民间金融长期以来遭到抑制,才导致无数微小的借款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我们和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领导人进行了对话(见《张化桥:我们是贷款行业的星巴克》)。
再如,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亟需改革,教育行政化、教学与应用脱节、资源分配不平等,加上连续多年扩招,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全社会之痛。安博职教由此切入,做起了大学生就业培训的生意(见《安博职教:淘金“就业难”》)。
有时候,发现制度之痛容易,创立一个商业模式清晰的企业也不是最难的事情,然而企业能否走在正确的路上,还要看经营者的远见与执行力。正如肖知兴教授所言:“要建立起微观创新的气候系统,创新者就像在打造孤岛,对企业家的要求非常高,成功的概率就更低。打破这种僵局只能靠一小部分人的坚守,价值创造型企业就像沙漠中的孤岛,当孤岛足够多时它便会连成绿洲,当绿洲连成片时它就是塞北的江南。”(见《别让创新者成为孤岛一对话肖知兴》)
切肤之痛指那些事关人之生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痛”。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百姓可能对“有机”“高端”等字眼未必很在意,他们其实要求不高,只求食品里不要掺杂化学品。就像一匹马,不要求多么精细的草料,只求草料里不要有石子。对于“蒙牛”和“双汇”身上爆发的食品问题,有人认为是海外股权资金在后面推动它们,疯狂扩张市场,导致它们无法完全控制源头,很大程度上,它们也是受害者。但仔细想想,资本没有那么大力量,资本有时候甚至是软弱而苍白的(宗庆后和马云诸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企业家个人,如果一开始做企业就是想当老大,就是“权力”驱动,就会出现问题。
有什么样的能量,负什么样的责任,权力和责任成正比,这是中国企业知道的,然而却总是很难做到。因此,我们选择上海一家肉食品企业进行调研(见《爱森猪肉:一家国企的“慢安全”》)。它从不做广告,是一家慢公司,10年时间,市场仅限于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口碑却不是一般的好。
只是让我们略感“沮丧”的是,这是一家国企。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印象,国营饭馆上菜可能慢点,服务可能差点,但料足,也还干净。民营企业开个饭馆,服务好,上菜也快了,但它可能用地沟油。如果你坚持品质,可能还没能等到市场的认可,就已经被不择手段的对手“干掉了”。国企看起来则更有“资本”做好事,摊上一个好的领导,稍微开明一点的人,绩效考核体系跟别的国企有些不一样,便能在“乱象”当中多坚持一点。这和帝制时代一样,赶上一个好皇帝,那个朝代就是好的。听起来沮丧的原因就是,当企业为减轻民众食品安全的痛点而作的尝试只是一件“碰巧”发生的事情,还不能对整个行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时,它的意义可能更像是针对癌症的一针止痛剂。
心灵之痛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婚姻矛盾、个人面对社会节奏的抑郁与失落、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某种意义上,心灵之痛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的,它是人之存在与社会现状的冲突,也可以说是社会进步必然带来的一种“富贵病”。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可以给中国很多借鉴的思路,因为它们的发展在前,“富贵病”的症状早已出现。如今在中国逐渐兴盛起来的婚姻咨询机构、灵修中心、心理诊所等等,也渐渐显露出了巨大的市场。
期待破茧
中国需要自上而下的力量,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后者显然更加“靠谱”,虽然所谓的社会痛点,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了企业家的能力范畴。但反过来,痛点和企业的经营行为又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其中可能蕴含商机,也可能蕴合危机。很多西方企业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有很好的实践(见《Madecasse:一家“蚯蚓视角”的公司》《大企业也能“痛点创新”》)。
零排放基金会创办人、作家Pauli Gunter(鲍利·冈特)在他的著作《蓝色经济》中有一段很好的话,全文引用如下:
“当婴儿诞生时,要穿过一个十厘米长的狭窄通道,肩部和胸部要经受巨大的压力,把肺里所有的液体排出。这样,才能吸入第一口空气。这股压力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虽然辛苦,带来的是降生地球的美好。对于所有生命来说,这都是相似的。当一只蝴蝶破茧而出,一个耐心的观察者会看到,它是多么费力地挣扎,甚至长达数小时,才能完全转化成拥有美丽翅膀的生灵。早先,有科学观察者曾经把茧子剪开,以便蝴蝶更容易地从紧包着的保护壳中出来,结果发现它飞不了,并且在这种无痛诞生后很快死亡。因此,压力可以看成是启动生命,催化各种复杂功能的关键,比如拉伸肌肉、心脏跳动输送血液、活动所有的关节及吸入和呼出空气等。危机是另一种形式的压力,激发我们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基于“痛点”的想象力,价值正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