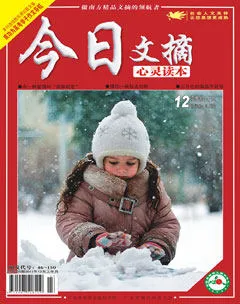痛
2011-12-24 00:00:00区乐民
今日文摘 2011年23期
梁伯是我的病人。他在内地出生,两岁的时候,父亲被入侵的日翠开枪击毙。粱伯八岁生日那天,母亲营养不良,患肺炎去世。
粱伯忆述:“每次找到食物,母亲只咬一小口,便把大部份给我。那时我真是太自私了,没有劝母亲多吃一点,只顾狼吞虎咽。”他至今依然自责。
“你不是自私,”我说:“而是年纪太小,也太饿。”
因着战争,梁伯痛恨日本,包括所有日本人。
冤家路窄,粱伯的邻居是个日本男人。偶然在升降机相遇,梁伯不至破口失骂,但把对方当作透明,从不打招呼。
“日本有坏人,也有好LrkVRpd6n6QOgDKG265Pbg==人;中国有好人,也有坏人。”有次我提醒梁伯。
“我知道,”梁伯道:“但内心的情绪,不是道理能控制。”
日本发生大地震和海啸,加上核电厂辐射泄漏,我问梁伯有何感想。
“我一直痛恨日本,”粱伯坦白地回答:“但不知何故,看了一幕又一幕的新闻片,竟然开始同情他们。家园尽毁,失去至亲,日本人哭了,我也哭了。今天我特地走去便利店捐钱赈灾。”
我不会鼓励人自找痛苦,但痛苦来临时,不妨想一想,它是否带着一些重要启示。
“还会当邻居透明吗?”我又问粱伯。
“昨天我做好水饺,按邻居的门铃,送了一些给他。过了一会儿,那个日本人按我的门铃,递来一盒精美的巧克力。”粱伯顿一顿,笑道:“我好像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