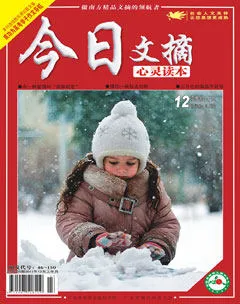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绘制揭秘
一层秋雨一层凉,九月到了。
每年,大约一到这个时候,在天安门城楼西北角的一个铁皮房子里,画家葛小光就开始忙碌起来。而他创作的作品,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肖像油画之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为了保持主席像的干净整洁,每年国庆节前,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都要换一幅新的。”专门研究天安门的军旅党史专家闫树军介绍说。
然而,虽然人们很熟悉这幅毛主席画像,但关于这幅画像的作者,即便是天天守卫在天安门前的年轻哨兵也毫不知情。
巨幅画像一人完成,“这个工作没人能替你干”
“咱们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高6米,宽4.6米。别的地方不敢说,至少这在咱们全国、甚至在东亚、东南亚一带,都应该是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不过,闫树军却告诉记者,天安门的主席像并非一直就是“最大”,“以前北京站也有毛主席像,高8米,那个像才是最大的。”
无论是6米高还是8米高,这些画像大都是由原北京美术公司的画师们承担的。但这些画师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同事关系,“北京解放以后,政府把北京所有画馆的画师都集中在一起,成立了这么一个北京美术公司。”刘杨介绍说。
不过,即便是集中了全北京的画师,北京美术公司中当时能画大型油画的画家也并不多,王国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64年,他接替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著名的肖像画家张振仕,负责绘画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像。但文革开始后,到处都要求挂毛主席像,全国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集中到了北京美术公司,公司里的画师们就算“连轴转”也很难满足各地的需求。最终,当时的北京市代市长吴德,特批了北京美术公司招一批学生,统一由王国栋培训伟人肖像画的制作。最终,刘杨、张春明等10人成为了王国栋的学生。
“这种大型肖像很不好画。”刘杨说,很多优秀的画家,在正常尺寸下都可以画得比他们更好,但一到这么大的尺寸,很多画家就难以找到他们在小画布上的感觉了,“一个鼻子比你的脸都大,有的人可能站在画布前就晕了,根本画不了。”
刘杨的画架上,放着一张毛主席的黑白照片,上面被笔画上了一道道淡淡的纵横直线,把照片分成一个个的小方格。作画前,刘杨会仔细分析和观察每一个小方格中的细节,再将其“放大”到巨大的画布上:“这张照片是王老师当年给我们10个师兄弟每人一张的毛主席当年的照片。这也是主席像的‘母版’。我们绘画的依据必须是这张照片,如果按照别人画好的肖像再去画,偏差会更大。”
绘制如此巨大的主席像,借助工具爬上爬下是家常便饭。“现在葛小光画画有了电动升降台,还方便一些。我们当时就是自己搭木头架子,跟工地上的脚手架似的。每次都是爬上去画两笔,跑下去看看整体效果,再上来画两笔,再下去看效果……来回地折腾。”刘杨说,当年画画时,他们有人还不慎从架子上摔下来过。
尽管麻烦又有一定危险,他们却不能叫助手帮忙:“这个工作没人能替你干。每个人对画的感觉都是不同的,哪怕助手就帮你画一笔,但那一笔可能会破坏你整幅画的结构,或者影响你整幅画的色调。”刘杨说,巨幅画像如果哪里出问题,改起来难度相当大,甚至可能需要重新画。
能画巨幅画像者凤毛麟角
虽然画巨幅主席像是个苦差事,但是,一旦自己的作品能有机会挂上天安门,画家本人还是会有莫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这种成就感,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据刘杨回忆,当时王国栋老师和他们师兄弟,都只是挣着一份普通的职工工资,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葛小光也同样显得有些“另类”。这么多年来,我还真没有听说过葛小光在哪里去出席什么商业活动,他就是安安静静地画画。闫树军说。
拜访王国栋的经历,同样让闫树军感慨万千:“老先生很简朴。退休以后他就一直住在那个又破又挤的大杂院里,光线也很暗,白天都得开灯。但老人本人却是无欲无求,他自己说:‘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干了一件事:画毛主席的像。”’
不过,王国栋老人的这些学生,并非所有人都一直还在坚持画画。“1997年的时候,当时喷绘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歌华集团就觉得我们绘画组再占这么大一个车间太浪费,就把我们都解散了。”但仅仅过了两年,1999年,歌华集团便又急忙“召回”刘杨,“当时是建国50周年大庆,游行队伍中的几张肖像画,歌华集团内部已经没人能画了,只好叫我们再回去画。”
这件事给了刘杨很大的触动,他才意识到:在国内,有能力画巨幅画像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本来计划转型去画其他风格绘画的刘杨,拽上师弟张春明,回归了巨幅画像的创作:“我们要是再不画,就真没什么人来画了。”
刘杨坦言,类似葛小光和他这样的画家,想培养“接班人”都是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但目前他们尚没有接到培养新一代画家的指令:“我们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是以后就不需要这种技术了么?直接用喷绘就可以替代了?”
“即便是替代,我们也觉得这种巨幅画像的技艺应该传承下来。”张春明认为,油画的魅力,是喷绘所无法替代的,“喷绘是死的,电脑设定成这样,机器就喷绘成这样。而油画是活的,是画家赋予其生命的,融合了画家自己的感悟在里面。”
既然不能擅自收徒,刘杨只能和张春明一起亲自来固守巨幅画像的阵地:“我们俩都50多岁了,估计画到60多岁,我们也就画不动了。我们的想法是:能守多久就守多久吧。”
天安门主席像的历代绘画者
据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透露,画像虽然年年换,但画像的画师却只有四批,分别为周令钊、辛莽、张振仕以及王国栋师徒。
周令钊笔下的毛主席还戴着八角帽,这幅画像被用在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
辛莽笔下的毛主席像正面短发,穿绿呢上衣。1950年,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应胡乔木邀请来到中南海,接受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曾是延安鲁艺美术教员的辛莽,挑选了一张毛泽东免冠、双眼略向上看的半侧画像。
然而,当巨幅画像挂出后,群众提意见了:“毛主席像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神向上。”辛莽随即又选择了主席一张基本正面、双眼平视前方的照片做摹本,这个版本的画像一直用到了1953年。
1953年后的毛主席画像是侧面像,主画师是中央美院教授张振仕。
据张振仕的学生,中央美院教授张孝友回忆,张振仕绘画功底深厚。他在窄小的侧院里默默作画,一画便是11年,直到1964年,绘制巨像感到力不从心时才停手。
1963年,北京市委在请示了党中央后,决定由张振仕、王国栋和另一位画家各绘制一幅毛泽东像,以作品决定将来由谁主笔。
一个多月后,三幅画像绘制完成,评选小组看中了王国栋的作品。经北京市市长彭真同意,1964年天安门城楼上开始悬挂王国栋绘制的毛泽东画像,他绘制的画像以毛泽东半侧面、双眼平视的照片为摹本。此后的毛主席像,都是由王国栋和他的弟子们完成。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举国哀悼。王国栋怀着悲痛的心情绘制毛主席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画巨幅主席像了。他把颜色调淡,把无限哀思凝聚于画布上。在举国追悼的日子里,城楼换上了新华社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追悼会后仍悬挂王国栋画的画像。
1992年,王国栋退休。而他早在1971年就开始培养的接班人葛小光,于1977年正式“上岗”。葛小光在师从王国栋绘制毛主席巨像的过程中,感到只照一两张照片临摹,很难体现伟人的神貌。于是,他便广泛搜集资料,先后收集了60多幅主席画像,从中筛选出十多张有特点的照片,编成集子,作为画像时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