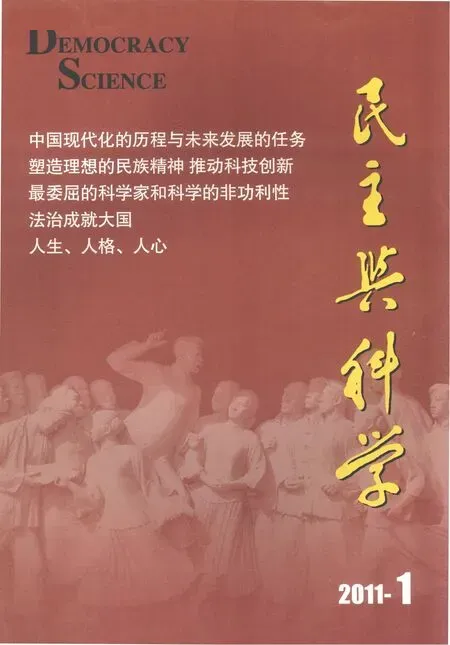科技界的利益集团形成机制:从寄生到共生
■李 侠
科技界的利益集团形成机制:从寄生到共生
■李 侠
近日看到一则有趣的研究成果: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进化》(Evolution)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在非洲一种卷尾鸟和一种画眉鸟之间反复上演着“狼来了”的故事。这种卷尾鸟自己并不寻找食物,而是经常飞到画眉鸟寻找食物的区域,大声发出有天敌逼近的危险信号,吓得画眉鸟纷纷丢下食物飞走,卷尾鸟便坐收渔翁之利。研究人员观察发现,它们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画眉鸟听见卷尾鸟声音后会更少地付出精力注意是否有天敌,而将更多精力用在寻找食物上。“撒谎的”鸟儿和“受害的”鸟儿之间进化出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科学网,2010-11-19)。由此,不禁想到笔者近十年来一直在思考的利益集团形成机制问题,这个故事恰恰可以为以往的论证提供一种基于动物行为学的解释。
利益集团原本是一个偏中性的政治学概念,一般是指基于共同的政治主张、信仰、道德或者利益等原因而集聚在一起的人群。利益集团的存在既有优点,也衍生诸多无法克服的缺点,对于利益集团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所指的科技界的利益集团是狭义的,专指那些为利益而结盟的团体。一旦利益集团形成,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路径与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从宏观上来说,利益集团通过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与引导;从中观层面来看,利益集团利用政策与资源的分配塑造集体的行动选择;从微观上,利益集团通过资源的具体分配措施,影响个体的行为取向。所以,科技界利益集团的形成,极大地降低了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败坏了科技界固有的学术范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活力,不客气地说,利益集团就是科技界的恶性肿瘤。
科技界利益集团形成的机制,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资本在缺少有效监督情况下的一种利益交换,它暗合了资本炼金术的游戏规则,即各种资本在学术场域中的兑换,以谋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现实中就是学术资本(以学术声望为表征)与政治资本(以权力为表征)以科技资源为媒介按照一定的比率进行兑换。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目前我们无法遏制各种资本之间的恶性兑换。一旦科技界的利益集团形成,将严重制约科技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益集团对中国科技整体发展造成的掣肘的结果。
反观中国科技界利益集团形成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也就是最近十余年的事情,我国自2000年R&D投入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1%以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持续快速增加,而相应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也正是这个期间,形成了当下中国科技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之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曾有名言:许多讨价还价都是关于“剩余”的分配问题。中国科技界的利益集团形成之初也大体遵照这个模式,作为资源管理方,期望通过压低项目预算,实现收益最大化,而项目申报方则希望通过一种讨价的交易实现项目预算最大化,进而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在缺少公开、公正的有效监督程序下,这种关于“剩余”的讨价行为就有可能演变为管理方的设租行为,这相当于寄生阶段,随着信任感与承诺的加深,安全与互惠的递增,获利行为就由单方寄生型向双方获利的共生型转化,此时,管理者开始真诚地希望项目执行者能够做出优异成绩,这样不但可以把租金固化,而且管理方可以获得行为合理性的证据。问题是,这种模式是以牺牲中国科技整体效率为代价的:一则,宝贵资源被用于了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滋生了众多权力部门的寄生现象,二则,科技界的这种共生型利益集团严重压制或剥夺了真正人才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导致科技发展路径被锁定在一种低效与缺少公信力的轨道上。
中国科技界的效率损失大多来源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共生现象,解决之道就是彻底切断各种资本之间的共生交易,相对于科技界的寄生现象来说,共生现象的处理难度更加复杂,因为利益集团之间发展到共生阶段,已经能够通过部分影响政策以及资源配置模式,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证据,而很多业内人士也已经被迫习惯了这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环境,甚至已经对此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感,这就是相当棘手的科技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表现。对此,除了制度措施的纠偏外,对于利益集团中的个体成员来讲,即便基于个人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也要尽量做到有道德的自私。因为节制对于所有理性人来讲都是一种美德。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