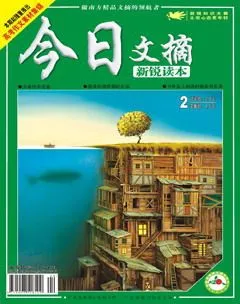张船山把酒审大盗
张问陶,号船山,清中期著名诗人。船山先生有一次去省城历下——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南,晋见新到任的巡抚大人,这位巡抚一向看不起汉官,偏偏船山也恃才傲物,两人不欢而散。
巡抚责难船山
这位小肚鸡肠的巡抚大人想要报复张船山,就把藩台请来商量。
藩台跟船山私交不错,他立马打圆场:“他这人是有点呆气,但在百姓中口碑尚好,一向不误民事。”
巡抚有点不高兴,打断话头道:“你说他不误民事,咱就考验考验他。最近不是抓到个大盗吗?听说这个家伙桀骜不驯,几次翻案,迟迟不能审结。不如就让张知府去审审,如果能审结,他还回去做他的知府,如果审不结,就将他登上邸报,送到京城,好好臊一下这个翰林学士的脸皮。”
藩台无奈,转来告诉船山。船山一听,笑道:“这个容易。”于是到按察司接手案子。
按察司的官员问船山几天可以审结?船山道:“这种小事,三天足够了。”又问审案需要哪些刑具?船山更是哈哈大笑:“刑具不急,但上好的金华火腿、绍兴美酒万万不可少。”
船山喝酒审案
第二天一早,船山在按察司要了一间静室,施施然坐到炕上。一张小桌子上,上好的金华火腿、绍兴佳酿早已准备妥帖。船山吩咐将大盗带到跟前跪下,左手端杯子、右手随意翻阅着案卷。
船山美美地咂一口,赞道:“果然好酒。”又拿起一大片切得薄薄的火腿肉,有些夸张地纳入口中,这才回头问那大盗:“你是郯城人?”
“是的。”大盗回答道。
“今年多大了?”
“三十七。”
“住在乡下,还是城里?”
“住城里。”
“你父母还在吗?”
“父母都去世了。”
“有兄弟吗?”
“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有老婆孩子吗?”
“有两个儿子,大的十八,能够打猎;小的十三,还不会打猎。”
“你以前做什么事的?”
“我无业。”
藩台和按察司的官员都很好奇,船山先生才华横溢、词锋犀利,他们都想知道他是如何办案的,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哪晓得他竟然问了这么些琐碎之事,跟案子半点不靠谱。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是一头雾水。
第二天清早,船山先生在好酒好肉的伺候下,重新开审。
“你是郯城人?”
“是的。”
“今年多大了?”
“小人今年三十九,明年满四十。”
“你是住在乡下,还是城里?”
“住乡下。”
“你父母还在吗?”
“父亲去世早,母亲改嫁了。”
“你有兄弟吗?”
“兄弟三个,我行二。”
“有老婆孩子吗?”
“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还小。”
“你做什么事的啊?”
“我种田的。”
屏风前后都是原班人马,藩台等人听船山先生所问,跟昨天一模一样,都捂着嘴偷笑。
盛名之下无虚士
第三天,藩台跟按察司的官员沉不住气了,他们截下船山,问道:“这可是第三天了,案子不结,抚台大人跟前没法交待,不是开玩笑的,先生到底怎么打算?”船山仍是呵呵一笑:“下官向来不打诳语,今天下午一准审结,诸位大人但请放心,看船山手段,只是这酒肉不可断了,常例刑具也须派人备好。”
敢情先生今天要动真格的,几名小官偷笑着去准备了。船山从容步入客房,喝酒、吃肉、问案。
“你是郯城人?”
“是的。”
“今年多大了?”
“去年四十,今年又添一岁。”
“你是住在乡下,还是城里啊?”
“有时候住城里、有时候住乡下。”
“你父母还在吗?”
“母亲还在,刚过七十。”
“有兄弟吗?”
“有两个哥哥,都去世了。”
“有老婆孩子吗?”
“有个奶娃子。”
“你做什么事的?”
“没田了,有时候打鱼,有时候砍柴。”
拉了三天家常,这大盗整个把船山当一傻官。屏风后面有人“噗嗤”笑出了声。
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问到了半下午,船山忽然命令撤下酒肉,召集皂吏,备刑具听用。
张船山整衣端坐,喝道:“本官正式开始问案。我已查阅了先前的讯录,你罪状确凿,为何每次翻案无常?”
大盗辩道:“大人明鉴,小的确实冤枉啊。”
船山拍案呵斥道:“住口,听人说你反复无常,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本官审你三天,与你说了三天闲话,你三次回答,次次不同,寻常琐事尚且如此反复,何况所犯罪行。你若再要狡辩,这三天的具结口供在此,本官定你个反复无常之凶徒,那时大刑加身,立毙于此也是你咎由自取。你且想想,还要自讨苦吃吗?左右,与我大刑伺候。”两边皂吏抖动刑具,公堂上“哗啦啦”一片。
这大盗本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徒,进刑堂直如家常便饭,但从未遇到过张船山这样的官儿。三天连审之下,已是头昏脑涨,此时只愿眼前这位老爷赶紧离开,急忙磕头如捣蒜,情愿实招,再不翻供。船山大喜,命书吏呈词画供,其案立结。
屏风后面的一干人面面相觑,叹服不已。藩台后来报知巡抚,巡抚也叹道:“盛名之下,果无虚士,想不到张船山有如此才干,本官再不敢小看这帮书呆子汉官了。”
张船山智审大盗一事,从省城迅速传遍齐鲁大地。
(何子易荐自《旧闻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