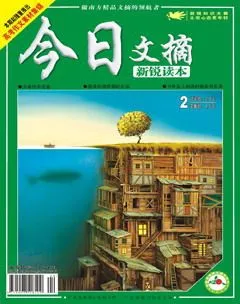我憧憬诗意的晚年生活
我的父母大人,他们都老了,母亲78,父亲82。母亲的身体还行,父亲不行了,他的脑子像一朵坚强又无法抵抗枯死的花,在病病歪歪地拖腾了几年之后,到了去年夏天,彻底告别了记忆,连我都不认识了。我现在每次回去,父亲总是拉着我的手,要我给他的老二打电话,让“他”回家看他。而我,就是他的老二。
父亲犹在,但形同虚设,他再不会给我打电话,不会对人夸耀他老二是如何有出息,不会对我数落母亲是如何小气不给他钱花,不会要我给他讲外面的稀奇,不会,不会,什么都不会了……他对我笑,母亲说是傻笑,他对我哭,母亲说别理他,他对着一只竹蓝子喊我的名字,而当真正面对我时又无动于衷,不会起身迎接,不会问寒问暧,当我告别时不会挽留,不会一如继往地对我说:路上小心一点,没事就多回来看看我们。
人在什么时候都有定向的付出需求,我这个年龄——人到中年,就是想为年老的父母捧出一颗孝敬之心。事实上,我也是这些年心里才开始装父母,以前忙这忙那,经常把他们忘了,去年我下了狠心调回杭州,就想最后陪陪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打上我疼爱印记的晚年。可我的父亲已经感应不到我的孝敬之心,这是最令我心酸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弥补。老人现在在我心目是被放大的,我愿意对老人抒发感情,也许这暗示我心理年龄老了,也许是因为我向老父亲表达爱的路被阻断了。
少于露面的我曾去艺术人生做了档节目,听宣传部负责联系的人说,这是一档敬老节目,重阳节播出,于是答应去了。节目做了一个下午,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别具一格,嘉宾阵容强大,老中青,文艺体,各路名流齐集良渚博物馆,在杭州金秋十月的桂花香气和明媚阳光下,大家畅谈人生的智慧、箴言,寻求岁月的真情、真理,各抒己见,各表心愿,对我来说是扎扎实实上了一堂“人生之课”。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喧嚣了,有些基本的问题都在我们匆匆的脚步中被踩踏到了泥土里,有个机会把它们翻出来看看,大有必要。正如印度一句谚语所说:请慢一点走,等一等灵魂。
节目中有一道“必答题”:想到老年,你的“关键词”?我答的是:诗意。我总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太没诗意了,我们搭乘的是“欲望号”街车,我们居住的是“钢筋水泥”,我们吃喝的是“三聚氰胺”,我们身处于“离婚时代”,“潜伏”在办公室里,时刻面临着“暗算”……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我们做的梦都沉重如铁,毫无诗意。
什么时候我才能告别这一切,让诗意回到我的身边?我思来想去,也许只有等年老了。为什么现在不行?这既是我个人的问题(局限),也是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不相信诗意!
我憧憬有一个诗意的晚年生活,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我爱我父母一样爱我,即使我像父亲一样失去了记忆,感受不到,我觉得那也是充满诗意的。
(无花果荐自《文摘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