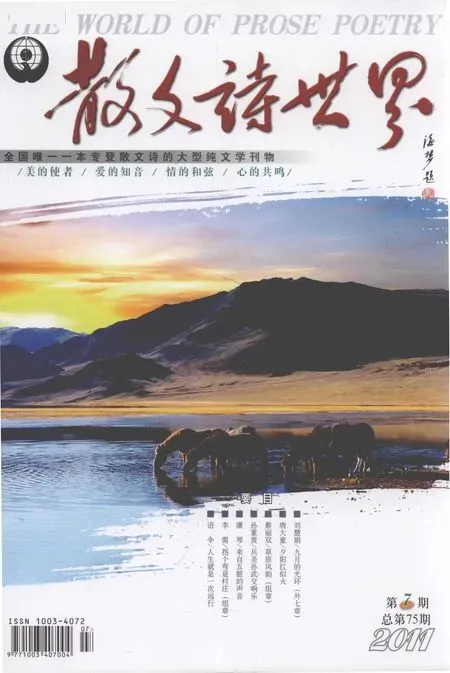人生就是一次远行
上海 语 伞
准 备
所有的思想都围坐在一起了。
我咽下告别的话语,推开窗户让空气与勇气对流。
行李已放在最方便的门旁,前世的乡愁突然夺眶而出。
我要首先准备一场暴雨,用雷鸣和闪电警醒自己的影子不要倾斜,用狂风刮走脉搏里的噪音,用大雨冲尽内心深处的污渍。
其次是准备一份足够重的孝道和感恩,选择夜宴前叩拜父母和先祖。落叶还要归根,我要随身携带祖辈们头顶的月色。
最后,准备一个健康的晴天,没有半处伤痕的阳光,一片一片往前铺。
伸开双臂,我看见人类的光阴密密麻麻,左邻右舍的鞋子,都睁着大眼睛。
我的鞋子,它们也一直醒着。
地平线
心上悬挂的地图,它们比宇宙的目光还要辽阔。
这时,我站在都市的立交桥上,环顾四周,车辆和行人都在倾诉匆忙,有如纵横的波浪涌向我,推着我——
我前行。奔走。攀跃。在空气中寻找力量……
光明从地平线上升起,好兄弟,好姐妹,我们就享受追赶太阳的幸福?
“本来我是愿意选择一匹马的,而且不打算举起鞭子。”
你们也同时这样说过。
但是,闲云野鹤只是历史里的典故。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多么习惯赶赴机场。
天地一阵轰鸣,全世界就踩响脚步。
前面的氧气和果实,美酒和乌托邦,它们在任何国度都气候适宜,它们生长在每个人的内心。不同的是,一些隐于丛林,一些露于山巅。
昨天已经准备很久了。
地平线也越数越多。
被我称为兄弟姐妹的亲人,假设他们还在睡梦中,白云的白刚醒,我就与上天商定——
他能不能把最好的起点献出来?
想或者可能
心与大脑同时涌动,我,一直在想。
在乡村的庭院里,我面朝清晨,想着城市与心比高的楼群;在城市的阳台上,我背向夜色,想着南山对面东篱下的菊花。
我有亿万种想法,闪过。连续。重复。
白天去叙事,晚上种星光。
“如果可能,我一定要抓住!”
亲人们还站在高处目送。一挥手。再挥手。我,已经出发——
从情谊的源头,走向远方的热血和烈焰。
大地上一切微小的生命,都在活生生的命里日夜兼程。
全身的筋脉,它们如何高尚,如何澄澈——
谁也没有理由阻止大脑的勤劳。
想着,就可以擦亮打火石,在黑夜里做白日梦。
辨 认
出了门,就要学会辨认。
牛羊还在山坡上,它们背着黄昏,悠然的是爷爷?他一直缓慢地裹着叶子烟。他没有在意他的子孙们因为一条路的方向,在十字路口踌躇了很久。
人生有多少个十字路口啊。
一堵墙的善恶,一个曲折的得失,仅凭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是啊,我走着走着就碰了壁。
耐心红肿了。
我不知道在哪里转弯最好,在哪里翻山最近,在哪里休息不至于耽误时光。
紫蓝的鸢尾花是梵高心中飞着的蝴蝶?我望着他的自画像。
有风景的地方,就有迷路的眼神?
这一路的雾霭,它们确实扰乱了我。
我就要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在弱点暴露之前,鲜艳的前方,终于,它又开始闪烁。
握 手
我认识了你,上天就赋予我们相见和离别的理由。
在远行的途中,我不断地和有缘人握手。
一些手握暖我,一些手握疼我。
那些使我疼的人,我怀着仇恨诅咒过他们。
那些使我暖的人,我害怕他们有一天会弃我走远。
我不断地信仰,又被信仰欺骗;我不断地绝望,又在绝望里重生。
闲看过的花开花落,它们是我际遇中珍贵的亲切?
正如人群中那些缜密的陌生的眼睛,如果少数的眼睛会对着你说话了,他们一定是你际遇中珍贵的亲切。
“我一直在人间!”真情说。
那么,你一定要握紧。
像海水握紧沙滩。
进行曲
我的步伐不倦。
我用普通话与各种语言交流,我用表情与神态交流,问答犹如一种音符。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距离,只是一颗心的距离。
我穿着触景生情的鞋子,在中国的体内,在亚洲的腹部——
把脚印伸向整个世界。
外公当年脱下军装的时候,不会说汉语就爱上汉语的人不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今,那些说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以及阿拉伯语的人们,都流行读《论语》了。
与我同行的人!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读得更好。
我越过的海洋,它们有些已变成湖水,有些仍然用波峰浪尖敲打我的足跟。
我又背诵了一遍乡愁。
值得我敬重的父辈和兄长:
“我不会像一片叶子那样轻易落下……”
在近处
想望见就望见了,一切都在近处。
儿时天空以外的天空,如今就在眼前抽枝发芽,长出最幸福的彩虹。
我路过的菜园,恰似父亲种得最春意盎然的那一垄。我的满足远远胜过父亲,他还期待来年更硕大的喜悦,而我,守着一片叶子想结果,然后剥下核,珍藏永远的种子。
把种子捧在了手心里,我一定要让它比泥土更温暖。
再冷也不去冰凉它。
故意找茬的霜雪,就和外婆的鬼故事一起送远吧。
哼着近处的歌谣,我一边行走,一边安静——
月光,青苔一样地匍匐……
知 音
你怀抱高山,我怀抱流水。
我们一定要遇见。
我们不谈子期和伯牙。
我们谈在浮躁面前如何不放弃干净的理想,我们谈在和平时期如何热爱自己盛装的祖国,我们谈人心所隐忍的一切疼痛,我们谈前世今生的沉醉和光芒,我们谈……
然后一起为生老病死,叹息!
我们把说出来的叫听心,没有说出来的叫境界。
朝露正浓也好,日落西暮也罢,我们走累了,就把俗世中的热爱暂时丢进历史,让一壶素茶分清精神和肉体的界限。
不一样的方言、祖籍、肤色、习惯以及悲欢离合的细节……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山水如画,心灵重叠,我们的琴音一定要长生不老。
探 险
我像削苹果一样削自己。
母亲一定很疼。
她嘱咐过我,如果口渴,就不要再向荒无人烟的沙漠走去。
除了讨厌拥堵,我和骆驼一样,所有的毅力都来自一片理想的绿洲,我要寻找心中最甘美的泉水。
汗流了很多,我的满足不讲述过程,我的遗憾不说出真相。
前面还挂着残酷的宝石,锋利的花雕。
“亲爱的远方,我爱上你了。”
是,我执迷不悟。
我追着巨魔的身影,二十四节气被我打乱了——
乡亲们正在耕种什么蔬菜瓜果?
邻居们穿着什么衣装上班?
我祈求他们的平凡岁月再香一点。
我走得再远一点。
高坐光芒
听着真实的钟声,在人群里,我被托举到光芒之上。
这一路险象环生啊。
我无数次在风雨中颤抖,在曲折中揉淤血,在浪尖上晒伤口。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多少年来,踏平了大地的哥哥,他一直教我默诵。
石头的骨髓里终于装满了水。
我坐在高处,听四面八方传来环佩之声。妹妹说,母亲初一十五都要上香,“请菩萨保佑!保佑。”她一定用双掌使劲握着心。
我的亲人们,他们的爱永远没有句号。
可是,高处不胜寒啊。昔日的知己不再是知己,志同的朋友瞬间仿若仇人,我开始主动认养孤独,我突然少了很多简单的自由。
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每天只需要几粒平凡的粮食,但我,还是时刻担心会从光芒上摔下来。
低生活
从角落的微尘里把自己请出来。
尔后,满面春风地想家。
蔬菜,饭桌,旧椅子赶走过的疲惫;唠叨,争吵,小算盘放大过的幸福。唉,那令人厌倦的热爱的生活,它竟使人眼睛湿润。
想起这些,我就情愿蹲下,为自己越来越多的杂念捉害虫。
深居简出,饮白开水一样无色的氧气。
保管好多余的善良。
既而说到一个人的宿命,早年无辜的理想,如今随手可触摸的空口袋……咳,有什么关系呢——
我水中有鸟,天上有鱼,他们有吗?
在雨中
我一直都在不停地切割雨水。
粗壮的,细密的,仿佛已用尽来生的光芒。
有时被闪电无意恐吓,有时被雷鸣当头一棒,有时一滴雨夹着两片霜雪。
我渴望一把伞从天而降,在我生命里撑开蔚蓝的天空。
一路仰望,雨,仍然无孔不入。
渐渐地,我开始平静地适应命运,并且暗暗庆幸,那沉重的硕大的冰雹竟没有砸到我避寒的山坳。
拽着七情六欲的绳子,我悲喜交加地赶路,我努力让自己的喜悦大于自己的悲伤。
那些同样在雨中和我并肩行走的人,当他们不小心滑倒时,我会立刻摆出拐杖的姿势,挤出哪怕是苍白无力的语言,去搀扶他们。
就这样,把雨中散步当作是上天的恩赐。
或许哪一天,天空撒下的都是神奇的花粉。我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另一种叫做浪漫的雨水。
遇见夕阳美
我倘在人间。
眼前的江水,泛动我浮生所想。如此真实!最美的烟火,不过是此刻的天涯海角。
这动静鼓瑟的黄昏,抹去上半生的最难将息。世界简单到,你只能看见风的手指,缓缓地拂过江岸芳草的十面埋伏。
可以减去平日的忧郁、沙尘和碎裂的光亮。
可以消融暗浊的冰块、乱石和所有饿与痛的骨头。
望得见的那叶扁舟,搁浅的是宁静,还是离愁?
不重要,已不重要。
亲人,仿若近在咫尺。
落日。向西。再向西。太阳的种子,已在大地的花蕊中浅浅地分娩。火红的晚霞,从天空中溢出来,远处的房舍如画,近处的流星撞击心弦。
我忍不住赞叹,如儿时信手指向如勾的弯月。天啊,我感觉到自己,第一次,真正犯了忌。
生命中的美,从来就不可触摸。
我触摸了,是不是就注定,我已经可以从这喧闹的人间悄悄地消失?
桥
扛着姓氏和脉搏的声响,我们计算——
人的一生,究竟要走过多少座桥?
俯身大地的,横卧山涧的,在胸怀上弯腰的……我们将步伐献出,从犹豫,到尝试,最后,收起疲倦的翅膀,在案头写下花间一壶酒,我们终于与桥对饮。
踮起生命可承载之重,我们垂下高傲的头颅,用内心巨大的虚空,思念桥。
桥的影子,其实无处不在。
偶然的一次握手,或者不经意的一个眼神,这些潜伏于尘世中的生命细节,它们虽比尘埃落地的声音小,却又比跨海大桥还要长。
很多时候,我们在别人修筑的桥上走;有时,我们也为别人修筑抵达远方的桥。
一座桥,可以在眼中显山,也可以在心里露水。
桥啊。让我们望着一本旧得发黄的日历,默默地感受我们的皱纹和白发,幸福地追忆那鹅卵石般油亮光滑的青春。
数字远比人生漫长
数字远比人生漫长,从正到负,从负到正,三生三世也数不尽。
神话可以合起天地,寓言可以从死亡中醒来。
露水滚落,影子站立。
谁能把灵魂的形状告诉我?
前世的足迹和抛掷,今生的乡愁和欲念,把我吸进去又呼出来,呼出来又吸进去,我无法摆脱它们,谁能摆脱它们呢?
说到人性的唯独和钟爱,每个人的内心瞬间就会显出原形。
比如语伞遇见一抹紫香,就突然弄丢了庄子的圣境。
以淡紫打开,暗紫关闭,整个空间里的事物就长成了一双有魔力的手。
从任何一个角度,都绕不过啊。
望望远方,找处伤口说:“有一种数字不等到数尽,越数越少就是残酷呢!”
转身,把夜色含在嘴里。
我思索,明天的早餐能不能大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