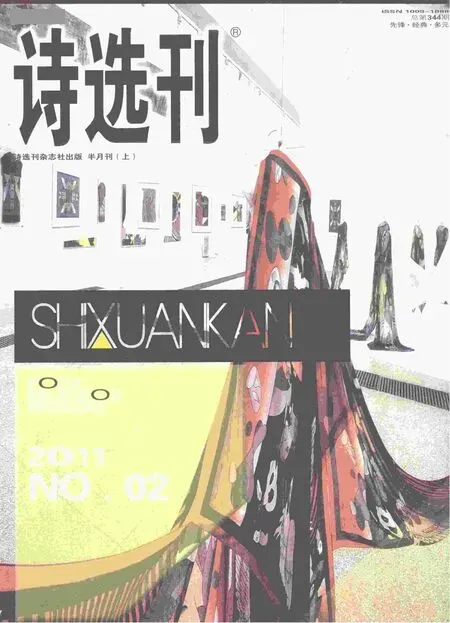重新恢复诗歌的难度
□刘 波
重新恢复诗歌的难度
□刘 波
1
如果说诗歌的隐喻破坏了朴实的日常生活经验,那么直白的说辞恰好能够接上诗人形式记忆的链条。直白与口语化本身并非诗歌之大忌,而关键就在于将无聊口水当作了口语,将俗浅平庸当作了直白,这是口语诗歌为很多人所诟病之处。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初学诗歌者,并没有真正从本质上理解口语诗歌的精神,从而简化了其形式,只看到了口语的表象,乃至误解了其意义。一旦如此,真正的口语诗就会被取消难度,从而变得浅白而俗气,毫无诗意,成为“口水”。
至今,我仍然相信评论家谢有顺说过的一句话:“诗人一旦取消了写作的难度,并且不再对语言产生敬畏感,真正的诗歌必将隐匿。”现在很多诗人就是陷入了对语言的过分轻视甚至是随意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这个快速成名的时代获得了短期的声誉,然而,这也透出了诗人对诗歌写作缺少一种敬畏之感,一份为语言与诗意而坚持探索的耐心。有过诗歌创作经验的人都清楚,灵感有时就是诗歌写作的催化剂,它由诗人内心喷薄欲出的那一刻,情感裹挟着的语言之美就呈现出来了。然而,对于真正的诗歌来说,灵感的出场只是一份诚挚诗性的调节剂,而不是诗歌艺术的全部。
除开纯粹的词语排列,语言所携带和具有的精神质感在诗歌中的作用不显自明。那些夸张的修辞,也并不能给诗歌的创新带来多少实质性的突破。所以,许多网络诗人热衷于以诡谲或调侃的姿态来为诗歌叫魂,但总是事与愿违。不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标新立异,还是想独出心裁,不对自我和人世发言的文字,不与日常和生命作对话的思考,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的分行游戏。放弃了担负美学与精神责任的写作,其结果可能就是将诗歌的难度不断降低,将诗歌的门槛彻底地削平了,最终与普通的散文文字同趋于消失。
米歇尔·福柯说:“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不断超越自己的规则又违反它的界限并展示自身。在书写中,关键不是表现和抬高书写的行为,也不是使一个主体固定在语言之中,而是创造一个可供书写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1)福柯所提出的,更多的是指小说创作上的技巧和观点,而诗歌写作,在很多时候同样适合于这种富有想像力的创作理论。
现在的有些年轻诗人,一天要写十首,乃至二十首诗歌,数量成为了衡量你是否是著名诗人的标准。我的一位年轻的诗人朋友跟我说,他曾在网吧里上网,几个小时能写十多首诗歌。当时,我很惊讶: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能叫诗吗?后来,我对其有了一种“同情之理解”:这是物理时间和写作环境对他造成的压力所致,在网吧里,他不得不快点写,将一时的心绪全面地调动和释放出来,形成文字,否则思绪一过,灵感全无。但是,这并不是成为我们取消诗歌写作难度的借口。因为,正是这种没有耐性、没有沉淀的写作,如今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导致了诗歌写作的大面积被丑化,被段子化和娱乐化。诗歌写作一旦变得过分功利,那诗人的创作大限即会渐次到来,因为诗歌所赋予我们创造的权力,诗人却丧失了运用权力的视野和眼光,任欲望摆布,而亮色全无。功利的人,会过度依赖灵感的现身,而真正的经验,却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今天的诗人如此,古代诗人又如何呢?唐代诗人贾岛则在《戏赠友人》一诗中开篇就说道:“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这是高产诗人的日常状态,虽然有点夸张,但还真有其人。他们就是为诗而生,为诗而活的。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不求最好,只求最多。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贾岛是怎样劝友人写诗的吧: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
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
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
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
每天保持写作,是一种好的习惯,但并不是所写的全部文字,都能成为优秀的作品而流传久远。其实,好文字,最终还是打磨出来的。古今中外的文坛上,莫不如此。诗歌本来是一种缓慢的语言艺术,但是现在在很多诗人那里却成了比速度和比数量的文字游戏,包括一些早已成名的诗人,在浮躁风气日显的当下,也耐不住寂寞了,也开始大批量地创作甚至是炮制垃圾。在网络上,看谁写得多,在博客上,看谁更新得快。与快节奏的生活搭上节拍,与消费主义的全球化潮流接轨,最后,多数人都被裹挟着进入到混世的行列中时,诗歌也就堕落成了缺乏艺术质感和常识性的文字表演,缺少了纯粹性,也没有了可信度,相应地,诗人成了小丑,诗歌也就成了笑话。
2
如果说革命就是一种冒险的话,那么很多诗人现在对语言的革新,就成为了一种不折不扣的铤而走险,如果这一步险棋走得好,可能就会让诗歌从此旧貌换新颜,而一旦把握不准,就会让诗歌走向彻底的庸常与俗气,从而让这种有尊严的写作失去其所应具有的难度。诗歌的语言自有它隐秘的内在肌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可以毫无规则地组合成为语言的精华。而恰恰就是那些自我感觉很好的诗人,却破坏了通往语言创造内部的那条隐秘通道,以一种过于随意的粗鄙方式,取消了诗歌写作的难度,进而将其降低成为哗众取宠的表演。他们带着先入为主的概念在写作,要么打着复兴传统旗号,让诗歌成为复古运动的道具;要么以极端狭隘的语言方式,寻求一种刺激和热闹;要么就是打着拓展知识的幌子,将诗歌“做”成了无人能够进入的高高在上的城堡。
其实,诗歌有时候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还原的,它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现实通过语言创造的形式,还原成为一种有情感力度与理想价值的存在。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他应该是语言的炼金术士,而不是曲高和寡的文字魔法师。所以,经典之作,它不仅仅是指向语言的层面,还应该指向精神与思想的内部,进而深入到人性与历史的层面。缺少历史感的诗歌,是无法在语言创造的基础上获得丰富感受的,因为它匮乏了一种能让我们寻找灵魂栖居地和思想落脚点的精神力量。
因此,在对待诗歌语言的问题上,诗人与批评家之间的争鸣,都只是停留在口语与书面语分歧的层次上,纠缠于口语与书面语哪一种能入诗的伪问题上。其实这对于诗歌写作来说,都是很外在的命题,不论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只要能创造出一种汉语之可能,一种思想之美,这都是诗歌写作最基本的路径。对于诗歌的语言问题,并非像一些年轻诗人所说的那样始终悬而未决,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对语言创造本身的理解。就像朦胧诗人杨炼在谈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时,针对长诗写作曾经说过的一样,“它必是一件语言的观念艺术,且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2)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正是诗人对诗歌写作一种理想的要求,也是先锋诗歌所应具有的艺术价值。语言和技艺实验的过程,或许就是挑战难度的过程,一级一级,循序渐进,诗歌的先锋精神与创新视野自会拓展和呈现,无需我们刻意为之。过分注重表演性的诗歌,让人没有信任感,终究经不住时间的磨砺与岁月的淘洗,而成为过眼云烟。
毕竟,诗歌的语言相比于小说和散文来说,是最具独立性的,它应该是文字难度的测绘仪,是思想启蒙的衡量器。任何一个诗人,都有责任为诗歌语言的个性展现而去体验,去努力,去创新。但这种创新并不是毫无原则、毫无逻辑地去拼凑,去另类、牵强地制造文字垃圾,而是为诗歌写作的突破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形式上的钻研,精神上的探寻,怎么写与写什么,都是当下的诗人们必须考虑的命题。勤奋,并不是说要一味地埋头写,而没有好奇心和想像力的参与,对这些诗歌的表象与内里全然不顾。优秀的诗作,必须在技艺的基础上呈现思想的困惑与精神的境界,这样的写作,或许才会让人充满期待。
真正的诗歌应该是逐渐向下的,因此,其语言方式也应该是向下的,而我们现在的很多诗人却喜欢做空洞的升华,没有美学压力,没有语言纠结,高高地飘浮在上面,沉不下来。沉不下来的后果,就是导致诗人在精神与语言上不断地自我膨胀,既无反抗的鲜明立场,也不承担创新的真精神,而是频繁地制造流水线上的话语工业产品,切入不到真正的汉语创造之美里,最后蒙蔽了诗歌的自由之真。
诗歌不仅有它的精神难度,更有它的语言难度,诗人一旦取消了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让诗歌滑入极端尴尬的境地。当下的先锋诗歌,应该在不断锤炼语言的地基上,呈现出令我们不知所措却又割舍不下的“矛盾”之态,呈现一种人生“无解”的困惑之美。这样的诗歌写作,看起来不难,但实际上并非易事。别说是刚出道没多久的新诗人,就连那些有着几十年诗歌写作经历的老诗人,也未见得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它需要你有在写作和思想上有失败主义的经历,而不是以一种唯我独尊的专制来保持单一的格调,也不是以自我阉割的方式来作思想的消声,它甚至要求一个诗人具有“苦行僧”般的抗拒诱惑的意志,专注于抒写人生常态之外的那些主题,去呼唤语言的力量,去发现深远的意象,去破除陈词滥调,将潜伏在人生历程中的可能性激发并书写出来,这才是当下先锋诗歌的正途。这些可能性,并非是主流的样态,或许从一开始它就是边缘的,恰恰是书写这些带有边缘意味的生活和存在,就成了诗人超越主流的难度。诗人王小妮曾经说:“真正的诗意和真正能够追求到诗意的人必然边缘。”接着,她对这个问题作为阐发性的解释:“诗人和诗必须心甘情愿地呆在边缘,这是必须的,你如果是主流,你就不是诗。因为只有边缘,才是稀有的、独立的,没有被另外的东西干扰影响,你的脑子始终保持着的是新鲜感,……也是悲惨的。而悲惨是一种美,在有的时候。”(3)这是让很多诗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一种境界。“心甘情愿地呆在边缘”,对于当下处于消费社会的诗人们来说,很难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因为诗人作为凡人,诱惑太多,变化也太多,这样的做法甚至有一种“自断退路”的决绝之意。其实,从诗歌创造本身的角度来看,正是这样的决绝,才是诗歌免于成为主流传声筒,而重新成为诗歌恢复难度的关键。
在恢复诗歌难度写作的问题上,诗人也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放平姿态,带着质疑的立场和独立的责任,尽量以平实的语言去接近自我的灵魂、人世的中心,让诗歌写作自身就呈现出清晰的路径,这正是我们让诗歌走出乌托邦困境比较有效的方式。
3
诗歌是表现个性的语言艺术,因此,诗歌应该是一个人所写,它不可能像小说乃至剧本一样,绝无合作的可能。这种拒绝合作的精神,恰恰促使诗人应该具有孤独的勇气,要敢于突围,敢于创新,敢于对腐朽或陈旧的抒写经验说“不”,敢于将久已失去的理想主义光彩重新纳入诗歌抒写的范畴。诗人们在孤寂的氛围中需要追寻的,恰恰也是被世俗之人所抛弃的生活中诗意的一面,即便它们已趋幻灭,已经消亡,其话语风度仍然存在。
甚至夸张一点说,诗歌有时候是需要一种神启的动力,哪怕一个不起眼的词语,一个简单的句子,它们也是诗人在灵魂的冲突中,对人事所完成的一种神秘的解读,这种解读用语言的幽光照亮了隐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独特的存在。诗歌的天才,有上苍赐予的语言天赋,而更多的,则还是自我经营的个性展现,唯有独特,才有风格,唯有创新,才有难度。诗歌的难度,一方面在于想像力空间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还在于当下诗坛对诗歌标准的取消或降低,从而导致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盛行以来,很多诗人都沉湎于写身体与欲望,而对语言的敏感似乎变得不再关心,甚至麻木,当然,其诗歌思维也就相应地变得迟钝。再加上消费社会的来临,面对诱惑与名利,对写作的反思与审视已变得不再具有核心意义,诗歌写作的随意性也就甚嚣尘上。
杨黎和伊沙,作为我一直以来所看重的诗人,他们的写作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人印迹与风格特点。杨黎作为“非非”诗派里的重要诗人之一,其对诗歌语感的经典性还原,对语言简洁化的精彩运用,曾引领了“第三代”口语化诗歌写作之风潮。而伊沙作为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领跑者,其诗歌在口语中带有的解构特点,也为先锋诗歌的传统创造保留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他们的写作,在新世纪之后都面临了问题。杨黎提倡概念性的废话写作,而伊沙也有重复自己之嫌,对于他们的口语化写作所形成的传统,在网络的放大之下,以及在由此传统所影响的一批年轻诗人中,都出现了诗歌写作“口水化”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无难度写作的困境,可以部分地从杨黎和伊沙的诗歌中找到症结所在。杨黎的写作,虽然在语感上有其独特性,但是其格局与气象,还是略显狭小,而无历史感与开阔性。他除了语言之外,对这个世界的哲学思考是简单的,不够的,甚至是匮乏的。
诗歌写作的驾轻就熟,能代表一个诗人的阶段性成就和高度,这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但是,它也可能是创造性僵化和停滞的起点。在创造性上没有挑战了,我们的诗意是否还有转型的空间?走不出重复的圈子,我们的诗歌写作还有无必要?王小妮说:“今天的诗意,对诗人的要求更高了,当什么都可以写成诗的时候,你必须得抓到真正的诗,这个时候,它是有相当难度的,而当一个套路给你,谁都使用的时候,诗意可能被理解为一个格式了。”(4)当我们普遍都认为自己写的就是最好的诗歌时,难度就被降低乃至取消了,诗意也会大打折扣。没有追问与审视意识的写作,无论是从语言修辞,还是从思想准则上,都缺乏必要的超越精神。太多的繁荣,太多的胜利,导致我们缺乏一种失败主义的警惕精神,那将贫乏和无知当诗意的时代,就自然来临了。
以当前网络上的状态来看,先锋诗歌被取消了难度,或者说有被取消难度的趋势,尤其是一些刚刚踏上诗歌之道的新诗人,他们热衷于模仿口语诗,以为诗歌就是口语,就是白话,就是你我日常交流简单的文字游戏。所以,他们由简单地理解诗歌,到把诗歌写成“废话”与“口水”,写成没有什么诗性与意境可言的分行文字,那些不算是诗歌的东西由此被网络鱼龙混杂地纳入到了诗歌的行列。由此来看,诗歌在此是到了应该重提难度写作与深度写作的时候了。真正的诗歌,是富有人性和生命力的艺术语言,是有诗人深切的感受与经验渗透其中的哲思存在,是尖锐的发现与沉实的趣味的微妙融合。网络上那些没有难度的诗歌,并不是简洁美学所要求与提倡的分行形式,这样的诗歌剔除了人的想像与复杂的情感因素,而直接朝着语言的分行排列形式一步到位,中间省略了创造的过程。诗人奥登在其经典文章《论写作》中,对这种偷工减料的写作做了如此评价:“如果诗歌可以在迷离恍惚之际一挥而就,其中根本没有诗人自觉的劳动,那么,写诗将是一件枯燥乏味甚至令人不快的活动,只有金钱与社会地位这样的物质报酬才能诱使一个人来写诗了。”(5)而恰恰很多人正是冲着这样功利的目的在电脑上闭门造车。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写诗成为了一种可以随时进行的事情,写完后就迫不及待地贴在了博客或论坛里,求点击率和关注度,少有沉淀与修改。而还有一些人则纯粹出于发泄的目的,不假思考地在网络里粘贴他或不知所云或极端散文化的分行文字,而且一天可以写十几首甚至几十首。出于这两种目的,网络诗人们似乎都深究不到写作诗歌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相反,他们还乐此不疲,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都坚持不到最后。很多曾经在网络上活跃的诗人现在都消失了,有的不写分行文字而转向小说与散文写作了,还有的则如昙花一现的幽灵一样消失于网络,从此不再现身。
取消诗歌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网络的错。这样的错,同样在诗人身上体现得明显,就如同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一样,没有经过审视的经验,也是不值得写进诗歌的。但很多诗人,包括一些著名诗人,都没有遵循这样一个艺术最基本的原则,而是迫不及待地表达,最后却让表达变成了一种文字的泛滥。没有精品意识,没有质量保证,只是一味地求多、求量,这是当下诗歌界最令人忧虑的现象。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经历的人,却有滔滔不绝的写诗欲望,这是凭借一种年轻的激情使然,而一旦这种激情过去或消逝了,其所谓的创作也就是完结的开始。适当的沉默,必要的积淀,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的诗歌创作态度。
重新恢复诗歌的难度,不仅仅要在语言的打磨和锤炼上下功夫,更需要提升写作在精神超越上的难度,尤其是思想性与力量感。这样的难度,需要诗人有诗歌抒写的激情,更要有理想主义的价值观;需要有诗意的现场感,更要有契合人类精神的历史感;需要有敬畏语言的风度,更要有独立批判的立场;既要有对时代与社会的记录,更要有颇具现代性的艺术情怀。诗歌的经典性,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回味的语言,值得共鸣的情感,值得不断为创新带来动力与热情的经验。有难度的经典诗歌,还在于其持久的活力与深具常识意义的永恒价值,在于其丰富的表达和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在于其所具有的拓展思想境界的真实格调。当然,优秀的先锋诗歌所需要的元素,还不止这些,如果一个诗人能达到如此的写作高度,哪怕他是一位诗歌美学的异端,也值得我们推崇。但如果还有更高的追求,还需要在感悟生活的同时,深入到灵魂里去挖掘生命的尊严。
最后,面对网络与各种刊物上诗歌被简化的现状,我仍然需要不断地重申,恢复诗歌难度的前提,还是需要诗人拓展自己的视野,重塑自己的精神空间,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在语言自救的道路上摆脱内在的贫乏。所以,诗人不能受制于小圈子行为,也不能将诗歌的语言之道变得越来越狭隘,他们不仅需要培养自由创造的心性,更是需要将诗歌当作语言艺术的精华来尊重与探索。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参见《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第2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杨炼《什么是诗歌精神?》,载《读书》2009年第3期。
(3)(4)王小妮《今天的诗意》,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5)[英]奥登《论写作》,参见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第296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