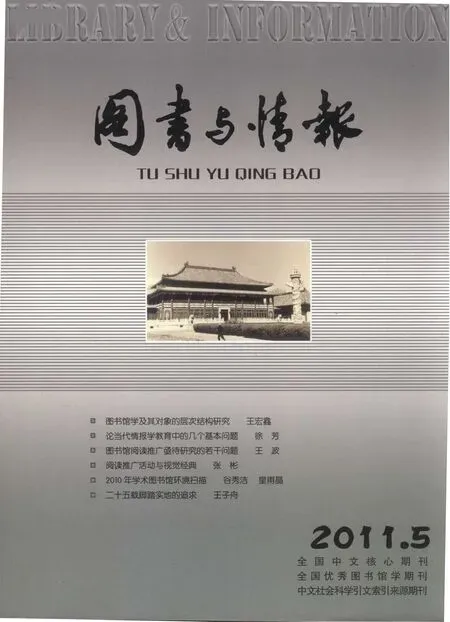知识考古视野下的一般文选学史
尹曙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自唐代文选学兴起,一千多年来,历代文选学研究者都力图勾勒、描绘出一部连续、完整的文选学史。随着新的文选学文献不断出现,特别是到近现代,一些珍贵的写本(如敦煌本《文选》)、抄本(如《唐钞文选集注》)、刻本(北宋天圣监本、奎章阁本、陈八郎本《文选》)等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时,这种努力益发迫切,似乎也更有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昭明太子萧统编定的《文选》最早的版本在唐代已荡然无存,它是在众人的传抄中得以延续的。目前所存的文选学文献,也只是曾经出现过的此类文献中的一部分,甚至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文献之不足征,注定只能书写出断裂的历史。由于有偏向的价值确认,在目前的文选学史中,与葛兆光所言一般思想史相类似的一般文选学史基本上没有一席之地。传统的文选学史主要关注《文选》的版本、注释、校勘、评论等内容,其流布范围也多局限于相对广大《文选》阅读者人数少得多的研究者,即使其部分成果可能体现在刊刻的《文选》中,大多数读者恐怕也难以领会到其中的苦心孤诣。一般文选学史则在意各个时代最普遍的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文选》的情形,审视《文选》是以何种方式在一般知识人中传播、他们学习《文选》的目的何在、他们见到的是什么样的《文选》以及他们对《文选》的认知程度。在知识考古的语境中,“考古学是一项比较分析,它不是用来缩减话语的多样性和勾画那个将话语总体化的一致性,它的目的是将它们的多样性分配在不同的形态中。考古学的比较不具有一致性的效果,而具有增多的效果。”[1]用知识考古的方式来考察一般文选学史,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文选学史,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大研究的视野,让文选学史更加丰富多彩。
1 《文选》的一般传播途径
在版刻大兴之前,《文选》主要以抄写的方式传播。以个人之力缮写白文三十卷的篇幅,无疑是一项卷帙浩繁的艰巨工程,更遑论有注的三十卷或六十卷、一百二十卷。唐写本、抄本《文选》中,还没有发现一部完整的《文选》。帝王之家阅读《文选》,也唯有抄本。如《旧唐书·裴行俭传》:“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2]百卷绢素书一部《文选》,当是供唐高宗专用的大字本。自曹宪在江淮间为文选学,到李善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选学逐渐自东向西传播。李善显庆三年(658年)成《文选》注,三年后,又将善注六十卷《文选》藏于秘府。选学深入帝都,上达庙堂之高,获至尊之好,以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的导向,《文选》在其时的广泛流布当非虚妄之谈。开元年间,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通过使节请《文选》等四种典籍,仍是通过秘书省写与之。这已是在吕延祚上五臣注《文选》十余年后,选学也正日益从高深的学术殿庑向更一般、更普通、更众多的读书人延伸。
除了从秘府抄出,《文选》也随着曹宪、魏模、许淹、公孙罗、李善等人的教授而向更广阔的人群散播。这种个人辗转传抄的方式散布力度十分有限,《文选》在民间广为流通,书肆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后汉书·王充传》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3]说明汉代已有书籍通过市场流通,而且还是贫家子弟的一个阅读场所。南北朝时期的徐文远与王充的情形非常相似。《大唐新语》卷十二:“(徐文远)被掳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4]北周时的长安,书肆比较发达,且其经营的成本必不太高,属于普通人能经营得起的范畴。唐代书肆更为常见,吕温作于贞元十四年(798年)的诗云:“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刘禹锡也有“军士游书肆,商人占酒楼”的诗句。《唐诗纪事》卷四十七:“(李)播登元和进士第。播以郎中典蕲州,有李生携诗谒之。播曰:‘此吾未第时行卷也。’李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5]梁元帝萧绎江陵焚书以后,直到唐初战乱频仍,隋唐以前的书籍颇多散佚,作为文章总集的《文选》,在唐代自然成了极为重要的集部之书。有市场需求,就会有人大量抄写出来,通过书肆出售,但其价格亦当不菲。
行卷作为科举的敲门砖,其篇幅一般不会太大,估计顶多与《文选》一卷的长短相当。以元和以后,李播吾未第时行卷值百钱推测,一部三十卷的白文《文选》当在三千钱左右。杜甫诗云:“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新唐书·食货志》:“(建中)三年(782)……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6]一斛为十斗,则一部最简单的《文选》也大约相当于十斗酒的价格;有注者价当更贵。从书写的简便和书籍的价格而言,相对简短的五臣注《文选》必然比繁富的李善注本更有优势,也更利于《文选》的一般传播。缺乏购书财力的人,就只好像五代的毋昭裔一样,借《文选》于交游间,免不了要看所借之人的脸色了。
进入版刻时代,雕版印刷令书籍的体积大为缩小,印数也远胜抄写之时,《文选》的传播更能深入到寻常读书人之家。现知《文选》最早刻本是毋昭裔仕后蜀时所刻,此时去萧统编选的年代已远,可资借鉴的集部之作,又多了唐人的许多优秀作品。版刻《文选》主要是李善注或五臣注,或二者兼而有之。据各种书目记载及现存的状况看,一部完整的《文选》少则二三十册,多则六十册。普通人家要购置一部,虽相对书写时代容易一些,但仍需花费不少。因此,就出现了一些《文选》的节选本,如北宋苏易简的三卷《文选双字类要》、明代张凤翼的十二卷《文选纂注》、清代洪若皋的十一卷《昭明文选越裁》等。
叶德辉认为:“宋、明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皆有官书以供众读。”[7]《天禄琳琅书目》卷三所载宋版《六臣注文选》,其解题说:“书中有宝庆宝应州印,及‘官书不许借出’木记。”[8]家中无《文选》的学子,亦可到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阅读。不能借出观看,对于个人是不甚方便,但保证了该书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这些地方已略具当今的图书馆性质。
2 阅读《文选》的一般目的
一谈到学习《文选》的作用,很多人都能轻易地想起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引用的“《文选》烂,秀才半”,简单地认为古人读《文选》主要是为了科举应试。
在唐代科举取士中占主要地位的进士科,从开元年间起,大抵分三场考试:帖经、杂文(诗赋各一)及时务策五条。此前,杂文并非专用诗赋。《登科记考》卷一永隆二年(681年)条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9]
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后,以经义代诗赋。进士考试分四场:一场考大经(《易经》、《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二场考兼经(《论语》、《孟子》);三场考论;四场考策。另宋代设有宏词科,先后涉及考试文体包括表、檄、露布、诫谕、箴、铭、颂、记、序、制、诰、赞、檄等。
明清两代重在以八股文取士,但仍兼考论、表、诏、诰、判、策。乾隆二十二年(1787年)罢论、表与判,增五言八韵试一首;五十二年定乡、会试首场考四书文与试帖诗,二场考经文,三场考策问,遂成定制。嗣后童试与岁试、科试也考试帖诗。
从历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看,与《文选》相关最多的是诗歌。唐及宋初诗赋地位较其他文体明显要高一些,但诗赋也只是《文选》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科举应试总的趋势是与《文选》渐行渐远,越到后代相关度越低。产生于唐代的《秋胡变文》中提到,秋胡外出求学所带的十袟文书就包括《文选》。李德裕称,其祖天宝末登第后,家不置《文选》。这都说明当时阅读《文选》的目的之一确实意在科举。
可《文选》毕竟是一部文章总集,人们阅读的范围还是不出集部。杜甫诗云:“续儿诵《文选》。”《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朝野佥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四二《宋府君玘行状》载:“(宋玘)雅性强记,暗诵诸经及梁《昭明文选》,以教授诸子。”王得臣《麈史》卷中称:“予幼时先君日课,令诵《文选》。”[10]张简之事虽系传说,但其时乡学中讲授《文选》则非向壁虚造。唐宋间,用《文选》作为孩子们学习文学的教材,当较为普通。
《麈史》卷中还记载了宋祁母梦朱衣人携《文选》与之后生宋祁,并小字选哥的故事,特称其“文学词艺冠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载南宋绍兴十四年事,也提到当时的普安郡王、后来的宋孝宗诵读《文选》。[11]皇家子弟与科举应试全无关联,其目的显然出于文学学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瑶溪集》云:“《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12]后集卷二又引《雪浪斋日记》云:“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13]都是从文章学习的角度讲《文选》的重要性。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九记载:“明代集《诗》、《书》、《论语》、《文选》为文,多至数百言。遂另辟一种风气。”[14]集《文选》为文已成为明代的一种文学风气。《红楼梦》中不喜科举的贾宝玉陪同贾政进大观园时,也稔熟地提到了《文选》中的多种异草名称,说明阅读《文选》的一般目的首先在于培养读书人的文学修为。科举应试与《文选》相关,是以其测试文学能力所致。
3 常见的《文选》内容
《文选》篇章众多,内容繁富,年代久远,注者纷呈,传抄刊刻,错误在所难免。历代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文选》内容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讹。好在“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15]《文选》内容上的传播有两种趋势:一是整部《文选》的内容越来越多,从最初的白文本,到一家注本,再到两家注本,甚至有多家集注本;二是删减本的《文选》陆续出现。
综观现存的《文选》写本和抄本,错讹衍倒处甚众,但却又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一些优于后世刻本的可贵内容。不少刻本也明确地提到,修改了以前版本的许多错误。北宋初年,国子监刻李善注《文选》就进行了多年反复的校勘,校勘者所见之本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保存在韩国奎章阁本《文选》中,沈严于天圣四年(1026年)所作的《五臣本后序》称:“旧本或遗一联,或差一句,若成公绥《啸赋》云‘走胡马之长嘶,迥寒风乎北朔’,又屈原《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如此之类。及文注中或脱一二字者,不可备举,咸较史传以续之。字有讹错不协今用者,皆考《五经》、《宋韵》以正之。”可见旧本《文选》不仅注有脱漏,正文亦有差遗。其所刊之本,以《五经》、《宋韵》正字以“协今用”,又会导致不少新的问题。奎章阁本书末还载有秀州州学元祐九年(1094年)的跋文:“秀州州学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入。凡改正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改动达两万多处,错失之多不能不令人惊愕。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在刊刻李善注《文选》的跋文中也说:“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朱熹也注意到:“孔明《出师表》,《文选》与《三国志》所载,字多不同,互有得失。”[16]究竟是萧统编入《文选》已与《三国志》所载不同,还是后世两书各自演变而不同,已难一一明晰。尽管各种版本良莠杂存,泥沙俱下,《文选》及其所载内容整体上总算辗转流传至今。
裴行俭用草书给唐高宗抄写的《文选》,估计是白文本的可能性较大。李匡乂《资暇集》卷上云:“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不相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17]李善注亦有不同版本,且以绝笔之本最为该备。宋代官刻《文选》中,国子监所刊为李善注本,州学则混刊五臣、李善两注,坊间所刻以五臣注本居多。作为一般阅读,五臣注篇幅短小、通俗易懂,李善注未免太过繁琐、冗长。故唐宋间,学者多赞李善而非五臣,世人则多习五臣。
元明以降,《文选》主要以李善注、六臣注本行世,间或有白文本刊行,五臣注本几近消失。[18]这是唐宋学界长期贬抑五臣注所致。一般读书人的财力和精力都难以拥有一部《文选》,并通读全书。于是,《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文选锦字》、《文选纂注》、《选诗约注》、《文选尤》、《昭明文选越裁》、《文选课虚》、《文选类隽》等摘类、删减之属的书籍相继出现。这些被绝大多数选学研究者认为毫无意义的众多书籍,在当时未必不如那些阳春白雪盛行,其所影响的范围也远大于后者,对考察当时普通读书人的选学水平大有裨益。这也是昔日皇家贵胄的《文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传播途径之一。
4 对于《文选》的一般认知
普通读书人对《文选》的一般认知,多流于皮毛,纵有科举之利,多数人亦不胜了了,往往随波逐流,并不十分理会已有的选学成果。唐代李匡乂、丘光庭皆非五臣而是李善,世人却“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聘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19]
宋代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八中谈及选学时说:“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20]他认为提问的应试进士选学水平胜过主司。细看翁元圻所引宋郑文宝《南唐近事》的内容,似乎未必如此。其辞为:
后主壬申,张佖知贡举,试《天鸡弄和风》。佖但以《文选》中诗句为题,未尝详究。有进士白云:“《尔雅》‘螒,天鸡’,‘鶾,天鸡’,未知孰是? ”佖大惊,不能对,亟取《尔雅》检之。 一在《释虫》、一在《释鸟》,果有二,因自失。[21]
“天鸡弄和风”出自《文选》卷二十二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其上句为“海鸥戏春岸”。李善注引《尔雅》曰:“鶾,天鸡。”五臣李周翰注:“天鸡,鸟名。”又《文选》卷十二郭璞《江赋》有:“其羽族也,则有晨鹄天鸡。”李善注引尔雅曰:“螒,天鸡。”五臣吕延济注同善注。故事中,张佖显然不知《尔雅》中有两种不同的天鸡。若果为文中所言“以《文选》中诗句为题”,张佖惊的是不明《尔雅》中有两种不同的天鸡,并非不知道上句的内容。他可能但知谢灵运之诗,而不熟悉《江赋》。反之,提问者倒可能只知《尔雅》中的二天鸡,却不熟悉谢灵运的诗句,否则他不当有此疑问。考官和考生对《文选》都不够精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中也有考生不明《文选》中诗意的记载:
袁州自国初时解额以十三人为率。仁宗时,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试进士以“黄华如散金”为诗题,盖取《文选》诗“青条若葱翠,黄华如散金”是也。举子多以秋景赋之,惟六人不失诗意,由是只解六人,后遂为额。无名子嘲之曰:“误认黄华作菊华。”[22]
“黄华如散金”出自《文选》卷二十九张翰《杂诗》,其首句为“暮春和气应”,是晚春景象,“以秋景赋之”已失之千里。仅六人不失诗意,说明不熟《文选》的读书人不在少数。直到清代仍有以《文选》中诗句出科举试题的习惯。乾隆年间,曾以《文选》卷二十颜延年《应诏宴曲水作诗》中“天临海镜”为诗题,不少考生不知上句为“太上正位”,无法明白其意在天子,竟误认为是写月光,终名落孙山。
雕版印刷的成熟,固然扩大了普通读书人接触到《文选》的几率,科举考试中也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但能真正熟悉的人并不多。这也可以反证不少人的确是通过简化的《文选》类书籍来学习的,粗浅的阅读,临到考试也不得不一知半解地应付了事。
[1][15](法)米歇尔?福柯.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177,6.
[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0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005.
[4]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6.
[5]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新1版:720-721.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419.
[7]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57:223.
[8]于敏中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6.
[9]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70.
[10]李昉等.太平广记[Z].北京:中华书局,1961:3658.
[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2439.
[1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6.
[1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9.
[14]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8:444.
[16]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5:3237.
[17][19]李匡乂.资暇集[A].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5,4.
[18]刘群栋.《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9,(4):152-155.
[20][21]王应麟.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35-1836,1036.
[22]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新1版: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