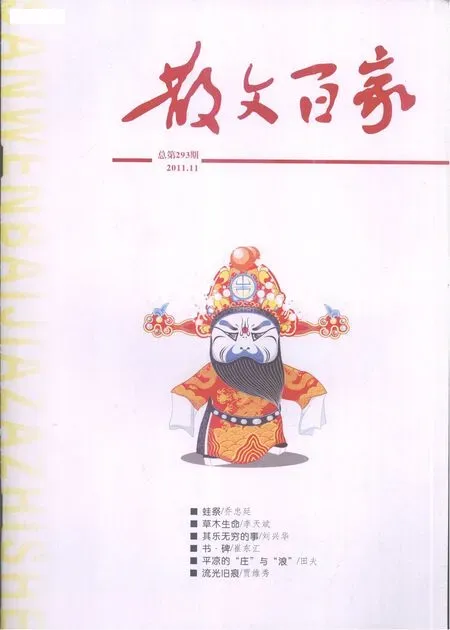为村落『申遗』
高勤
进村的土路曾经很颠簸,深且弯曲的车辙里如同藏着一个个恶作剧的顽童,会伺机搞一下你的车轱辘,车子一滑,心抖地一惊。
骑车在柏油大马路上,整个人是飘飘然的,说肆无忌惮也无可,看一下东,望一下西,给你“我欲乘风归去”的错觉,可以全然忘却关注脚下的路。车子一拐下大马路就是另一码子事了,仅仅三余里的田间土路,每一寸每一尺每一米地走下来,它不光锁住你的脖子,也锁住你的双眼,甚至锁住你的心,叫你不得“旁骛”,因为稍有不慎,即便它不给你个人仰马翻的难堪,也会叫七魂惊掉三对半。
念书时,看见“哲学”就头皮发紧,在终于考过被放行后,哲学课本连同笔记被我一毛钱一斤卖掉了,从此一拍两散,今生不打算再度相见。然而,三余里的村路让“哲学”从我的“贮藏室”里灰头土脸地钻了出来,它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它又说:也别忘夹起尾巴做人。它说:看天——因为希望。它还说:看地——为了踏实。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曾经,村路以及它远端的村落与我的生活休戚相关,但它不是哲学的衍生物。
后来,“村村通”把那条土路变成了“砂石路”,若干年后又换成了小马路。没有了颠簸,也不见了车辙,更告别了雨后的泥泞,但车轮碾在上边,发出“沙沙”的声响,无疑还在提醒着路人要记得它的与众不同,何况还有那在村头为车辆强行限速而叠起的道道鼓梗,使你不能畅快通行,这分明让人看到:村庄在且进且退中的犹疑,乡路在“新与旧”、“原始与现代”、“挣扎与渴求”的情感中一进一退地如何胶着。
去婆家的这条路来来去去走了二十多年。人说:嫁人就是嫁给一种生活。那么,正是从这条村路我走进了原来陌生的日子。尝过酸甜苦辣,也记得寒来暑往,同时也感知着这条村路点点滴滴的变化。偶尔还会想起寒冬时它冷硬而青灰色的脊背上皲裂的纹路,想起夏日里它被上涨的河水一点点溽湿的那份柔软。有一回,带在身后的儿子从后衣架颠到地上,滚下干涸的沟渠,一位放羊的老人托起孩子……他那份真切的担忧和虔诚的默念岂止是安抚了我的儿子,也把我吓丢了的魂魄“叫”了回来。
据说,一个人如果时常怀想过去,那么说明他的老矣。假若这个说法成立,或许我从二十几岁就有了几分沧桑。其实不尽然,我以为,念旧,并非是想重回过去,人活于世,心灵需要长期养护,而我们的根脉总会在泥土深处汲取养分。
在社会的变革中,村路完成了它从原始到现代的一次次蜕变,如今已脱胎换骨,但终归还能引导人们走向村落的深处,走进村庄的生活,它到底是作为一条路而存在着——土的也好,砂石的也好,柏油的也好,她就像一个符号,昭示着这个世界平和与安宁之所在,让人心里踏实。
今年春节回婆家过年,往日的小村,不仅因为节日的到来而躁动,一条关于“新农村改造”的消息令全村的男女老少兴奋异常。具体讲:在全县统筹的经济建设规划中,农村集中建区,把相邻若干村的老百姓搬进统一安置的住宅楼,腾出的土地及旧宅处用来搞经济开发,力争在三年内把原本的一个农业县近50万亩耕地变性,打造成“无粮县”……
要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屋而搬进新楼,要丢掉世世代代握过的锄把去做工人,神话一样,难怪有人已经在掐自己的大腿,以判断其是否在梦里。
我出生在农村,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人”,长在县城,亦没做成实实在在的“城里人”。曾经很排斥城里男孩儿吊儿郎当的公子哥儿做派,可当真和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一路生活下来,才知道到底把自己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喜欢农村人的朴实,但也看到了他们的狭隘。认可城里的生活更随心随性,但也常常畏惧小市民间的那份冷漠和工于心计。关于农村和城市,在我的感觉就像面对自己的左手和右手,看看左,再看看右,都是肢体的一部分,可能压根儿与取舍无关。
曾有过在基层税务所工作两年的经历,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冬天。几辆经过改装、重新喷涂的小公共汽车刚刚在乡际间投入运营,艳俗的车身和里边不洁的内置、糟糕的车况倒也呼应一致。时常有半袋子铁器或半扇子猪肉、一篮子鸡蛋随它们的主人一同跨上车来,甚至拎两只活鸡去串亲戚的也偶尔有之。抱着孙子的老奶奶在车上为孩童把尿,口中会自然伴以最原始的哨声,而“七大姑”、“八大姨”乡音俚语的呼唤也常常会在车前车尾遥相呼应。还有那足以让你惊掉下巴的“司乘人员”。我就见过,乘务员把去了壳的毛鸡蛋也放在引擎盖子上,再抖抖手里那个白色的盖口儿处打过眼儿的小瓶子,给毛鸡蛋淋上几星盐花儿,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回转身,用另一手捏起“收拾停当”的毛鸡蛋放入口中。也见过司机和乘务员如何在车子的行进当中就交换了位置,同时也交换了身份。然而当时在车里为此情此景瞠目结舌的人大概只有我一个,我震怒于人的生命被如此漠视,简直要拍案而起,可环顾左右四邻却是一副副波澜不惊、谈笑自如的样子,似乎性命相托不过行李寄存,既然交出去了,就没有理由一惊一乍再怀疑什么。我压抑下自己,把头扭向窗外,看远近灰蒙蒙的村庄一簇簇从眼前跳过,很隔膜的感觉。
这天窗外飘起了大片的雪花儿,车在短暂的停顿后,上来一位老妇人,中式对襟碎花棉袄,一块方巾拢向脑后,肘弯挎着个大包袱,如果拍旧式电影,这些都是不用化妆,也不用安排道具和场景的。上了车的老妇人有些拘谨,她微笑着将车里的人从前看到后,不知是算作打招呼还是找座位。车子本就不大,已经客满,她顺势坐在身边的引擎盖子上,把包袱抱到身前,然后问身边的人:“坐一回多少钱啊?”显然这是她的第一次。和老妇人挤坐在一起的正是刚刚从司机位置换下来的小伙子,他笑着说:“不要钱,大妈,您随便坐。”边说边抬手掸去老妇人肩头的雪花儿。一个中年男人接茬儿说:“您可别信他的,他臭王八蛋不跟您要双份就便宜。”一车人都笑了,老妇人也笑了,说笑间她并不躲闪小伙子那只还在她肩头拍打着的手,那场景自然如一对母子。大城市的公交车正规而舒适,训练有素的乘务员礼貌又周到,能坚持着笑出第八颗牙齿,让你不小心咳嗽一声都会为给别人增添了麻烦而羞愧难当。自然大概只属于乡村,裸露着的情感,就像蒲公英一样开遍原野。我再望向窗外,看到一簇簇从眼前晃过的村落里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起,在高处缠绕在一起,如仙似幻,却是地道的人间烟火。
婆家灶间的八印锅里炖着满满一锅肉,真香!吃饭用的大碗哪怕是空着,一上手已是沉甸甸。坐到饭桌上自是有一翻推让,婆婆是真心地让,“吃,留它干啥”。我是坚决地推,因为怕长胖,怕“三高”。在城里,不光拿捏着做人,也拿捏着胃袋的,你想活得“纯天然”,那只是电视里的广告语。
农村人自有农村人的狡黠。平时因为忙,回去的次数并不多,每次一见面,婆婆自是:奶奶咋样?姥姥咋样?姥爷咋样?连我的侄男八女都关怀个遍,开始我还逐一回答,后来发现那不过是老人的外交辞令,她并不在乎我如何回答,我也就一笑了之。倒是我的父母,“这两瓶酒带给他爷爷喝。”就是带给他爷爷喝,绝没有多余的话。
英国诗人库泊说:上帝创造了农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也许农村的存在体现着“上帝”的意志,人类却在让城市一天天地膨胀。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并非它们水火不容,正因为它们以各自不同的形态和内容并存于世,才让这世界因趋于完美而魅力无穷。
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进行中,让人既喜且忧。来年,这条三余里的村路是否还存在?几年后,那错落的、一簇簇既相隔相望又根脉相连的村庄是否将被抹去?不得而知。如果说“新农村”约等于住新楼,“新农村建设”意味着农民丢掉土地,那么,多少年以后,我们会不会要像对待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三江并流自然景观”一样,为现在的村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哪?后代子孙,会不会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缩微后的村落模型哪?锐意改革、大胆创新也许会彪炳史册,那么,由谁来担当“败家子”的恶名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