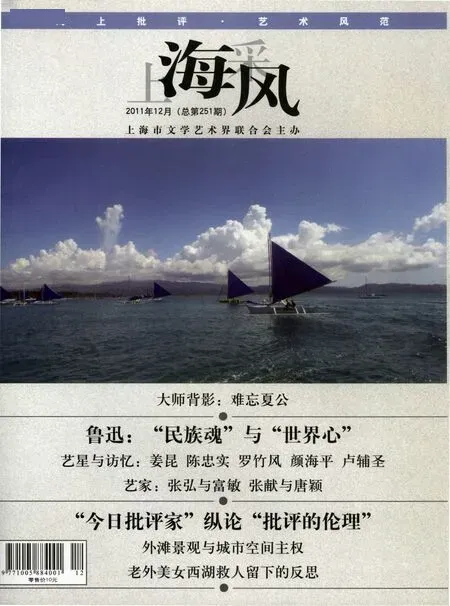穿麻布披风的隐士
文/蒋友柏
我生活在台北,可每当有朋友叫我形容台北时,我都会陷入两难。身为台北的居民,我有权利与义务强烈地推广台北在面对现代化与国际化时所做的努力。我应该告知天下,“101”曾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楼,虽然我想不出它的建筑设计除了“避震钢球”外,有什么特别的;或是凸显台北的垃圾回收入选上海世博会的“模范都市”,虽然我每晚遛狗时踏过的街还是那么的脏与不环保;甚至应该骄傲地拿出我的笔记型计算机,用无线上网无死角的效能为现代化的台北摇旗。但是我做不到。因为这些台北元素都太新了。新到我还无法与这些元素建立情感连结。台北在国际上营销的现代化外表并不是吸引我落地在此并成家立业的原因。我之所以选择从纽约回到台北,只是因为这里保有我绝大部分的人生拼图。
对我而言,台北,一个由东、南、西、北四门所框起的城市,就像是一位穿着麻布披风的隐士,或是一部轻碰灰尘就会在空中跳舞的泛黄旧影片,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它只是默默地融合在街景中等着被遗忘。一旦用心去找,就会发现它置身在仁爱路与信义路中间小巷内古早味排骨饭的油腻中,或处身在西门町戏院外旧报摊老板眼角的鱼尾纹旁,甚至隐身在中山北路婚纱店前的金钱砖下。对我,台北就是这么的平凡。
回顾我短暂的35 年生命,我曾迁出台北3 次。第一次的离乡晃过了4 年。当我在16 岁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看世界的视线前加上了蒙特利尔、旧金山、与纽约的滤镜。当时眼中的台北缺乏蒙特利尔四季分明的人文之美,也没有旧金山的艳阳高照的律动活力,更缺乏纽约熔炉的文化创新。仿佛比起这些一级城市,台北所具备的软硬件都需要升级。但是,台北却让我感觉自在。为了这个自在感,我宁愿放弃在国外一级都市所学会的生活享受。我知道我无法再感受面对蒙特利尔做的雪天使时的宁静、不能享受旧金山的联合广场逛街的悠闲、就连陶醉在纽约中央公园内的动静反差都变得遥不可及,但我却再一次被这个城市迷惑。从我家往北40 分钟的车程,我可以听到海水的蓝;向南搭90 分钟的客运,我可以闻到慈湖天鹅的雅;往东步行10 分钟,我就看见阳明山的蝉鸣;而我也可以随时跳进繁闹的街头,用臭豆腐配着街舞吃。那时的台北是金银岛里的海盗船,载着我游戏人间。
第二次背井,是为了逃避丧父悲伤的追杀,躲回了纽约。这一躲就是3 年。虽然在国外的城市面貌里,很少会看到父亲的残留身影,但悲伤无预警的痛击,仍旧难以承受。恍惚之间,我随着我的心,又再度回到台北。这一次,我的心眼看到的是一段充满回忆的走马灯。在天母的河堤旁,我喝着啤酒,细数着与父亲过年放过的鞭炮;在仁爱路的圆环外,听到了第一次去父亲办公室的嘈杂紧张感;在七星岩山的山脚下,远看那时满山的红枫,依然遵守时间更换衣裳。因为这次用心面对,我回收了在台北的人生片段记忆,而第一次接受了父亲不在的事实。这个时候,对我,台北已不再只是一座城市,它成了我的朋友。
但就像所有的剧本所述,朋友总会因为爱情而分裂。在23岁时,爱情的冲动引诱我抛弃了我的朋友台北——我自私地偷了一年的时间,私奔到新加坡。好玩的是,在那个阶段,我所有的心思与焦点都集中在爱情上,所以对新加坡的记忆细节是模糊的。就连对国际知名的世贸大楼外观,都没有记忆。唯一记得的,只有约会时去过的动物园,是我生平仅见的壮观。那是一个开放式的人造空间,让动物在规划过的框架内,伴着自然生态,过着无限制的生活。因为这个体验,当我完成任务返回台北后,迫不及待地重游台北市立动物园。在童年的记忆中,台北动物园的壮丽是可以与新加坡相提并论的,但事实却与记忆有相当大的落差。当我灰心求去时,却不预期地看见了大象林旺的标本。林旺,这个对台北以外的人没有意义的菜市场名,却是每一位台北人都熟悉的长者。他在战争时用它宽阔的肩背为军队背过补给,又在和平时用温柔的眼神为人民带来慰藉。最后在台北的不舍下,林旺捐出了骨肉变成了永恒的雕像。刹那间,我知道台北动物园对台北人的独特是在它提供了一个共同记忆与回忆的平台,让台北的居民与过去、现在、未来互动。这些互动也让台北升华成大家精神的支柱。
随着年纪的不同,台北从我的玩伴、我的朋友、进化至我的支柱。当一座城市不再具型的时候,你要如何形容它?我只能说,当我人生遇到风浪时,我的自动导航系统就会引领我回到台北。就这个意义来说,台北就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