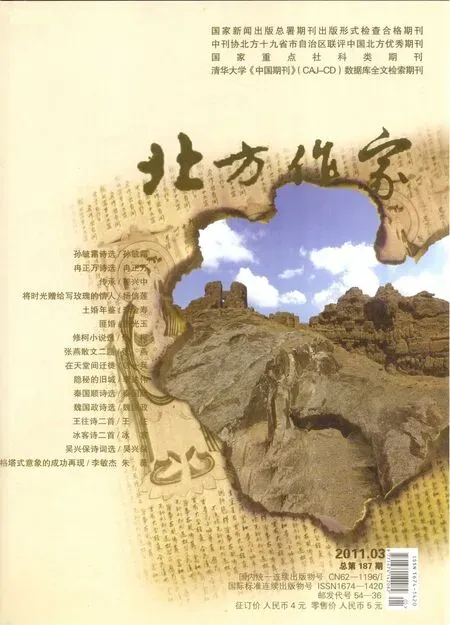隐秘的旧城
李达伟
隐秘的旧城
李达伟
在那片旧城游荡的过程中,我发现那样的石桥并不多见,总共才见到三座,都跨过那条曾经的护城河。那条河在依然缓缓流动,它只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河流,属于过去,属于精神层面。我第一次出现在县城时,我只是把它当成一条小溪,一条颓败的溪流,一条囤积肮脏的溪流。在这里我想述说的是从县一中门口往北百米左右的那座石桥,跨过那座石桥就是旧城的西区,于我而言旧城的西区所储存的记忆远远多于别的区域。在县城读书时的许多日常细节基本都发生在旧城的西区。
我在那片旧城里租了一间破旧简陋的厢房,我要经过那座石桥才能进入那片旧城的内部,石桥成了我通向或者走出某个世界的载体。走过那座石桥,走入那片旧城,那个世界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息:醇厚、深沉和忧郁。由于气息的浓厚,在一次又一次跨过石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沾染了旧城的忧郁和深沉,我经常远离周围的世界,远离嘈杂的新城区,远离群体。似乎忧郁不止属于我一个人,属于所有的一切事物。同样有一些学生在那片旧城区里租房子住,我发现了一些女学生,内心深处沉睡的蛇开始苏醒,我坐在那座石桥上等待着其中让我心仪的女子经过,似乎那个女生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同样在扑鼻的芳香里发现了细弱的几丝忧郁。当我发现那个自己暗恋的女子和某个社会青年交往时,无法释怀的痛彻感长时间地折磨我,但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座石桥上,把目光和嗅觉刻意地折向了别的方向。在石桥上,我渐渐地忘了那个女孩,并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了大众,那些从石桥前面经过的人群,我能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在那些人群上空飘荡。
石桥上总是倒着一些剩菜剩饭,还有一些香(把松柏枝碾成粉末),这些东西的出现暗示着一些信息:神秘的信仰,某种与存在于思维里的世界交流的方式,到处布满神性的暗喻……在那座石桥上往往会发现一些虔诚的信徒在那里祭拜,祭拜过后的老人安详地坐在石桥上,唠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我猜测在那个虔诚的行为后面,他们暂时地抛去了精神的重负,或者依托着神性的力量往上爬去,发现了另外的世界。那种行为里,我发现了人类的两面,甚至是多面性,那座石桥把人性的表情托到空中,长时间地停留,长时间地悬浮。傍晚时分,在石桥上会经常发现一些神经质的人,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疯癫的,似乎疯癫没有任何遮蔽的事物。在我的观察中,我发现只有在那个时间段他们才会呈现出疯癫的状态,他们时而很安静,时而很躁动。在那个时间段,我远远地看着石桥以及石桥上的人群,我把自己定义为区别于那座石桥和那些人的旁观者。在我看来,那些人的安静和躁动都在极力掩饰自己的脆弱,他们担心来自外部的袭击,而在他们的思想里避免袭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强烈地躁动,或者极度地安静。在和石桥对面的小卖部的老板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其中某些人是真正的疯癫,而另外的一些人可能不是。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们一行人经常会在晚自习的时候逃课去那个小卖部看电视,我已经忘了那时候最吸引我们的是怎样的电视和电影。在电视的喧闹中,我们同样听到了区别于电视的嘈杂,是那些疯癫的人群集体的躁动。在听到那些人不顾一切地发出神经质的呓语时,我会很紧张,似乎那些呓语的人会伤害到我。直到离开那片旧城,我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些看似疯癫的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人,反而流言里发生过那些疯癫的人被人伤害的事件。我不知道那些流言是不是真的,但我坚信也只会出现伤害他们的事件,而几乎不会出现他们伤害人的事件。
在那座石桥旁边,一些学生会经常聚集在那个地方打架斗殴,基本发生在放学后,我在经过那座石桥的时候,总是看到了那些打架斗殴的场景。在那些我能感知到的打架斗殴里,有一些人是为了女生而打架,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的懦弱。假如我冒失地为了某个女生打架斗殴的话,在回望那段时间时,我只会觉得那种行为里包含着的心智上的不成熟。现在再重新揣摩那些打架斗殴的人群时,我总会觉得那是心智不成熟后的不理智行为,他们是通过打架斗殴来麻痹对于自身脆弱的感知。幸而那时我沾染上了那片旧城的忧郁和沉静的气息,因此对那些事情进行了冷处理。我会莫名地感到恐惧,似乎那种械斗的场景会蔓延到那座石桥,我匆匆地走过那座石桥,对那些场面视而不见,我听到了其中一些被打的人因疼痛因恐惧而发出“嗷嗷”的叫声,像极了某种动物受伤后的叫唤。我离开那座石桥,回到厢房里开始阅读,只有阅读才能把那些场景彻底从眼前消除。院子里唯一的那棵石榴树上经常会飞来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声音总是悦耳动听,那种声音在微弱的风的交杂下显得缥缈而实际。在那间厢房,我发现了阅读是对抗暴力的最好方式,当然只能在精神层面进行对抗。对抗暴力的方式是远离暴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类的脆弱,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可以说是对暴力的鄙视和忽略。回到厢房后,关于石桥,关于石桥下面的溪流,关于那些学生都远离我的世界,只有那片旧城独有的气息依然凝聚在周围,永远无法消除。那股气息甚至多了一丝血腥味,肮脏腐烂的气息无法把那丝血腥味彻底覆盖,那些肮脏气味的存在暴露了那片旧城的隐秘。
那座石桥起到的作用是让一些人把生活的节奏放慢,让人们在那个地方彻底安静下来,同时给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即便由于那片古老民居的遮挡导致了由视角延展出去的世界显得很狭小,但可以通过把视角拓宽的方式,避开世界的狭小。我在那座石桥上关注着许多事物,那些事物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往往是陌生的事物。只有对那些事物由陌生转变为成熟稔后,才会感觉到与旧城的距离在缩短,同时熟悉了一些事物后,又会产生进一步发现另外一些陌生或者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物的想法。在石桥上的很多时候,我甚至会怀疑出现在面前的泥土、植物和小动物都不是真实的,或者说那是一些与我的思维完全相悖的存在,在我的思维里,只有与民间紧紧连结在一起才是真实的。我心目中的民间,是与泥土近距离接触的乡间。
石桥在我心里面也成了一个神秘和温存的所在,在我接过小卖部家的那个并不好看的女儿手中的东西时,我没有多少心思稍微关注一下那个还是学生的女孩。在与她面对面的过程中,丝毫感觉不到那个年龄段应该存活的清纯,而是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就是那种超乎年龄的咄咄逼人无法让我燃起哪怕瞬间的关注,我接过她手中的商品,匆匆地走出了小卖部。在那片旧城里生活的那段时间,我会像避开那个女孩一样刻意避开一些事物,同时去找寻另外的一些事物,并在那些事物上找寻某种表达和感觉。我在那条西大街上行走,西大街通向一片庄稼地,通向金华山,我听到了一些人在谈论着西大街的过去。那座石桥是关于那些对话最好的旁听角落,有很多人在充满忧伤的唠嗑中“出卖”那片旧城的过去,并透露与旧城相关的人类或者植物、动物的信息。与西大街的过去相比,我更喜欢关于植物的交谈,我往往听到人们谈论着那种名叫“紫茎泽兰”的植物。在溪流流经的沟道里长着的那种“紫茎泽兰”,那是一种霸道的植物,它的出现更明显地暗示着那条河道的脆弱,以及别的许多植物的脆弱,或者是不合情理的退让。那种植物把那条溪流吞噬后,那些密集的植物里很难再杂入另外的植物,即便有另外的植物出现,它们同样在缺水缺氧的情形下死亡,溪流中曾经活跃的小生物在我的目睹下消失。如果没有经常出现在那座石桥上,如果没有在经过石桥的时候把视角深入那条溪流的话,我将对那些植物熟视无睹。在很多时候,我会感激那座石桥,是它让我发现了一个经常被我忽视的世界。依然有很多人在忽略那片旧城。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