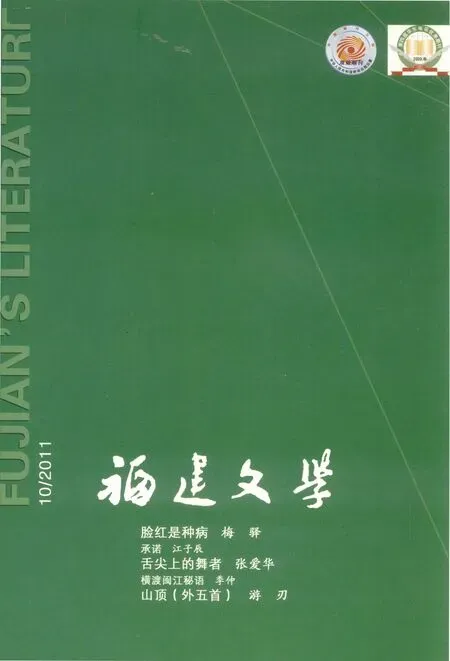陈伟宏微型小说两题
陈伟宏
相 亲
春风吹,杨柳青。小镇边的狮子山公园里,大才西装革履,一脸喜气洋洋。要问他今天有什么喜事?原来村南头的喜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约好在此见面。听说这姑娘是镇幼儿园的老师,模样儿俊俏,心眼又好。他能不高兴吗?
大才快是而立之年的人了,前几年家住破茅棚,加上又有一个瘫在床上的哑巴婆婆,哪个姑娘愿意上他家门呢?可这两年大才家硬是“脱胎换骨”了。自从承包了村里的茶场,一年下来,三层洋房魔术般地竖立起来,令村里人刮目相看。
家境一好,远近姑娘自然找上门来。只是这些姑娘看到瘫在床上的婆婆,不是捂鼻就是撇嘴。一来二去,大才冷了心。大才可不忍心让婆婆遭受这份冷遇。大才三岁死娘,七岁亡父,是哑巴婆婆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其间吃过的苦头,只有大才心里清楚。有一次生产队里分粮食,会计少称给他家二十斤,是婆婆颠着个小脚,摸着黑赶到会计家里,“哇呀哇呀”比划着跟会计吵,硬让会计给补足的。当时有多少人围观着,笑婆婆的模样。当婆婆把二十斤粮食背回家里时,眼泪已默默地爬满一脸。那时大才就发誓,以后要好好地孝敬婆婆。
大才看看手表,约好的时间快到了。他看看公园门口,好像来了两个人。他看清有一个就是喜婶。他忽然觉得那个姑娘有些面熟:红衣绿裤,短发圆脸,仔细一回想,不禁大惊失色:那天大才路过聋哑学校,就发现这个姑娘正做着手势,在跟别人打哑语。
“原来喜婶给我介绍的对象就是这个哑巴,难怪说模样好。”大才有些怨恨喜婶了。家里有个哑巴婆婆,再娶个哑巴媳妇,村里人会怎么看呢?
大才这样一想,趁两个人还没走近,拔腿就溜掉了。跑到镇上,心里火气难消,索性坐到馆子里,自饮自醉起来。
挨到中午时分,他才离开馆子往家里去。走近家里,发现喜婶和那个姑娘正在婆婆房里。姑娘一边和婆婆打着哑语,一边细心地为婆婆梳理头发。婆婆乐呵呵地笑得可开心哩。
大才扭过身子,想走出房门,这时候,喜婶看见了,连忙跑过来,一把扯他进门,点着他脑门怨道:“你还跑干吗,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也难找呀。”
婆婆哇哇地打着手势,叫大才过去。大才走过去。婆婆朝姑娘望望,又朝大才使劲点点头,大才见婆婆已是老泪盈眶。
喜婶说:“春梅听我讲了你婆婆的事,就专门跑去学哑语,为的是能跟你婆婆交流感情啊。”
“什么,她不是?……”大才一时醒悟,他激动起来,一把攥住春梅的手。
“哎哟。”姑娘叫了一声,一脸羞红。
“大才,你呀!”
银铃般的声音迅即钻进大才的耳里。
山囡嫁往城里去
农历十月小阳春,阳光暖融融的。山村的梨树花又开了,白晃晃点缀在满山坡。
村东头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一派喜庆的热闹景象。今天是这人家的女儿山囡出嫁的日子。院子里、屋子里人声嘈杂,有来相帮着搬桌拿凳、劈柴烧火的男人,有在水池边洗碗洗菜的妇女,有在热气弥漫的铁锅前拿勺的厨师,嘴里咬着支烟大声喊帮厨的预备碗碟。一时没活计的帮工寻找院墙一角,有太阳照着的地方,打牌赢钱。也有闲着的老人和小孩站在院子里,一心盼接亲的队伍来。村里的狗也集中在这里,人群中窜来窜去,抢肉骨头吃。
近中午,一阵爆竹响过,几辆黑亮亮的小汽车驶停在院门口。接亲的人来了!人群跑着围拢去观看。新郎从皮包里抓出一把糖果抛撒开去,男男女女就慌作一团趴头在地上抢抓,一边嘻嘻哈哈地笑。
接亲的人进了门,在正屋堂前的八仙桌前坐定,喝茶水吃糖果瓜子。城里的摄像师歪戴个帽子忽左忽右拍录像。门槛里外站满了看新鲜的人。就有人指点着新郎说,到底是城里人,穿着打扮也洋气。一妇人接嘴说,山囡真有福气,到城里打工几年,就嫁了个城里人!
这时候,山囡的阿婆也蹒跚着走过来,阿婆个子矮小到人腰间,只能扒开人缝看新郎。有人见状就移动身子,让阿婆钻进人墙去。阿婆站在接亲人身后边,拢着双手,眼睛定定地看新郎,嘴巴张开着木木地笑。
不知谁往前挤了把,阿婆一下站不稳,身子前倾,两只干枯的老手就按在了接亲的城里人的身上。城里人回头望了眼,立刻掸掸衣服,一张脸慢慢挂了下来。新郎的脸上也显出了不快。
山囡的爹闻声跑了过来,拉起阿婆出了门。到边上,他恶着声说,让你到小屋里安耽坐坐,你跑过来凑啥热闹?阿婆站着一声不响,像个做错事的小孩。阿婆记得前几日家人就交代过她,山囡嫁到城里要体面,你一个老太婆腿脚不便脑子糊涂,不要乱走动让城里人看了见笑。
接下来,阿婆就搬了个椅子坐到院子的远处,一个人冷冷清清晒太阳。家里的花鼻狗蹲在阿婆身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忙忙碌碌的人群。
又是几声爆竹响后,接亲人照仪式把一件件嫁妆搬到车上。新娘子下了楼来,立在堂前板凳上,恭恭敬敬拜了天地祖宗,又湿了眼眶向父母道了别。这时候新郎就喜笑颜开把新娘山囡抱出了家门。人群又轰地一下跟随着去。
山囡在车里刚坐好,回过头来,忽然看见阿婆也颠着脚赶过来,矮矮的在人墙后边眼巴巴四处张望。山囡心里紧一下,她想摇下车窗朝阿婆喊一声,可是车却慢慢开动了。
待大酒店的喜宴完毕,天完全黑透下来。一对新人回到了安静的新房。山囡把新棉被打开,忽然就呆了一下,一双新布鞋展现在她面前。前天晚上,阿婆摸到山囡房间,把双布鞋递给她,说是囡囡结婚了,我也没啥好送的,一个夏天时间纳了双布鞋,你带了城里去穿。可在一边的爹当即就把鞋丢旁边了,说城里人怎么会稀罕这土东西。
阿婆是何时悄悄把布鞋塞到棉被里的呢?山囡脑里闪过阿婆紧跟着人群搜寻她的一幕。她呆坐一会,望着新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忽然就放开声音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