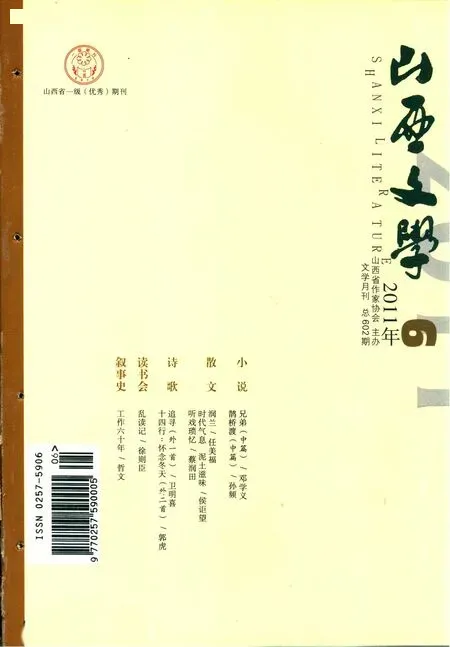润 兰
任美福
任美福散文小辑
润 兰
任美福
春之灿烂
1968年盛夏的一个早晨,我背上书包去上早自习。走到街上,眼前的一幕把我惊呆了:但见几百个人横七竖八睡满了一条街,枪支、行李扔了一地。他们看来是累极了,都在呼呼大睡,那情景和电影《战上海》中部队露宿街头的镜头差不多。我跑到教室,发现也全睡满了人,一个睡眼惺忪的年轻人,还举起一个茶缸喊:“缴枪不杀!”细细观察才发现,里面还有妇女、儿童、老人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邻县和顺两派武斗的杰作。“红总站”被“红兵团”打垮,星夜自和顺城沿清漳河一道川溃逃到我们村。由于陈永贵支持“红总站”,我们家乡与和顺县紫罗公社接壤,这里便成了“红总站”的避难所。公社各村都住满了总站“战士及家属”,我家也分配住进了一家八口人,这家人的大姑娘怀里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当晚,这家人就住进我家大北房。农人们是憨厚朴实的,热情接纳这落难的人群。我抱着柴火去给他们烧灶,两家人热闹得成了一家人。正在添柴时,一个小姑娘在我跟前蹲下来说:“来,我帮你烧!”我扭头一看,一张红扑扑的小脸,一双大眼扑闪着看着我,似乎在说:“行吗?”她是这家人最小的三姑娘,名叫润兰,和我同是12岁。母亲便逗她:“给俺做了媳妇吧!”她哈哈哈哈笑起来,可这一笑不要紧,满屋人的目光都聚到她身上了!
一个纯洁的少年女孩儿,不知是哪种造化的神奇给她注入那种灵秀?我至今也不明白她怎能爆发出那么动听的笑声,无丝毫做作,笑出那么感人的艺术美。啊——哈哈哈哈!她又在笑了!在她那具有感染力的笑声中,我二姐姐看着她连连说,真亲,真亲!她那笑声,动人的舒畅中仿佛有一种强烈的穿透力,直入你的心扉。她笑的时候,总是突然爆发,像带你坐了一只快艇,倏忽间爬上激浪高坡,随即又从波峰倾流而下,畅快淋漓滑入深谷。
因为她的笑声感染,我便偷偷打量她。浓黑的眉毛像延绵的小山峰一样,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人时像手电筒一样放光,那张红扑扑的圆脸总会让人联想到健康、活力、青春,贝齿洁白如玉,门牙上缺了一个豁口,可那豁口缺得正好,笑起来好迷人。
她在我家12岁长到14岁,她那青春的小身躯一举一动留给我的美好信息,多少年后我才慢慢解读出来。她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会说话:那两颗溜溜的黑葡萄就不用说了,额前的小刘海随风一摆,两只粗辫子一甩,飘逸着青春的活力。她常穿着一件粉红的上衣,到了夏天,总是一双用旧布条拼凑成布带缝制成的凉鞋,一种朴素得体的美。看她的背影,衣服总掩饰不住青春的韵味,静静地立在那儿,似风摆杨柳,弯弯的腰就像在说话。
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只是觉得她长得好亲,笑得好听,在一起好玩。反正喜欢和她在一起听她开心地笑。我们很快就厮混得如同亲兄妹,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谁叫她玩都不去,就喜欢和我在一起。我在街上写好板报,她就集合上小女娃们去参观,还炫耀:“看!这就是我家那房东小小写的,他还是村里学毛选的辅导员哩!”
夏天,我们小伙伴下河捉鱼,她坐在岸边光光的石岩上,挽起裤腿,一双小脚丫拍打着河水。有的伙伴用石头击水溅她我就阻拦,不让别人欺负她、逗她。吃饭时,母亲这样喊她:“媳妇,媳妇,舀饭来!”她便羞个小红脸恭恭敬敬端过饭来。遇我不上课时,她便关起门,不让别人进屋,一个人给我表演舞蹈《五好红花送回家》,蹦得活灵活现,一会儿她又学老大娘送儿子一下一下收头发,很像那么回事,滑稽得让我笑不停。
想听她笑我就约了她上房顶,胡谝乱侃,每次总是逗她笑得前仰后合。笑过之后便揶揄我:“你就谝哇,才不是呢!你咋恁会谝啊!”
农村是封闭的,更是封建的,对两个小少年也不例外,我俩的行踪成了总站人们和村里大人小孩逗趣的素材,弄得我和她不好意思在一起玩了,见了面总是羞个大红脸。无拘无束的光阴那么快就消失了,两个小少年见面还煞有介事地偷偷摸摸起来了。
一年后的一天,她要回和顺城家里走一趟,来向我道别,我担心地问:“不怕兵团的人开枪打你?”她说:“不怕,我悄悄就溜回去了,我回去给你捉一只刚出生的小兔子来,可亲呢。”她走了两个月,我天天盼着,不知是盼兔子还是盼她。
她终于回来了,给我带回一只小白兔。50里山路,走得她满面红光,俨然绽开的一朵桃花。她头上还冒着热气,一边喝水一边与我抚摸小兔子。总站的男孩子们在门缝里偷看我们,做鬼脸,她嗖地一起身,突然打开门,说一声:“死小小们!”然后用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灼灼逼人地瞪着他们,一言不发,一直瞪得挑衅的小男孩们跑得无影无踪。总站的男孩们说她和我的笑话,她每次都脆生生地回敬得他们一言不发为止。
不知不觉间,秋天又到了。那天我正在做作业,她悄悄跑到我身后,“呔!”吓我一大跳。
“带我摘杏去吧。”
“怎想起来去摘杏?”
“怎就不能想起来?”
“不敢。不怕人看见?”
“怕什么呀!你先走,我再去寻你……”
我便先跑到一个小山坡下等她。一会儿,听见她像一阵小旋风似的跑来了。待她追上我,我再跑到另一个地方等她。
刚聚到山杏树下,正庆幸没人干扰准备摘杏,突然山梁上传来猛烈的凿石声。哎呀不好,有人呢,我连连用眼色示意她快跑!她很听话,转身就跑了。一直看着那个小身影跑下山去,我才返下山。
之后,不知为何她总是央求我去摘杏,但几次都被我拒绝了。
可她却变得有点缠人,我的什么事她都想知道。我上山刨药材,一回来,她就过来问。中午我歇晌,她又溜进来。我穿的一双新球鞋灌满了土,还有臭汗味,生怕她看见我弄脏了鞋,她却怪得很,蹑手蹑脚过来非看我的鞋,还要扒开看个仔细,嘴上还念念叨叨:“哼,邋遢,半天就脏成个这!好臭!”
有一天,她抢去我的一个毛主席像章,我不依不饶,拧住她的手非要她还我。她不给,我就一直拧,拧着拧着她吃不住了,笑容消失了,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攥着像章的手松开了,像章掉到了地下。我一看闯了祸,像章也不捡了,也不知哄哄她,躲到黑煤池里去捡煤块儿,吓得扑腾腾心跳。不知把她的手拧断了没有?正在恐慌时,煤池墙上露出她的圆脑袋,我一抬头,她两眼红红的却是笑盈盈地看着我,脸上的泪珠还没有拭净,手里拿着那个像章说:“给你!”我赶紧说:“给你吧,我不要了……”
转眼到了1970年,“红总站”的人们已经在我家乡住了三个春秋了,我和她都长到14岁了。就在那年的一个晚上,我去离村13里外的一个小山村看总站人唱戏,第二天突然不演了。待我返回村时,傻眼了:所有“红总站”男女老少都走光了!路上只碰见她的父亲,我问:“润兰呢?”他说:“她早走了,她让我转告你……”连一声告别的话都没有说,相处了三年的小朋友就这样走了,一个春天的童话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夏之残缺
和润兰分手时未曾见面,她走后的几年我就经常回忆最后一次说话和玩笑时她的音容笑貌。可惜平时不留意,这最后的情景竟找不出来。
她走后我读完了初中、高中,回到农村劳动,后来到社办企业参加了工作,一晃过去了七年。1976年夏,和顺县好些单位欠厂里结算款,我长途骑车去要账。从厂里出发到和顺县城50里山路,骑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在想,这么近的路,这么简单的事,为何拖了七年呢?七年当中怎就没有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清漳河的发源地就在我村里头,这条河一直流到和顺县城。沿路顺流而下,后来才知这条河竟流过她的村前,也许她洗衣服就在这条河边,她与我共饮的是一条河水。
办完公事,在和顺县城中和街北头一个饭店吃了午饭,我便在和顺县城关搜寻起她的家来。我努力从印象中回忆七年前她给我描绘的位置,找到了最大的参照物两幢牌楼,就在县城中和街北门处。一前一后两幢牌楼多少年矗立在那里,上面凝聚了那么多久远的历史信息,其中一幢是明代所建,当时也不知是省级文物,只是感觉到那么气势恢弘,镂刻工艺巧夺天工。但未曾把那两幢牌楼细细看够,只觉内心一阵冲动,想快看一看我那小朋友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先去找她姐家,根据印象里她描绘的情景判断,认定与饭店隔街相望路西那个门楼小院一定是了。叩门之后,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问我找谁,我说找小兰。“啊?找我妈呀?”原来这就是当年在我家炕上襁褓中那个婴儿!总算找到了!她姐姐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带我去她妈家。她一家人熟悉的面孔一下子都见到了!
可唯独不见她!打量四周,偌大的老南房,屋顶上椽和檩被烟熏得黑糊糊的,满屋的家什没有一件亮丽的东西,唯有墙上相框里一张放大的女孩照片,顿添了小家碧玉的气氛。望着照片,我不禁暗暗吃惊:七年没见,出落得这么漂亮了!当年的稚气不见了,多了青春的韵味,少时那泼辣的眼神变成了淡淡柔情,只那弯弯的眉毛像初一的新月依然那么调皮。
几年不见,她竟变化这么大,真是闭月羞花之貌!真成了民歌里唱的“要命的二小妹妹”了!这十几秒的凝视竟看得我心里一阵慌乱……见了她会是什么样呢?只听她姐姐出去喊人:“快去地里把润兰喊回来,她在剪果树呢,告诉她就说丫儿房东的丫孩来看她了!”
我坐在炕沿边上,倚在大地柜旁边,她姐给沏了一大壶茶水。我捧着个大水壶,倒进碗里,呼噜呼噜一直喝水,浑身好不自在,好尴尬呀!静静地等着她,盼她快回来,心理上总感觉她回来我就自在了。她姐姐、父母不时过来问这问那,问得最关切的话题还是找对象了没有,这么灵气的后生不知有多少姑娘抢着跟呀。不一会儿,院里一阵嘈杂,从门口扑通跳进一个姑娘来。我抬头一看,啊!七年前那个小朋友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刚从地里回来,双颊红润鲜亮,真像一个熟透了的红苹果!她看到我后,本来走得红腾腾的脸庞霎时又罩上了一层红晕,美丽的凤眼只看我一下便低下头,羞怯怯立在那儿,抿着嘴只是笑,一言不发。我看她那两只手横竖不知放哪儿好。她父母、姐姐见状就一个劲儿骂她:“傻!傻!怎一句话不说?忘了房东丫儿孩啦?看看丫儿孩已经有了工作啦!”她才抬起头来,红着脸又看我一眼,说:“来啦?”这一下子把院里跟过来的人连同她家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她羞红个脸,腾腾腾走到我跟前,抓起瓷茶壶就给我倒水。我呢,也只是看着她傻笑。我问她:“剪树累不累?”她说:“怎不累?哪比你,都有了好工作了!”看得出她内心十分兴奋,倒水时,那双灵秀的手微微发颤。我心想:这双手还是会说话呀!
又没话了。她倚身立在柜子边,两眼闪闪忽忽看着我只是笑,还一个劲儿不停地给我倒水。我呢,一个劲儿地喝。趁她姐姐离开时,她突然悄悄指着我说:“比小时候更俊了!”我说:“你才是呢。你怎不那样笑了?”她撇了一下嘴说:“丫儿再也不那样笑了!”
盛夏的天好热,加之不停地喝热水,我又有点拘谨,脸上便汗津津的。她这时胆子大了,一直盯着我看,一个劲儿说:“快喝吧,喝呀!”她姐便嗔怪:“你怎傻一样催人家呀!”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也不知逗留了多长时间,说了多少闲话,我几次欲走,她都不肯,小樱唇一噘,嗫嚅着总是挽留我再待一会儿。但总归我还是要走了,全家人出来送行。送到小院栅栏门前,男女老幼全都自觉退回去了,只她和我相跟着走出来,那一截小胡同走的感觉好美!她低着头走得轻轻的、慢慢的,像怕踩死蚂蚁似的,她右手拿着个小木棍含在嘴里咬着,一言不发。我说:“把墙上那个照片给我吧?”
“那照得不好,我给你再照一张吧。”
“我就要那张,你一定给我放好,下次来拿……”
走出小胡同,到了大街上,两幢牌楼身后昂然而立,我本想还让她送,又觉得不好意思,心想家里人一直在等她回呢,便冒出一句违心的话:“你回去吧。”她呢,本想继续送我,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好意思起来,竟然停住不走了!唉,遗憾啊,那截路太宝贵了,怎么就忸怩掉了呢?只记得当时心里盼她跟上来,可不觉间已走出去了,与她拉开了距离!这个距离竟成了永远的爱情盲区。更糟糕的是:听她在我身后面喊:“阿夏,我再送送你吧?”我却言不由衷地回了句:“不用了……”
唉唉,美丽的青春偶像,仅见此一面,她动人的青春时期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天,只记得我走出一段路后,回望,她直直立在那儿,楚楚动人,手在刘海处挡着阳光望着我。
夏天是生长的季节,刚刚露头的春芽就缺了雨露……
那次分手后我好生气,我让一让你你就停住了?为何不再送送我?赌了气,好长时间里我多次到和顺县城都故意不见她。这一赌气便把以后的故事都赌掉了。后来去找过她一次又巧遇不在家,在那幢牌楼前我久久驻足凝视了半天。每次走到她家那条小巷前,便犹豫着不再前行,她亦没有给我任何信号。一次次,都让机遇擦肩而过。再后来,恢复高考了,我考上大学,四年毕业后忙忙碌碌一晃又是七年……两条本应相交的线却阴差阳错,平行地滑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可爱、美丽的润兰,她的年青时代,竟与我相见一次就画上了句号。
秋之苍凉
光阴荏苒,一次难忘的相见之后,竟一别就是十三年。
人生真如一梦。十三年后的一天夜里,无意间她竟走进我的梦里。她早为人妻为人母,可梦中的她依然是青春模样,只是冷冷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立在院中把头扭一边去了……梦里她的院落既空旷又杂乱,房子很破旧……梦醒之后,许久沉浸在梦里,不知她咋会在梦中找我?最感动的时刻是往日美好的怀念。现在的她会是什么样儿了?她过得好吗?她还保有那张动人的容貌吗?少年的活泼、青春的腼腆,我还能在她身上找到吗?
正好年初一个会议开到长治。会议结束后,我改乘路过和顺县线路的公共汽车,在和顺县城下了车。
一想到这个小城里还留着一份牵挂,心里便有一种别样的滋味。多年来,我印象里始终凝结着她少年时的模样,青春时期的音容笑貌,往日的老镜头总是不时闪现。
终于,那幢石牌楼又映入了我的眼帘。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牌楼依然如故。人哪,一生都在忙什么?当年怎不约她在这牌楼前好好观赏逗留?为何没有和她在这里散步叙话?牌楼是不会很快苍老的,可润兰是会的呀!为什么就不去好好地端详可爱的姑娘呢?唉,让我再一次从从容容仔细端详这两幢牌楼吧!那明代的石牌坊,是省级文物,比较珍贵。石雕契合得严丝合缝,镂刻的人物、动物栩栩如生,石狮的表情惟妙惟肖,牌楼匾额上书“陵京锁钥”四个大字。另一幢牌楼亦十分气派,斗栱美不胜收,石狮形态各异且有点顽皮,像活的一样。匾额上书“龙章五锡”,下面长额又写“珍宝祖国艺术遗产”。当年咋不与她一起在这里研究一番呢?她住在这里,牌楼上蕴涵的故事她知道吗?
这一次,我径直走进她母亲家。还是那间大南房,一进门,通铺炕上坐着一个姑娘笑眯眯看着我,她和青年的润兰太像了!这……是谁呢?润兰不会有这么大的孩子啊。一问原来是当年门前迎接我的那个小姑娘,在我家里度过了婴儿时期的那个孩子。润兰的父亲老了,话少了,他只淡淡地说了声:“润兰嫁到风台了……”
我只好到县财政局先做了顿客,其实为的是借一辆自行车,说要去看亲戚。第二天才奔到风台村。在村前一个小道边,我静了一会儿,独自猜想:她会是什么样儿了?
当我推开那两扇吱吱呀呀的街门后,惊呆了:院落的情形,房屋的走向,和我梦中所见太相像了!我无法破解这是怎么回事。而当我推开她的西房家门时,几乎是在我看见她的一刹那,她脱口而出:“阿夏?”
我笑一笑:“十三年了,你还能认出我来?”
“哎,剥了你的皮丫儿也能认出你来!你怎想起来看我?”
“我去长治开会,前几天梦见你了,开完会专来看看你。”
她不说话了,柔柔地盯着我一直看,看,许久,轻轻地说:“你还是那样精干,你还是那样帅气,你好像一点也没变啊……”
经她这么一说,我才好好审视起她来。才十三年,那个美丽的润兰变样了。无情的岁月把一张光彩照人的青春俊脸碾压得痕迹斑斑;调皮的粗壮的小辫子不见了,原来鲜亮的“红苹果”像是在冬日储藏久了,显得有些干皱有些泛黄,她怎么还有了明显的抬头纹?还是那双凤眼,可不再水灵;还是那双秀眉,却再无韵致。唇里的贝齿曾经如中秋的白马牙玉米整整齐齐,而今,那个豁口还在,却怎么也找不回那种迷人的调皮可爱了。一去不复返的岁月,把她如花似玉的风韵、鲜活亮丽的朝气,连同那天真活泼、腼腆娇羞冲刷得荡然无存……眼前的她,就是那个美丽、调皮、活泼、勇敢、相处了三年的小朋友吗?还是那个娇羞动人的润兰姑娘吗?
她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唉,你别看了,丫儿不讨人喜欢了……”如今的她,不再是活泼调皮的小朋友了,也不再是腼腆羞涩的大姑娘了,她是为人妻的女人了。她显得从从容容,用手摸我的粗纺呢衣服:“你从小就精干,现在还是,唉,看这扣子快抛下来了。”她穿针引线,要帮我缝那扣子。唉唉,虽然她容颜变了,可那种心底里的柔情依然!往日岁月凝结的那种情霎时穿透时光隧道,眼前的她叠印着往日的形象,回归着以往的纯情,在视觉中产生着亲情的美……
“孩子呢?”
“大小子10岁了,二小子8岁。”
“他呢?”
“在煤矿下窑,中午不回来的。”
“生活还行吧?”
“行什么呀,你都看见了,就这样了。”
“嘣”的一声,她咬断了线。她拿针引线的动作、咬线的神态一下又叠印出当年那个小姑娘给我缝红袖章时的情景。
“她在干啥?”
“当孩孩王呢。”
“你今天来看我,她知道吗?”
“我不是还没有回家嘛。”
“丫儿就知道你是个土地爷。”
“土地爷是啥?”
“就是怕老婆!嘿嘿嘿!谅你也不敢告诉人家……”
这时,她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欲张口却又止,脸也微微红了。我问她:“你想说什么?”她说:“唉,算了,说那干啥?……”我心想:别看少年时期三年在我家住,青年时又相见在她妈家,可又何时说透过一句心里话了?便说:“你说嘛,现在还有啥不能说的?”
她长叹了一口气,“唉,你呀……”
“你在恨我?”
“我恨你咋哩,恨得上呀?你见了丫儿一面再也不来了,丫儿等你再来,看看丫儿,可再等不来了,丫儿也不知怎么作害你了。”说着,她的眼眶湿了,“你可是不赖,还有心来看我……你别走,等我给你做好饭吃。”
她麻利地挽起袖子,切了韭菜,又炒开了鸡蛋。她想给我多说说话,可那两个淘气的儿子一阵阵打架,过来找她评理做主,害得把我们谈话一阵阵打断。她总是耐心地劝他们:“快去吧,啊,叔叔还有事,叔叔还有事……”孩子一走出门,她又给我聊起来,我也由不得想探寻过去未解开的两人心中的谜。我问她:“你在我家住时,别人开玩笑逗咱俩,你是怎想的?”
“那时我嘴上骂他们,心里可高兴呢,我还盼着他们说呢,可对他们逗咱俩的事,我那么小能想多少?羞死个人,不敢想。那时丫儿哪里知道你是咋想的。就是喜欢和你在一起。”
“你那时怎老叫我去上山摘杏?第一次叫我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脸都红了。”
“那时我们总站女娃们聚在一起议论,才知道她们都很喜欢你,但又觉得你和所有的小小们不一样。那些小小们虽长得黑头愣脑,但不知怎么三两下就把女孩们骗住了,总站和你村的男男女女们半夜三更在牛棚里都有笑人事呢。可你那时就知道看书,女娃娃们都认为数你胆小,书呆子。……后来,我老想叫你上山摘杏,就咱俩人……唉,反正你是个傻帽。”
“嗯,我现在也不灵……那年,我去你家看你,你怎送出我来不走了?”我总认为当年她再前进会是另一番风景,她在众人的目光下敢送出我来,却在两人的世界里踌躇不前,正是那一截路,她给画上了休止符。
听到这里,她把和好的面“叭”地一下摔在盆里,嗔责的目光盯着我:“你还有脸说呢?丫儿不好意思嘛,丫儿小时候敢,丫儿长大了那还不害羞呀,怨丫儿呀?就算没送你吧,咋后来就再也不见了嘛?丫儿可是有心等你,可丫儿不敢等了,再等邻家都会说丫儿有毛病了,家里也不让等了……”
“那你哪年结的婚?”
“23岁。”
“我在上大学时,有一次在部队看电影,一下又想起了你。”
“唉,开始我等你,看见别的小小叫上女娃去看电影,更是急死个人,晚上也想。后来想:唉,没用,没用。”
就这样,两人一边包饺子,一边聊着过去的事。她抓起我的手说:“你的手还是那么白。”她这一动作让我想起当年她也是这样抓起我的手,听手表的滴答声,那是我刚买的手表。
她一直唉唉地叹气,一切回忆、留恋都渗透了惋惜:“唉,连电影也没叫我看一场!”总之都是过了期的废话。忽然,她捏饺子的双手不动了,脸上泛起了红晕,偷偷笑了起来:“你呀。”又摇了摇头,欲言又止。我问她:“又想什么了?”她像是狠了狠心嗫嚅出一句:“你那么聪明一个人,咋那么笨?白喜欢我一回,小时候不懂,长大见了我怎就一点也不知道……”
在我吃饭的时候,她脸上现出了满足的神情,也许是看着她的劳动成果让少年的朋友享受上了心里快意?抑或是看着这一霎间的情景像幻想中理想的圆梦?不得而知。
该分手了。我要赶公共汽车,下午两点钟的。我问她要那张照片——那张当年在墙上挂着的玉照。她说:“唉,找不到了,结婚后不知我妈给丢哪里去了。”我说:“一定给我找找,一定找到啊!”
她提出要去车站送我,我说不必了,城里车站离这儿路还挺远的。她却说:“不!丫儿一定要去送你,你先走,我换了衣服随后也骑车去!”
还不到两点钟,我在车站候车室见她来了,她特意换了一身崭新的、过年穿的深蓝色衣服,那是她最好的衣裳吧。在候车室与我一起等待了大约半个小时。在这个时段里,两人都没有话,不知是该说的都说了,还是想的不愿说,也许一切都在不言中。我上了车,探出脑袋与她告别。车越走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然后消失……
唉,润兰呀,那一年你怎不像今天这样执著地送他呢?少年的你是幼稚的,却是勇敢的、早熟的,可他是憨愚的、不更事的;青年的你是一枝含羞草,可他是不懂的;而今的你依然是深情的,却只剩下无奈和遗憾了,两人只握着一张过期的船票。
那天我多想听到她的笑声,但那让我永生难忘的笑声却再也没有听到。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丽动听的笑声永远地消失了,那张玉照也永远失去了下落。
冬之希冀
大约过了三年,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儿找我。我打量她,似曾相识。那女孩儿却是又调皮又大胆,说:“有一个人想你呢。”说完嘿嘿笑了,随后润兰走进了我办公室的门。女孩儿是当年在我家那个婴儿,24岁了。那一天我很忙,没顾上给她们多说,她们找我办事,我把她们送下楼。可那次走后她们再也没有来……
拙笔的回忆,记叙不尽岁月年轮的生动和平淡,描述不准多少年心灵的感动与遗憾。多少次不经意地想起:她还好吗?今天的她该做婆母了吧?该有孙儿了吧?她苍老了吗?她会在偶尔一个不经意的意念里想起少年的朋友吗?就要快进入老年了,老年是人生的冬季,善良亦是一种力量,但愿她收获得多多,生活得安详。
抽空,我一定还要去看看她,38年前的少年朋友。但愿那时的描绘,是清风,是春意,不是萧瑟,不是苦涩。
责任编辑/吴 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