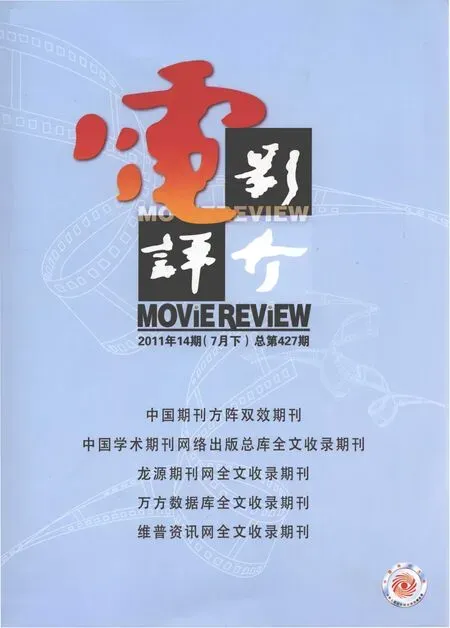让观众感受和思考:从《莉莉•玛莲》看法斯宾德电影中的现实主义表现
一、引言
作为新德国电影运动的重要导演,法斯宾德的电影创作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德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无论是在其早期的《爱神比死神更冷酷》、《恐惧吞噬灵魂》,还是在后期的“女性四部曲”——《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莉莉•玛莲》、《罗拉》、《维洛尼卡•福斯的欲望》等影片中,他都始终以冷静而理性的眼光深入探讨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对德国历史和现实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和批判。因其影片大多直面德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并揭露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因而可以算作是现实主义电影。
然而,在法斯宾德的现实主义影片中,我们却发现许多与传统现实主义电影不大一样的东西,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的那种直面现实、抨击社会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增加了许多极具个人风格的表现手法。在其众多的影片中,我认为《莉莉•玛莲》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较全面地体现了其创作风格。因而本文将以这部影片作为主要的分析文本,重点探讨法斯宾德电影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二、影片《莉莉•玛丽》中的现实主义表现
1、题材和内容的现实性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其美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影片的题材上。而在法国电影学者克•克卢佐看来,现实主义电影的题材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有社会反响的题材,如就业、住房、青少年犯罪等;另一种是有政治反响的题材,如战争、种族冲突等。[1][1,P222]它们有的是作为影片故事的发生背景,如美国南北战争之于《乱世佳人》;而有的则是作为影片主题加以表现,如越南战争之于《现代启示录》。但不论是作为影片的故事背景,还是作为影片的中心议题,它们都体现着创作者直面现实、面向社会的勇气和创作立场。
法斯宾德虽然在其早期创作中主要受法国新浪潮导演们如戈达尔、罗梅尔等人的影响,而且也始终坚守着“作者电影”的创作理想,但是他的“作者电影”与法国新浪潮导演们所倡导的表现自我的、“自传式”的“作者电影”不同,他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关注德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并通过影片表达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因而,他的电影往往取材自现实生活或是历史真实事件,具有较强的现实观照性和历史洞察性。影片《莉莉•玛莲》即是取材于历史上的一段真人真事。它原为一首歌曲的名称,由当时德国女歌星拉勒•安得森演唱而迅速走红,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流行歌曲,拉勒•安得森本人也因此而一举成为红极一时的大明星。与此同时,拉勒正与犹太作曲家罗尔夫•利贝曼热恋,然而由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两人终究未能如愿结合。最终,残酷的战争使拉勒失去了一切,并毁掉了她的爱情。三十多年后,新德国电影运动的战将法斯宾德将这段真实、浪漫而悲戚的爱情故事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在影片中,导演将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置放于二战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展现,把个人的爱情悲欢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影片中的爱情悲欢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同时也使得影片本身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然而,由于影片涉及了二战中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血腥历史,使得影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德国政府当局的严厉审查,以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强烈质疑。同时,创作这样一个敏感而具有强烈“政治反响”的题材影片,对于身为德国人的法斯宾德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在面对自己国家的这段丑恶而血腥的历史时,他将无法回避对历史的追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民族的伤痛。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战争进行反思。在影片中,导演并没有把战争作为一个简单的时代符号来表现,而是深入挖掘战争背景下艰难生存的个体。在影片中,歌手维莉始终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孤独个体,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她无能为力,只能任人摆布。她一心苦苦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然而却被战争给无情地摧毁了,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其先前深爱的男友竟最终背叛和离弃了她。同时,天真的她一直以为自己只要好好地唱歌,就可以取得成功,然而却不幸最终成为政治的玩偶和牺牲品。由此可以看出,战争本身不仅在肉体上直接毁灭了无数无辜个体的生命,而且还摧毁了无数像女主人公那样的个体幸福(包括爱情和家庭等)。同时,从女主人公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体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影片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尽管令人扼腕,但导演并未对其给予过多的同情,而是尽量克制,以使观众尽量从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中超脱出来,进而思考整个战争对个体、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点从影片相对开放性的结尾(导演把最后一个镜头对准波澜的江水,而没有安排像许多情节剧中女主角伤心欲绝而跳水自杀的悲惨结局)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使影片跳脱出了一般情节剧的套路,另一方面也给观众以广阔的思考空间。
2、叙事手法:情节剧+间离法
“如果说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作家来说,是在自然主义/真实主义还是“被解释的世界”之间作一取舍;对于画家来说,是选择与现实相符的摹仿(照相、逼真艺术、移印图画)还是移位/非具象表现,那么,在现实主义电影中,则存在着故事性还是纪录性之争。”[2],P209]确实,在创作现实主义影片时,有的导演可能会更偏重影片内容的真实性和影像的纪录性,采用大量的长镜头和景深镜头,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地在波地》等;而有的则在坚持反映现实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注重影片的故事性和观赏性,如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
而对法斯宾德来说,影片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再声称自己不拍深奥莫测、晦涩难懂的“作者电影”,而要拍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为此,他在影片的叙事上下足功夫,极力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手法,倾心学习道格拉斯•西尔克情节剧的叙事策略,尽量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让观众在轻松愉乐的气氛中感受和思考。同时,他也主张情节剧在具有观赏性的同时,应该蕴涵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和批判。他认为“电影必须在一定的时候停止作为电影,成为故事,而应开始变得活生生的,使人能提出问题”,也即是使观众“从故事中脱离出来,去面对他们自身的现实”,并思考“我与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而这在他看来才是电影“最根本的”。[3]他力图把好莱坞的情节叙事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批判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好莱坞式的德国电影”,即“它尽管也具备好莱坞的特征,但是不像它那样虚假骗人,它们应该同时是能够对体制进行批判的电影。”[4]为此,他在借鉴好莱坞情节剧的叙事技巧的同时,又借助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法”,采用各种反叙事手段来摧毁观众对影像的幻觉,将观众从银幕内拉出来,并运用自己的思辩力对银幕故事进行思考。
例如在影片《莉莉•玛莲》中,导演一方面采用好莱坞的情节剧模式,设置三条情节线(主线为女主人公维莉与男友罗伯特之间爱情故事,副线一为战争的发展进程,副线二为地下组织秘密营救犹太人),并让其交错发展,从而把动乱时期的爱情悲欢叙述得哀婉动人,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另一方面,导演又运用各种间离手段如镜头运动、光影、构图等来打破观众的幻觉。其中,镜子在影片中的运用对营造间离效果起到很好的作用。如影片在表现女主角维莉在酒吧唱歌的那个段落中,巧妙运用倾斜的玻璃墙来反射人物形象,使得画面的构图显得有点“怪”,从而打破了观众对维莉优美演唱的沉醉,而把关注点投注到酒吧的整体环境和各色人等。更重要的是,导演运用这种特殊的构图来表现两个纳粹军官,更是暗含着导演对纳粹分子的嘲讽。此外,影片在表现维莉收到众多歌迷的来信时,导演故意使用了惊险片的经典镜头语言——倾斜+黑影式的构图、紧张而惊险的配乐,再加上女仆的“你终于回来了,现在情形可不妙啊”这句很具紧张感的对话,使得本来应该充满惊喜的场面显得危机四伏,而这也暗含着维莉成功的背后充满了危险与阴谋。
这种让观众跳脱出影片并思考的做法,后来被有些批评家拿来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法相提并论。针对这点,法斯宾德一方面承认自己确实受到过布莱希特“间离法”的影响,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使用布莱希特的方法(即间离法——笔者注),你可以看到感情要在目睹感情的同时进行思考,但你永远不能感受到感情。……我认为我走得更远些,我让观众感受和思考。”[5]这种让观众在观影时既感受影片中人物的情感,同时又思考影片故事和影像背后所暗含的意义,“让观众感受和思考”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正是其一方面借鉴好莱坞情节剧的叙事技巧,另一方面又吸收布莱希特的“间离法”的宗旨所在。
3、电影语言的风格化
真实是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灵魂,同时也是巴赞、克拉考尔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家所极力倡导的创作原则。在巴赞看来,电影应该“再现世界原貌”,并按现实生活的实际流程来结构影片,从而实现“完整的现实主义的神话”[6]。为此,他极力倡导长镜头、景深镜头和场面调动等创作手法,以追求影像的真实感。然而,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现实主义电影越来越突破了这些似乎已经有些僵化和过时的创作手法。纵观电影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众多经典的现实主义电影中,其实存在许多表现主义,甚至是超现实主义的镜头语言和表现手法。例如影片《现代启示录》,在表现马龙•白兰度所饰演的叛军将领的形象时,采用了非常具有表现性的光影构图和音响效果,而这种表现手法并不会破坏影像的真实感,更不会破坏影片整体的现实主义品格,相反它在一定程上加深了影片的批判和反思力度。
同样,在法斯宾德的现实主义影片中,也存在着许多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极具表现性的电影语言,在此,我把它称为现实主义的“风格化”表现。例如在影片中,大量曝光过度的灯光的运用,就具有强烈的反现实主义倾向,它使得许多室内景显得“不自然”,甚至让观众感觉别扭。有的光甚至极具风格化,让人产生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如影片在表现纳粹士兵的形象时,采用红光,把士兵们的脸部表现得通红通红的。更极端的例子是总统生日的庆祝晚会,在这个段落中,从影片画面上,我们可以直接目睹的光源只有几盏白炽光,按常理画面上应该是白光,然而整个段落的画面中却全是布满了异常的红光,这显然是有悖生活常理的,是“不现实”的。导演之所以采用这种高度风格化的光影,我想,主要是为了突出表现纳粹分子的疯狂和非理性。此外,影片的声画剪辑也多处具有极强的表现性,其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音画蒙太奇段落:当广播里第一次播放《莉莉•玛莲》这首歌时,随着歌声的响起,画面上展现的却是战场上连天炮火和士兵死亡的悲惨场面。影片把优美的歌声与惨烈的战场画面这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内容对位组接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法斯宾德之所以在这部现实主义影片中,加入这么多“风格化”的电影语言,我想,这主要源于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一次采访中,他曾明确指出,“我所说的,并为我所希望的现实主义,应该是发生在观众的头脑里,而不是映现在银幕上的。……我所要的是一种空白的现实主义,它允许现实主义,但又不造成人的自我封闭,如果拿给人们看的都是些他们经历过的东西,我认为,那样人就会出现自我封闭的情况,因此必须提供一种使人接受美好事物的可能性,事物越是真实,也就越应奇妙地自然。”[7]这种“奇妙地自然”也许就是法斯宾德在其现实主义电影中所追的“风格化”的“真实”吧。
三、结语
从法斯宾德的现实主义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题材与好莱坞叙事技巧、影片的现实批判性与娱乐观赏性有机融合的某种可能性,他为“作者电影”与普通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正如德国著名电影史家乌利希•格雷格尔所指出的:“法斯宾德的影片并未根本改变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是这些影片却使‘作家电影’摆脱了与公众隔绝的状态,产生了新型(尽管它们是从现存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的电影。它严肃地对待观众要在影院中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需要,归根结底也是对于娱乐的需求。”[8]同时,他也指出“这种新型电影就其剧作结构与电影语言来说,是异常明白易懂的”,它在叙事上采取好莱坞情节剧的那种“直线叙事方法”,同时又“对当前的争端表明了态度(尽管是以一种主观主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了批判,用拔高和夸张的方法给人们以‘启发’甚至‘启蒙’。”这种既尊重观众,具有较强娱乐性和观赏性,同时又兼具思想性和现实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影片,正是我国当下电影所需要但又极度缺乏的,值得国内电影创作者们学习和借鉴。
[1][2]克•克卢佐.法国电影中的现实主义潮流[J].顾凌远译.世界电影,1984,2.
[3]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无序的幻想[M],法兰克福菲舍尔出版社,1986.47.转引自滕国强.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一位英年早逝的“新德国电影”奇才[J],当代电影,1992,4:70.
[4]转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赖•维•法斯宾德作品回顾展观摩资料[M],第9辑.
[5]见诺贝尔特•斯派洛.我让观众感受和思考:法斯宾德访问记[J],电影家,1977,2:21.转引自(美)布•波克尔.热感情与俗艺术:法斯宾德的叙事策略[J],仲云译,世界电影,1993,1:78.
[6]安德烈•巴赞,“完整电影”的神话[J],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8.
[7]汉译电影丛书.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M],威尔弗里特•维甘特.对法斯宾德电影的观察[M],西德慕尼黑卡尔•汉译出版社,1985.89.转引自滕国强.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一位英年早逝的“新德国电影”奇才[M],当代电影,1992,4:71.
[8]乌利希•格雷格尔.世界电影史(1960年以来)[M],郑再新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