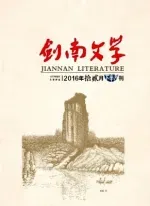深 夜
● 陈 霁
深 夜
● 陈 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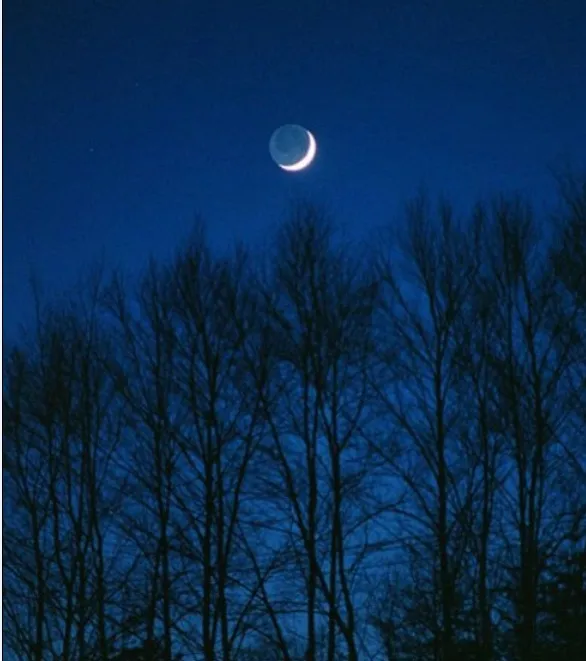
1.
对黑夜的恐惧贯穿了我的童年,甚至更久。
记得儿时的夏天,热得睡不着,男女老少都拥向晒场,铺一张席子,顶满天繁星,听大人天南海北地吹。一个言之凿凿的故事,讲的是邻近乡镇,一户有名有姓的人家,发生了一连串诡异而恐怖的事件。绝境中,请一位阴阳先生来家勘验,发现是他家的老人埋进了“养尸地”,即鬼穴。挖开墓穴,打开棺材,人们发现,掩埋已久的尸身比活人还鲜活。可怕的是,原来很慈眉善目的老人家,身上已经长出兽毛,嘴里现出獠牙,即将成为厉鬼,在深夜飞出来吃人。
虚拟的一个青面獠牙的形象,衍生出没有穷尽的故事版本,让我们既入迷,又恐怖。鬼是另外的一个图腾,也是孩子们另外的一个保姆。它以超自然的可怕力量,让我们在夜里中规中矩,不敢跑出大人的视野。好在孩子们的睡眠都好,很难听说哪个孩子会失眠,将鬼带入梦乡。
稍大,我们又知道了还有远比鬼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同类。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说明黑夜不仅仅是掩护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更多的是滋生罪恶,掩护坏人,与罪恶合谋。坏人往往是在暗夜出来活动,阴谋总是在黑暗里酝酿。是他们,以及他们代表的秘密,再加上另外一个深夜主角——鬼,一起填充了那个黑暗的巨大空洞。
因此,在我的词典里,很长时期的黑夜都是带有原罪的。夜的深度,有时候就是罪恶的刻度。
上世纪60年代末的射洪小城。街头红红绿绿的标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挂黑牌戴高帽子的游街示众,乘着大卡车呼啸而过的武装造反派和零星的枪声,在一个县城里缩写着那场大革命。经常停电,乱世之夜就格外的长,让人不安。于是,人们早早关严房门,吹灯入睡。文化馆远离居民区,独守一片老林,出门就觉几分阴森。
一个夏夜,我和父亲在沉睡中突然被外面巨大的响动惊醒。准确的说,是父亲寝室外面的墙被什么物体沉重地撞了一下,接着就听见脚步杂沓和惨叫、叱骂和厮打的声音,令人心惊肉跳。外面的动静太大,父亲穿衣起床,悄然出门。我跟出去,看见平时晚上一片黑暗的文化馆外临河一面,一盏路灯居然亮着,昏暗的灯光照耀着几个人正在将一个黑壮的中年男人五花大绑。他几乎全裸,湿淋淋的躯干肌肉鼓凸,像青铜。我一眼看过去,正与他可怜巴巴的眼神相遇,令人立即想起《收租院》那些苦难的形象。但是,从他湿透的裤衩里露出的半截阴茎,像一条丑陋的肥嘟嘟的什么虫,让我为他感到无地自容。几个汉子将他捆结实了,就开始打他,用脚踢,用竹块打,用皮带抽,要他交代罪行。但是,那人被打得遍地打滚,只顾得上哀叫。他的叫声凄厉,有些夸张,但仍直击人心,令人动容。这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一个小伙子,形象俊朗,白净面皮,好像是文化馆下属曲艺队的,姓肖。他手里提了一支左轮手枪,一边用穿了塑料拖鞋的脚朝那人身上猛踩,一边还用枪管戳,嘴里吼道,老子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好不容易才知道,那人趁夜深到公园河里用手网偷鱼,在文化馆外的河边被抓了个正着。盗贼。这是所有人见了都会同仇敌忾以对的公敌。不过,爸爸和文化馆的叔叔阿姨们都觉得那伙人下手太毒,严正要求他们将贼交到派出所去。但是,他们哪里听得进去。他们继续对他实行群众专政。一个精瘦的小伙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根木棒,从背后对准刚刚挣扎站起的贼就猛击了一棒。那贼虽然强壮,有宽厚的肩背,但还是吃不住那冷不防的一棒。只听嘭地一声闷响之后,他倒下去了,再也没有爬起来。几个人认为他是装死,再踢了几脚,看看仍然没有动静,才拖着他离开。
第二天上午,有消息从街边卖菜的农民口中传出,昨天晚上城郊紫云公社的一个菜农不知道被什么人打死了,扔在人民医院围墙外。
我马上就联想到昨天深夜那骇人听闻的一幕。
天哪,他已经死掉了吗?我想,他的年龄跟我爸爸差不多,应该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吧?从今往后,那孤苦伶仃的孩子该怎么办啊?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那个差不多就死在我的眼皮底下的“贼”和他的孩子,突然就和我拉近了关系。他们可怜哀哀的眼神,让我久久牵挂,不安。
同时,贼,也因此由抽象而具体。这时,他们身上原先附着的邪恶、猥琐和或多或少的恐怖,顿时消减大半。
贼纵然是千夫所指,但是除了运气不好撞到少年英雄刘文学手上那个偷辣椒的老地主外,其余的贼,那时的政治身份其实都很模糊。虽然犯事时人人喊打,然而事后他们往往还是能够顺利回到人民的队伍。革命群众批斗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时,他们还可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像是最彻底的革命者。甚至,还有曾经被打得死去活来的贼,摇身一变,成为高举大旗的造反领袖。反倒是低头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那些“阶级敌人”,善良,卑微,低眉顺眼,身上看不出半点邪恶,与常人无异,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也许,真正的阶级敌人都在布告上。文革使布告成为最热门的通俗读物。公安局门口,城墙边,一张张布告前总是人头攒动。一排剃了光头的黑白照片下面,一个个名字,有的还被打了血红的大叉,各自扛着“恶毒攻击”、“反标”、“偷听敌台”、“反攻倒算”、“投机倒把”、“破坏军婚”、“流氓”等罪名,雄辩地标示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布告人物中,我唯一能够将名字与本人对上号的是一个叫邓南山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据说,他自封为皇帝,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还传说,每个新入伙的成员,都要从自己身上割一块肉下来给他吃,以示效忠。
这是一个全县人民恨不得要千刀万剐的吃人恶魔,理所当然地被判了死刑。
那时枪决犯人,也许是怕劫法场,也许是怕造成场面混乱失控,总之刑场都是临时决定,绝密。不过我很骄傲,作为高一学生,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射洪县中队有内线。因为他们大院门口的巨幅雷锋画像,就是我不久前画的。所以这次枪毙犯人,连执行行刑任务的战士是谁我都知道。当公判大会开完,上万群众在广场眼睁睁看着载着犯人的汽车绝尘而去时,我已经提前到了即将行刑的山坳里,等候那个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于是,我亲眼目睹了从汽车由远而近、胸前挂着纸板背后插着木牌的邓南山被拖下汽车、按着跪下、然后两声枪响倒地的全过程。
待架着机枪的卡车载着公安局和县中队的一干人走远,我和不多的一群观众才走近邓南山,要零距离地看清这个传说中的魔头是何面目。不过,他仰面倒下时,脸被原先挂在胸前的纸板盖住。我大起胆子,一脚将写着“反革命集团首犯邓南山”的纸板踢开,却发现躺在一团血污里的邓南山,一脸油黑,眼睛半睁半闭,不过是一个最常见的那类壮年农民形象。
糟糕的是,我踢过邓南山的那只脚,心爱的军用胶鞋糊上了污血。中午,直到晚上,我都无法正常吃饭。污血,以及想象中邓南山吃的人肉,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胃神经。更可怕的是,自以为冒犯了邓南山,他的鬼魂可能纠缠,报复,总觉得有什么祸事会随时落到我的头上。
这以后的许多个深夜,我都被噩梦惊醒。刷过石灰的天花板像银幕,定格着邓南山蜷曲在血污中的影像,令我心跳加速,嘭嘭如鼓,担心他随时可能伸出的魔爪。
2.
高中毕业那个晚上,我与好朋友唐健、李强散步。此前的很多个周末,我们都在夜色笼罩中的马路上走啊走啊,如同热恋中的情人。现在,告别了学生时代,也许我们从此就天各一方,所以那天的散步就有了告别仪式的意味。
我们出了县城西门,往郊外走,一直走向田野深处。
田垄像切豆腐,将辽阔的土地分割成大块,形成四通八达的道路。但是夜色笼罩了一切。黑暗使我们失去了方向感,就像我们所处的1976年,躁动,迷茫,看不到出路。不过,夜空飞扬着柑橘花香,似有少女飘然而过,让刚出中学校门的小青年兴奋。我们不知不觉就已走进夜的深处,想象的深处。
唐健和李强侃侃而谈,都是形而上的话题。李强的理想是机械工程师,研究汽车,或者设计飞机。唐健的目标,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只是感觉很大,与哲学、政治经济学有关,甚至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这类经典著作有关。他们的理想都像是顺理成章,有水到渠成的一天。但是我的理想却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不过是希望像爸爸那样,在文化馆,天天画画,经常被人尊敬地喊“陈老师”。然而严格地讲,这还算不上是我的理想。因为这个理想对我而言太大,很不现实。稍微靠谱一点的是凭一手好画,到某个工厂当工人,到一个小剧团当一个美工。不过,因为父亲的出身、历史问题,因为农村户口,我就是在工厂、剧团当正式工也不怎么现实。学生生涯已经结束。我的理想,像夜空里的那几颗稀疏的星星,远在天边,若隐若现。它们发出的微光,面对深邃漆黑的夜幕,无法洞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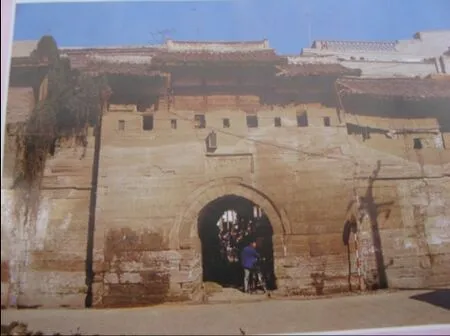
射洪老城墙
几天以后,我回到了梓江边上那个小村。
这里不是我的出生地。我甚至不认同它是我家的所在地。一个不大不小的老宅院,曾经是曾祖置下的产业,但是现在成了十几家人挤在一起的大杂院。我家拥有三间偏房,但是母亲生病,弟弟妹妹上学,他们都在城里,现在由我独守。虽然父亲出生、成长在这个小村,他身上有太多这个地主大院的基因,但是我早已把自己从这里庞杂的根系里拔出。几个月后,我奉命在村里画宣传画,其中就在老宅的高墙上画了一幅分别举着榔头、锄头和枪杆的工农兵,他们虽然指向不明,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幅标题揭示了一切。我用广告颜料调合石灰画成的“杰作”,至今清晰在墙。
这不是我作为一个共青团员的觉悟,大义灭亲,而是时代的规定,形式和内容都别无选择。
同样,它也标明了那时我在这里身份的尴尬。
这是一个连土生土长的年轻人都梦想逃离的地方。人多地少,一年的汗流浃背也难以糊口。未嫁的姑娘们有二次选择的权利。条件好的梦想嫁食品站、供销社卖肉卖货的职工和乡干部,至少也要嫁森工局的伐木工人。一般的向往着成都绵阳那些平坝地方,差的也想远嫁据说可以吃饱饭的外省,哪怕是新疆。村里光棍扎堆。而小伙子们,人人有打光棍的恐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白日梦,就是到什么地方去倒插门。满仓他哥哥,从部队复员两年讨不到老婆,就“嫁”给了外乡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寡妇。
我回到老家不久的一个深夜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老光棍在一个寡妇家里被寡妇的儿子所杀。这个乡村版的《哈姆雷特》,有多年情仇,其实也是因为光棍太多,女人,性,过于稀缺。
青山,绿野。瓦屋,炊烟。狗咬,鸡鸣。与陶渊明无关,更与梭罗无关。田园牧歌的表象,轻易被生活残酷地撕开,把我打回在农耕深处的原形。
单薄,文弱,一直做着画家的梦,没有当农民的心理准备,更没有准备好一副可以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的身板。尤其是抢种忙收,紧张如同打仗,把人累得死去活来,每一天都是难以趟过的水深火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昼长夜短,时间仍嫌不够用,只有两头披星戴月,挤占睡觉的时间。这时的农民,属于自己的只剩下了深夜。
我的理想,这时已经缩水为最简单的东西:睡觉,美美地睡一觉。
好不容易熬到大忙过去,却传来了纯的死讯。大我两三岁的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好,形影不离,几乎是我在乡间唯一的朋友。他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和我的父母差不多也是朋友。纯虽然也长在乡间,但毕竟母亲是教师,父亲也是旧军人,熏陶出不同于普通农家孩子的气质。喜欢读书又都拥有一些书,是我们成为朋友的主要原因。他刚在邻村一个叫天台山的地方当上赤脚医生,我是在准备去看的前夜才知道他的死讯的。他的死因极不光彩:搞大了当地姑娘的肚子,然后吃了整瓶的安眠药,让自己永远沉睡,逃离绯闻。
在充满诡异的小村里,我愈加感到迷惘和绝望。
每天晚上,我的小屋里都会响起口琴声。我的敦煌牌口琴是我最好的深夜伴侣。我已经学会了用舌头抵触琴格,一吐一缩地打拍子,随心所欲地吹奏会唱的歌曲。我吹口琴有拉手风琴的酣畅感,让我十分投入。但是我早就没有了《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之类的豪迈。只有《北风吹》、《绣红旗》以及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啊朋友再见》这样的曲子,忧伤,悲壮,以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无法回避的死亡气息,与我的心境合拍。只有折腾到午夜以后,我才上床,关严蚊帐,用油灯去烧预先埋伏在蚊帐里的蚊子。当扑的一声,火焰触及蚊子翅膀,它们像中弹的敌机,纷纷坠落在我的面前。我由此而获得了几丝快感,然后吹灭灯,迅速像猪一样睡去。
幸好,我在这个小山村之外还有广泛的联系。
我的来信超过了生产队里乡亲们收信的总和。它们来自新疆喀什、上海金山、甘肃张掖等老百姓闻所未闻的地方,更多的是来自射洪的各个乡镇以及省内的成都、绵阳和安县等地方。寄信的都是要好的同学。同校的,也有不同校的。里面也有个别女同学,具有时代特征的苍白语言后面,似乎隐藏着天大的的内心秘密,欲启未启,让我想入非非。深夜的读信和回信,就成了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最主要的形式,调节着我的心态,校正着我的世界观,让我重新燃起希望。
冬天,我开始写诗了。
深夜,摊开一张白纸时才感到夜的宽广和强大。我把它关在门外,也可以听见它在奔跑,在推动和拍打门窗。但是,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时候,人们因熟睡而暂时弃权,把世界放在了一边。这时,我就有了空前的自由度。我凭着一盏孤灯,可以逆势而上,寻找任何一条路径,把铁板一块的夜幕掏出一个空洞,让我在里面像矿工一样,一点一点地掘进,像挖金子一样写出诗句。
不过,无数次的熬夜,无数次的投稿,虽然那些诗稿还开后门在公社加盖了公章,但是因为 “编辑同志”们缺少慧眼,直等到粉碎了四人帮,我才在《绵阳报》上发表了我的诗歌处女作,骄傲地得到了5元稿费。我的大作全文如下:
万里东风鼓征帆,雄文四卷作指南,
华主席为咱掌大舵,革命航船永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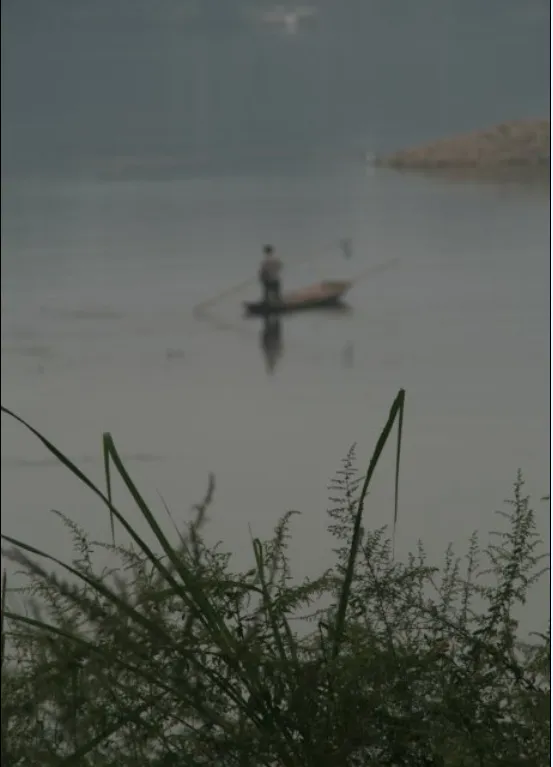
涪江夜幕下的打渔人
3.
希腊神话说,夜神是黑夜的主宰。他有一对孪生子:穿白衣的睡神和和穿黑衣的死神。他们干的事情都是让人睡去。只不过,睡神要让人在白天醒来,而死神是让人长眠不醒。
1990年冬天,一个深夜,全世界人民都在幸福地酣睡,我却被死神追赶着。这不是做梦,而是现实的死亡威胁。
那时,我已经由江津调回绵阳几年了。女儿已满三岁,生活安定。
上午,机关组织的体检,血压、心电图、B超、血常规,我一如既往的正常,正常得令人羡慕。问题出在下午的胸片上。照X光,科学的、现代的仪器冷冷地指出了我肺部有重大问题嫌疑。医生的笔迹潦草,但是意思不容置疑:发现两厘米大的球状阴影,必须对肺部再做检查。
球状阴影,不就是肿瘤吗?是肿瘤,癌症的嫌疑就大了。是癌症,就等于是被死神捉住了,在劫难逃。
出了医院,我以假装的镇静,密封了内心的翻江倒海。夜晚,我的世界一片漆黑。我听见我自己分裂成正反两方,就自己的生死问题进行激辩。
正方说,体检有疑点而复查是正常的,我的身体从来都是健康的,别疑神疑鬼……
反方说,现代化的仪器错不了,肺部球状的东西,不是肿瘤又是什么?癌,就是肿瘤嘛……
反复吵架,竟是反方渐渐占了上风。夜深人静,家人均已熟睡。恐怕连睡神自己都睡着了,我却孤立无援,被死神拽住,难以挣脱。这时,我忍不住站在生命的“终点”上,回望来路。我觉得自己刚刚三十出头,吃苦不少,享福不多,事业毫无建树。尤其是女儿才三岁,等待她的命运难道就如此悲惨吗?
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去医院挂号,想争取第一个复查。哪知医院所在片区停电,检验科不上班,我的煎熬进一步拉长。又一个夜晚来临之时,我只能一个人在静夜里呆望着天花板,继续思考自己的“后事”。
第三天,终于成功复查,一切正常。一种死而复生的幸福,从天而降,瞬间将我笼罩。走出医院,重负卸去,我的行走轻盈如飞。我在阳光下长长地吁出一口气,真想对我看见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活着真好啊真好啊。
免费享受了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死神的擦肩而过像是一道闪电,将我生命的许多角落倏然照亮。也许,我前往终极的道路,如同一位智者说的,将因此能在生的过程中更精彩地展开?
近几年,我在沉睡时,手机都醒着。这是领导的规定,以便他的指示随时抵达,不分昼夜。但是,大约我工作的部门不太要害,也许和平年代,领导也需要正常睡觉,总之从来没有领导在深更半夜电话召见。倒是多次有毫不相干的酒疯子,不但晴天霹雳般在午夜把我吵醒,还骂骂咧咧对我发“指示”。苦不堪言,于是好多时候又关了手机睡觉。
前年春天,那个晚上我恰恰又关了手机。半夜,房门突然被猛烈拍打,令人心惊肉跳。一看时间是凌晨三点,就越发觉得恐怖。开了灯,反复喝问,才弄明白是单位的驾驶员和一位小兄弟在门外,急不可耐。狐疑地开了门,他们只说是市委通知,开紧急会议。
这让我更加满头雾水。凌晨在市委开紧急会议,是世界大战爆发了吗?有恐怖分子即将在我市发动暴乱吗?即使是这样,也轮不到我开会啊。
车到市委,开会的迹象完全没有。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一位似曾相识的纪委干部过来,引我上楼。凌晨,纪委。各种联想迅速产生,又被我迅速否定。自信任何腐败案件都与我沾不上边,因此,我在电梯里底气十足地主动询问,才知道是我单位一位女士的丈夫刚才跳了楼,地点就在这栋楼里。要我参加,是要我负责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
进到一个小会议室,已经有三位市委领导坐阵,正在听公安局、检察院、纪委等部门的头头汇报。
案情很简单。根据警方侦查,死者属于自杀。
这个深夜跳楼的人,我熟悉,并且印象不错。他军人出身,身体健康,人很低调,事业顺利,在重要部门担任颇要害的职务。
他为什么要走上绝路?
他本来是在机关里加班。但是,工作的压力远不至于把他推向绝路。他杀?现场勘验和种种证据都排除了这种可能。深夜的跳楼,事先试图给家
属、朋友打电话,不通,还发了短信。虽然决绝离开,但也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他究竟是怎么想、怎么形成决定的,已经成谜。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当时一定觉得死去比活着轻松,才选择了深夜的一跳。
夜阑人静的时候,深陷黑暗,深陷孤独。个人被放大,内心被放大,焦虑、怀疑、畏惧、羞愧、愤怒、不安、脆弱,绝望,都被一一放大,铺天盖地,无法冲破无法挣脱,最终将他推下楼去。
也许,深夜,也常常充当着杀手。
4.
我的黑夜是生命中另外的一条平行线,是特殊的一部个人史。
生活在城市,周围的人何止万千。绵阳市区人口已经过了百万。但是,哪怕是在电梯里,一些人都将脸别在一边,装着在紧盯楼层数字的跳动,以掩饰人与人之间的尴尬。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彼此就隔了几米远的距离,甚至是邻居,彼此却是国境一般森严。世界之大,真正拥有的何其之小。只有深夜,人们暂且放弃了索取,缩回了自己的小窝。是璀璨的灯火,还是无边的夜色,只有醒着的人感知。想象无边,一切皆有可能。虽是暂时的拥有,那一瞬间,也是国王般的富翁。
今天,面对黑夜,我已经不再感到神秘和恐惧。因为,我确信深夜里并没有鬼魅。并且,每天阳光都会揭穿黑夜的老底,让我们对朗朗乾坤来一次验明正身。
已经送走了几位亲人,参加过无数次追悼会,尤其是5.12大地震,曾经从北川县城废墟的死人堆里趟过。经历了太多的死亡,死亡也就成了寻常的事情。夜深人静,追忆逝者,场面惨烈,恐怖,历历眼前,我也不会犯怵。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失眠。一次畅谈,一次畅饮,也可能无缘无故。
在床上使劲闭着眼睛,茫茫黑夜之中,那个叫“睡眠”的东西,像一段漂木,浮在意识的表面。努力把它朝深水里按,它总是顽强地不愿下沉。于是,只好放弃努力,索性让意识随波逐流,甚至天马行空。这时如果起身,踱步窗前,就会发现城市彻夜流光溢彩,夜车隆隆碾过坚实的大地,川流不息。卡拉OK、火锅、烧烤、麻将馆,都像昼伏夜出的动物,几乎通宵达旦。
生活和职场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人在向睡眠索取时间。因为有灯,向黑夜的索取也越来越容易,“主动失眠族”就像在进行填海造地的运动。
夜不再深沉,睡眠不再深沉。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深夜。
今天,又是深夜,又一次失眠。我突然怀念儿时,怀念乡村,怀念那种纯粹、简单、安静的黑夜。
真的,那样的黑夜多好啊,哪怕穷,哪怕有鬼的存在。
陈霁,四川射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当过教师、公务员和媒体人。作品见于《散文》《美文》《人民文学》《读者原创版》《文学报》《青年文学》等报刊。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品文选刊》等刊物选载。多次入选《中国散文年选》等年度选本和中国散文排行榜。有作品入选多种中学语文阅读教材。曾获四川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征文一等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