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回忆我的父亲阎武宏、母亲齐改珍
■阎文华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回忆我的父亲阎武宏、母亲齐改珍
■阎文华
2010年10月19日,是父亲阎武宏去世5周年纪念日,母亲也离开我们3年多了。虽然岁月流逝,但许多事情犹如昨天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事情刻骨铭心,总有些记忆挥之不去。
儿时记忆中的父亲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很忙碌,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是深入基层,就是召开会议。但只要有点时间,他就会给我们讲故事,讲做人的道理。
他常常告诫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理问题时对人要宽,对事要严;要切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要在背后随便议论人,也不要轻信别人的闲言碎语;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些话,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我的一生。
记得上初中后,我也和所有那个时期爱做梦的女孩一样,喜欢读长篇小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小说非常有限,所以,只要听到有新书出版,就缠着父亲到单位图书馆借阅,先睹为快。后来,爸爸对我说,长篇小说固然好看,但太浪费时间,你现在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习文化课上,偶尔可看一些短篇小说或杂文解解馋。
1973年冬,我从大同矿务局一中高中毕业,学校动员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因大同矿务局工种的特殊性,男同学都直接安排就业,所以上山下乡的对象主要是女同学。当时,父亲已恢复工作,任大同矿务局局长,有些局领导和个别处长正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孩子安排工作。因为我二哥1968年到右玉县插队后一直没有返城就业,母亲说什么也不愿让她唯一的女儿再去农村。这时,父亲就先做我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咱们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化,你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应该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我理解父亲的苦衷,就带领21名女同学到大同市南郊区马军营公社阳和坡村插队。临走时,我茫然地问父亲:“爸爸,我还能回来吗?”父亲默默不语。下乡后,我很快适应了当地农村的劳动、生活,各方面都表现突出,曾任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团支部副书记,并凭借自己的努力,被第一批推荐参加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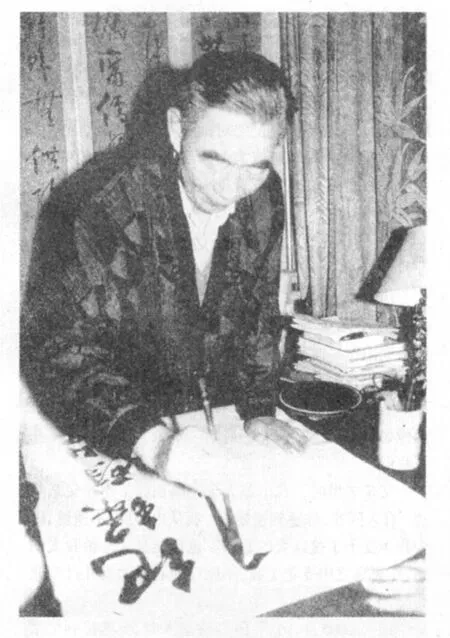
父亲的网球情结
自父亲患病卧床后,我工作之余的精力就放在照顾父母方面,所以很少再有时间去省老年网球馆打球。偶尔去一次,总感到那里的一切都非常亲切: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虽然我也五十出头,但大家总是亲切地直呼我的小名“华华”,那是父亲对我的昵称。每到这时,眼前总会浮现出当年父亲和李立功书记、王森浩省长等人一起打球的场景。
1979年至1988年,父亲曾任山西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非常关注离退休老同志的业余文化生活。1985年初,在父亲的倡导下,建起了我省第一个网球馆——山西省老年网球馆,当时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那时,国家网球队还经常来太原训练。退下来的老干部,各行各业的老同志、老专家和老教师都挥拍上阵学习打网球,网球馆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矫健身姿。你挥拍抽球、我上网拦击,一派生机,充满活力。正如网球教练钟明坤在诗中的感慨:
啊!网球,您就是乐趣,想起您,心中充满欢喜;
啊!网球,您就是生命,有了您,全身充满活力;
啊!网球,您就是纽带,通过您,人际充满友谊;
啊!网球,您就是享受,迷上您,生活充满魅力。
就在那时,我才知道父亲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担任定襄县委书记时,就学会了打网球。他近一米八的个子,跑跳自如,挥拍潇洒。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立功、森浩叔叔一起学会了打网球,并使我受益终身。
用200个勺子图像样本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再用30个勺子图像验证该神经网络的检测效果。其中,30个勺子图像分别为:10个勺子同时具有边缘缺陷和表面缺陷;10个勺子只具有边缘缺陷;10个勺子只具有表面缺陷。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我省于20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省网球协会,并由他担任主席。为了使山西省网球专业队提高水平、打出成绩、走出山西,父亲经常和省体育局领导、教练员一起开会,研究训练方案。那是省体育局女子专业网球队实力最强的时期,培养出了我省第一个网球健将、第一个国家网球队队员、第一个国家级网球教练员;同时,也是山西省群众性网球活动最鼎盛的阶段,参加人数多,比赛内容丰富。这里有父亲的心血,他总是千方百计给省网协筹措资金,解决各类难题。父亲的一生,始终是大智若愚、举重若轻,这是大家公认和钦佩之处。尽管筹到那么多经费,但他从未动用过,也从不干涉省网协的日常工作。经常是遇到困难时,大家就找他谈,我在家中就见到过数次。所以,至今我一踏入老年网球馆,见到网球界的前辈或同辈,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华华,你爸爸是个有功之人,没有他,就没有山西网球事业的今天。”
1999年3月12日,父亲突发大面积脑血栓,以至后来瘫痪在床近7年时间,永远离开了他热衷的网球事业,离开了他热爱的老年网球馆。在此期间,省网协、网球界的老同事、老球友去看他时,他还关心着山西网球事业的发展。
2007年底,山西省网球协会换届时,我当选为副主席。我知道,那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省体育局对父亲多年来为山西体育事业、为山西网球事业作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在网球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要对父亲说:爸爸,您安息吧,网球界的叔叔、阿姨以及我的同龄球友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对山西网球事业的贡献。目前,山西老年网球馆已成为山西群众体育活动的中心,为大家的健身、交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父爱无边
1999年3月12日19时,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夜晚,父亲正在客厅看新闻联播时,突发大面积脑血栓被送到山医一院抢救。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怀下,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父亲虽然挽回了生命,但却未能恢复健康。2005年10月19日凌晨6时,父亲就像燃烧的蜡烛,熬干了最后一滴心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时,我出差去了湖南长沙,不在父亲身边。有人问我,你感到遗憾吗?我从内心说,不遗憾,因为我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也可能是父亲怕我太伤感,在冥冥之中支走了我,不愿让他心爱的女儿过度悲伤吧!
记得2005年10月19日凌晨5时,突然接到父亲的陪护人员韩小平的电话,他带着哭声说:“爷爷已经不行了,你快回来吧!”我听后失声恸哭,泪如雨下。
早已预感到父亲的病情不可挽回,只是个时间问题。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想像着若父亲离去时我将如何面对;无数次在睡梦中惊醒,怕听到电话铃响(那一段时间夜晚不敢关手机)。但父亲最终在我毫无思想准备、不在他老人家身边时,离我而去。接到电话后,我从长沙辗转到咸阳机场时,已是深夜12点。连夜坐汽车赶回太原,一路上夜深人静,朋友们都进入了梦乡,而我却在默默流泪,心在慢慢滴血。想着慈祥的父亲,不知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奔丧,这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情节,让我亲身经历,那种痛由心生的感觉,是撕心裂肺的,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
父亲生前为人低调,对自己的过去不曾留下只言片语。他曾说,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老领导、老同事,感到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大事。原以为父亲离休12年,又卧病近7年,早已被人们淡忘,但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原省委书记张宝顺来了,与他共同生活战斗过的老同志、老部下都来了,他曾帮助过的、我们不曾相识的人来了,近4000人向他依依惜别。一些人在灵堂前长跪不起……
啊!父亲,您从不为自己的子女争一官半职,却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据说,在您遗体告别的那一天,太原市的鲜菊花都卖光了,那么多的人群、那么多的花圈、那么多的挽联、那么多的哀思……
“文化大革命”中的母亲
“文化大革命”那段经历,是我最不愿触动的神经、最不愿谈起的话题。那时,我刚刚10岁。它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太多的伤害,真是不堪回首,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1965年9月,父亲被派到大同矿务局任“四清”工作团团长,随后,担任局党委书记。1966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夜之间父亲变成了大同矿务局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批斗成了家常便饭。先是住牛棚、劳动改造,后又被投进监狱,停发一半工资,住房也被侵占一半,大哥被发配到晋东南三线工作(因他没随父母去大同,留在太原上中学),二哥插队到右玉县,一直把我们兄妹7个带大的70多岁的姥姥,因亲眼看到我父亲被挂着牌子游斗而一病不起,于1968年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关于父亲被批斗的情况全家人始终瞒着姥姥)。那时,家里就剩妈妈、三哥、我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5岁。我们每天担惊受怕,不知爸爸被关在何处,挨饿了没有,挨打了没有,造反派何时又要抄家……家里缺衣少食,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走在大街上,大多数熟人都躲得远远的,生怕受连累,更有甚者还喊着口号,骂我们是狗崽子,真是世态炎凉啊!这就是当时我们家的处境。长大工作后,许多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说,你有那么优越的条件,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怎么一点也不娇气、一点也不盛气凌人,而是那么善解人意、愿意帮助别人呢?我想,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段惨痛的经历使我成熟得更早,对人生的意义理解得更深一些吧。
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母亲表现出了少有的坚强。她带领我们房前屋后种地,挨家挨户借粮本,买每个粮本上仅供的2斤高价粗粮艰难度日,想尽办法打听父亲的下落。当造反派多次威胁母亲要与父亲划清界限时,均遭到母亲的严词拒绝。母亲说:“我从15岁参加革命,始终和他爸爸在一起工作,我怎么能不了解他呢?他爸爸13岁参加革命,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坚信党组织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母亲是乐观的,在父亲被没完没了地批斗、根本就看不到一丝曙光的时候,母亲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半点的幽怨,从来也没掉过一滴眼泪。她时刻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并托人捎话给父亲:“要相信党,相信人民,千万不要想不开。”当时,好多“走资派”的家属感觉到前途渺茫,吓得谨小慎微,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有被迫划清界限的,也有主动揭发问题的。在那个年代,母亲所表现出的坚强和勇敢是少有的,她也是为数不多的敢和造反派顶撞、敢据理力争的“走资派”家属。她常说:“我1940年参加革命,既没叛党又没变节,我怕什么,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能给我扣什么帽子!”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孩子多,工作又繁忙,母亲30多岁就患上了高血压病。“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到大同矿务局胶鞋厂糊胶壳帽(工人下井时用的安全帽)。中午带饭,晚上很晚才能回家。经过一天的劳累,身心非常疲惫,但回家后既要生火给我们做晚饭,又要给我们准备第二天的饭菜。那个年代,哪有今天这么方便?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最基本的主食,什么都得自己亲手来做。晚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还得缝补衣袜。这些情景,让我终生难忘。好多年以后,和母亲在一起劳动的阿姨们告诉我,母亲当时中午带的饭是最差的。就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况好转后,母亲还总是把细粮留给父亲,自己从来不舍得吃一口。至今,还有好多人记得,母亲抽了一辈子的烟,从来舍不得抽好烟。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抽的是从老家捎来的“小兰花”。90年代,一直抽的是价格最便宜的黑玉蝶牌香烟。孩子们经常给她买一些好点的烟,再三说明劣质烟对肺功能的损害,她却说:“我的烟瘾大,不爱抽其他,这种烟利痰。”但我们知道,她是舍不得抽好烟。她就是这样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伟大母亲。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生活与政治的双重压力,给母亲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以至她在晚年患有多种疾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心脏与肺功能也不太好。所以多年来,母亲一直在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

刚强的母亲 脆弱的生命
1924年10月31日,母亲出生于定襄县龙门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面有两个哥哥。1940年3月,年仅15岁的母亲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曾担任过县妇联主任、县法院副院长(主持工作)。1954年,随父亲转入工业战线,曾任轩岗矿务局土建队书记、阳泉矿务局女工部部长(正处级)、省煤矿科研所专职书记。1965年,调到大同矿务局,“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劳动。1975年10月,调省电管局保卫处工作。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
母亲的独立性很强。生前,父亲一直工作繁忙,家务事都由母亲操心。尽管孩子多、负担重,但她从未放弃过工作,也从来没有因父亲的地位而怠慢过因工作或个人事情来家的客人。她待人热情、好客,从不干涉父亲的工作,也从来没有给父亲带来过任何工作上的麻烦,向来在物质上没有更高的要求,经营着家里俭朴的生活,让父亲能够放心地在外工作。父亲常跟我们说:“你妈妈就这点好,不贪利,能吃苦。”
这就是我的母亲,善良、朴实、勤劳、勇敢、坚强。
父亲病倒后,母亲也已75岁高龄。她时刻牵挂着父亲的冷暖,总是想着给父亲做点好吃的,常常到医院陪护。父亲去世时,大家都在商量是否告诉母亲,担心她已近81岁的高龄且身体多年有病,能否承受住这巨大的悲痛。但当母亲得知后,却非常镇静,坚持要见父亲最后一面,她在父亲的遗体前默然许久,深情地凝视着父亲的遗容,凝视着和她一起从战火中走来、一起参加新中国建设、一起经历“文化大革命”、一起为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呕心沥血的革命伴侣……
2007年4月10日深夜,母亲突感不适,右腿发软站不起来,CT显示脑躯干部位有血栓。治疗过程中,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仅仅20天时间,迅速发展为各个主要脏器衰竭,多种综合病症爆发。在母亲自己与儿女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中度昏迷,生命垂危。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终未挽回她的生命,让人难以接受,心痛不已。我脑海中常常定格在母亲中度昏迷时紧紧拉住我的手始终不放的情景。那一幕,是她老人家对生命的渴望,也让我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人在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刻,有时是那么无奈、那么脆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没能留下只言片语,带给活着的人只是无穷的悲痛、无尽的思念和终生的遗憾。唉,刚强的母亲,脆弱的生命!
这篇简短的回忆、零散的记忆,是我一直流着泪断断续续写完的。父母相继去世后,我总觉得应该写些什么,但又不忍提笔。现在,总算了却了这桩心愿,对自己心里也是个安慰。我非常热爱爸爸妈妈,他们的离去给我带来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这种痛是无法用语言作出完整表述的。他们生前的高尚品格和感人事迹,无疑会成为后代人生活和工作的无穷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