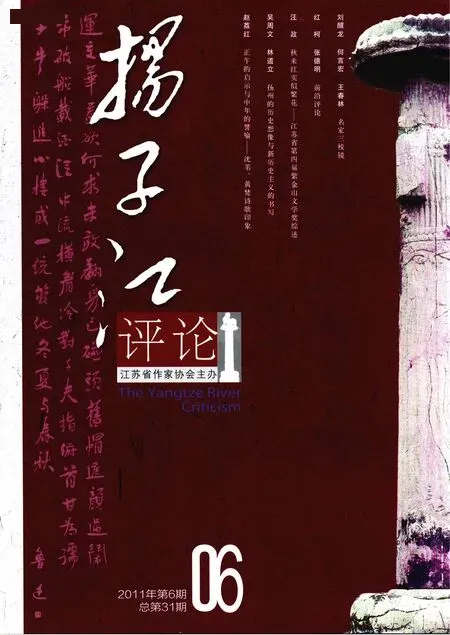扬州的历史想像与新历史主义的书写——关于蒋亚林长篇小说《大盐商》的评论
吴周文 林道立
文学中扬州的被想像、被书写,在近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只见李涵秋的《广陵潮》等极少数作品,比之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天津等等大城市来,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差不多被文学所冷落和遗忘。然而,近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苏扬州籍作家蒋亚林所著的长篇小说《大盐商》,却给我们读者带来了期许已久的惊喜。《大盐商》值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去关注与评论,因为它写了扬州的历史想像,更因为它选取与把握了扬州盐商这个特殊题材。诚然,《中国盐业史》、《两淮盐法志》、《两淮盐商》、《扬州画舫录》等等文史、笔记书籍中对历史上的扬州盐商有过很多记载与描述,但作为纯文学对扬州盐商的想像与书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蒋亚林还是始作俑者,《大盐商》则是第一部文学意义上的原创之作。
扬州,是一座被明清时期盐商改变历史、并且被他们创造历史的城市。换句话说,没有扬州盐商,就没有历史上的扬州;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扬州十日”屠城之后,这座古城已基本毁灭。后来的再度复兴与繁荣,与盐商在扬州的开发与发展盐业经济有着极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说,没有清代盐商在这里的“殖民”,就没有扬州再度的复兴与繁荣。近代人陈去病的《五石脂》中有这么一句话:“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①蒋亚林在这部小说中对扬州的历史想像,就是建立在对这样一个基本历史事实的尊重之上,即对徽商“殖民”与扬州复兴两者之间因果链价值的一个文学的认定。对此,作者明白而又坦率地说:“在扬州,由盐浸润发育的不仅仅是一条街,还有一家家书院,一座座寺庙,一片片园林……可以说,清代盐商如同太阳,其炽热灿烂的光辉辐射了整个扬州城,使得这里一切的一切,大至城池市井、商业文化,小至一楼一桥、一草一木,无不折射着它的光焰与色泽,从而发出幸福的歌吟。”②从这段描述可见,作为“扬州人”的作者写“扬州”的自豪与激动。他正是怀着草根性、幸福感和责任心,在自己的历史想像中为养育他的这座名城,进行了很有审美趣味的“树碑立传”。而揣摩与评论作者的历史想像与书写的一些个性特点,我们认为对于讨论当下历史小说与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无疑会提供有价值的话题和很有益的启悟。
一
王德威在《想像中国的方法》中说过,小说之类的叙事文体,“往往是我们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③小说之于历史的客体,之于一个城市或一个乡村或一个地区的历史“文本”,基本上有两种叙事立场与方法。第一,作者站在传统的主流话语立场,在尊重历史元背景元环境元人物或者尊重元历史生活题材的前提下,用政治话语的善与恶、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简单二元对立,来进行历史性的阐释。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如“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小说《红岩》、《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三家巷》等等。第二,作者站在民间立场,用非政治功利的话语,即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人性的等等多元视角进行历史生活题材的审美。如凌力的《少年天子》、《星星草》,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帝王系列”,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等;以及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先锋小说中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苏童的《武则天》、乔良的《灵旗》、叶兆言的《状元镜》、格非的《青黄》、余华的《活着》等等。两者在“历史真实”的把握方面,前者尊重历史的元背景元环境甚至元人物以及一些元事件的真实元素,进行有限制的想像与虚构;后者则在大体、模糊的尊重元背景元环境和元事件的基础上,或者只取历史生活的题材,进行着几乎无限制的想像与虚构。而在这两者之间,蒋亚林写作的立场与姿态,毫无疑问是属于后者,而且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某些主要特征。
历史永远不能复原,永远是“现在”的历史而不是“过去”的历史;历史叙述的作用表现为对历史自身的唤醒或重新获得认知,并为历史的未来进行“预期想像”。所以,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文化诗学”理念认为,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惟其如此,蒋亚林心中历史的扬州,就是他对扬州想像与虚构的历史。作品所展示和描述的,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的四五年间的扬州历史。然而,作者却将满清入关之后的扬州历史,进行着“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的美好想像,历史仅仅成为作者想像与书写的参照物;尤其是对扬州美好的名城文化进行展示与描述。如作者自己所说:“史料于我,只是为了形成飞翔的翅膀,而不是让它食而不化地堆积在心中,限制甚至阻碍艺术翅膀的高飞。为此,我甚至将不同时态的人物、不同空间的事件拉扯到一起,令它们开花结果。有时还改变一些历史上的称谓,比如扬州瘦西湖在乾隆时叫保障湖,五亭桥叫莲花桥,小说中却一律采用今人的叫法。此外还把当时还没有后来才相继出现的个园、富春、共和春、烟花醉等园林饭店与酒的名称聚入小说,目的是为了让一个外乡人进入我的家乡扬州后,更便捷地认识她,记住她,并在胸中生出爱意。”④于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蒋亚林的笔下,一锅端地展示属于扬州的艺术文化和消费休闲文化,描述着饮食、园林、书画、服饰、沐浴、美女等等方面的景观,几乎把扬州的各种地方文化囊括其中。这种整合性的描述,是作者在历史真实材料基础上的夸张拼贴,其方法的夸张甚至让“扬州八怪”和袁枚、吴敬梓、纪晓岚等等历史人物,共时共空地出现在小说的情节中间;这种不合历史细节真实的拼贴和怪诞出奇的想像,则是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很少见的一种写作策略。解释的唯一理由,是出于新历史主义小说手法的花样翻新,再现扬州历史上文化的辉煌的使命,使作者具有了想像的激情与命定的“我行我素”的才能与勇气。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大盐商》对扬州的历史想像,又是通过家族小说的形态来讲述的。即通过康氏家族的视角,来表现扬州盐商的崛起、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与《红楼梦》、《家》、《财主底儿女们》一样,作品气势恢宏地塑造了康世泰及其妻妾、三房儿子与妻妾和两个女儿等众多家族成员的艺术形象,并且描述着他们各自殊异的泪与笑、歌与哭的命运,这些成为作者进行扬州想像的思想载体。新历史主义小说极端重视欲望描写,其人物被各种欲望所驱使而形成各自思想性格发展的自身逻辑。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蒋亚林把握了“盐”这个特殊的文化符号,进行了想像与虚构。小说让所有的人物与“盐”发生关系,让“盐”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人物的命运发生关系,于是“盐”成为小说欲望叙事中特有寓意的一个象征物——每个人在故事情节中赖以生存的象征物。盐,与油米柴等等一样,是人生活最基本的物质,是人生存的必需。《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说过:“盐是任何民族都最早发明服用的。在民族学史的记载上,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不知道吃盐,但这个民族已经灭亡了。可见不吃盐的民族是会灭亡的。”⑤蒋亚林在《大盐商》中对“盐”的文化符号的寓意,让我们联想起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刘恒《狗日的粮食》、苏童的《米》等作品。苏童的欲望叙事,自始至终把“米”与其主要人物五龙的短暂一生纠结在一起的,从他因饥饿当米店老板的女婿到在返乡的火车上结束生命,对“米”的欲望成为他的生存之根。同样在康氏家族的每个成员身上,作者演绎着“盐”是他们的生存之“源”之“根”,因“盐”而生成了他们形形色色的欲望。对此,作者进行了多维度的想像和书写:或者,“盐”是竞争的欲望符号。康世泰因“盐”在扬州发迹,其盐业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为两淮盐商中的商总,在他“盐”永远是巧取豪夺、称王称霸的欲望之巅;守诚欲继承父业及家族荣耀,谨小慎微地在商场打拼,怀抱的是守住家业、代代传承的欲望。或者,“盐”是淫乐的欲望符号。守信用“盐”赚来的钱泡妞纳妾,花天酒地,甚至在小金山抛洒金箔以示豪富,在他“盐”就是享乐无度、无德无行的欲望。或者,“盐”是追求儒雅的欲望符号。守慧凭着家里的豪富追求儒商的风雅,与社会上诗书画的文人交友结社,并厮守着贾宝玉林黛玉式的真情至爱,“盐”成为他洁身自好的欲望。作为原配夫人的安静瓶一心向佛,只愿守在安徽老家过清静的日子;二女儿芝芝毫不贪图扬州的豪华生活,不愿与扬州地方官僚联姻,而回老家乡村去追求自己青梅竹马的爱情。母女均不屑于因“盐”暴富的扬州之“家”,而以宁静淡泊为其心性之欲求。凡此种种,康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连同作品里写到的其他人物如盐政官员、地方政要和大小盐商等等,他们的生存、竞争、倾轧、发迹和败落,他们情欲的发泄、婚恋的痛苦、商场竞争背后的焦虑、纸醉金迷背后的人性扭曲,无一不与“盐”纠结在一起;“盐”,成了小说中人物生存的全部背景、原欲内涵和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盐”成了小说所有人物的生存之谜与人性之谜。“盐”让他们痛痛快快地生,“盐”也让他们凄凄惨惨地死。“盐”是作者想像的命脉和虚构的泉眼。
不难看出,蒋亚林与先锋作家们一道弃绝了历史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之后,站在民间立场进行了历史想像中的“家族”历史书写。当从生存与欲望的层面对扬州进行历史想像的时候,他不再像传统的文史、笔记著作那样,把盐商历史书写成令人肃然起敬的“神话”,而是冷静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寓言”的叙述者。这充分显示了作者历史想像与书写的个性。
二
引发《大盐商》历史想像最初的根本,毫无疑问是历史上乾隆时期在扬州的大盐商江春。康世泰的人物原型就是这个“两淮八大总商”之首的江春。籍贯安徽,乾隆临幸江氏宅苑,御赐“孔雀翎”封号,家养戏班进京为皇太后祝寿,以及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大案等等,蒋亚林把这些属于江春的个体印记都移植到康世泰身上;然而有关原型的这些细节,毕竟只是描写康世泰的依稀朦胧的想像而已。关于江春发迹腾达的故事,如果想像处理为“官史文本”,则可以写成正剧,也可以写成喜剧,当然也可以写成悲剧。新历史主义小说恰恰正是消解、颠覆和重写“官史文本”,把历史书写为“野史”、“稗史”、“民间史”甚至“寓言”,并且以此进行反历史、反英雄,甚至进行反文化、反哲学的另类思辨,这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最主要的价值取向。虽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新历史主义,评论家把它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然而,作为一种先锋文学创作的理念,仍然延续并活跃于当下的小说创作甚至“后现代”的创作,自然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蒋亚林正是在这一理念上,展开了他的历史主义的想像与书写。
作者说:“扬州盐商——这个曾经令大清帝国仰视了四百年的商业寡头,他们凭借怎样的秘诀积聚出无比庞大的商业资本?他们的骄奢淫逸达到了怎样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们庞大的商业资本,为什么不能像大英帝国那样催生出蒸汽机与产业革命的赤子,只是一味地奢侈、糜烂、腐化、逸乐,并对后世产生若干负面影响?鼎盛时期的他们,烈火烹油,炙手可热,一旦轰然倒塌,何以家抄籍没,父囚子亡?天意乎?人祸乎?在他们身上隐匿着怎样人性的秘密?最终的悲剧对今人又有着怎样的警醒和启迪?”⑥正是从这种历史的叩问和寻找出发,蒋亚林成了一位残酷的言说者。他根本无意把江春写成“英雄传奇”,而是消解了原本属于江春大盐商身上的“英雄情结”,剥离了那留在历史上作为一代盐商枭雄的英雄气概,也无视富甲一方、慷慨仗义的作为道德家“阳光”的一面,而把康世泰处理成一位与历史上的江春相悖的失败了的“英雄”。小说把康氏家族“富二代”,作为主人公康老爷的补充形象来写,以找寻、演绎其“失败”的原因。长子康守诚经营理念的保守和循规蹈矩,缺失的是除旧改革、锐意进取的思想与作风。三子康守慧只求虚空的潇洒儒雅,把盐号交给二掌柜打理,半生无所建树,最后落得吸食鸦片身亡。而次子康守信“走私”的旁门左道,极度的张狂骄横与沉湎酒色,甚至用八个美女作自己的“轿夫”,可谓腐败到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程度。——三个儿子都不能继承父业。于是在作者的笔下,康氏父子无“壮举”可叹,无“理想”可言,无“希望”可说;总之,无“英雄”可以书写。他们的本质只能是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殖民者”群体,其本质决定了最后难逃穷途末路、一朝倾覆的命运。小说情节中特别强调康氏家族包括整个扬州盐商,是靠封建国家的“盐引”——类似于计划经济的证券,来从事盐业商业经营的。这个宿命的经营机制,决定了盐商沉浮的命运掌握在高度集权的皇帝手里而成为恭敬听命的“御用官商”;所以最后乾隆皇帝的一道“圣旨”,就封杀、结束了康氏家族的荣华富贵。同时,作品以大量篇幅描写康氏家族群体的豪华糜烂的生活,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小姐、管家等等,衣食住行都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都处于超级消费、极端享受、疯狂淫乐的状态,以此强调大盐商们消费性本质的腐败性。以上两方面的强调,是作者消解与颠覆盐商历史的一种追问与一种悲叹。其追问与悲叹的,是扬州盐商只能创造扬州市政、市井一种属于文化表面的繁华,却根本不能成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更不能改善生产关系;于是,这个“商业寡头”除了给封建王朝提供纳税的资本而外,命定不能成为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爆发工业革命的历史先驱。正当扬州盐商耗费大量白银在瘦西湖上建造豪华的五亭桥之时,西方的瓦特正在改良蒸汽机,并由此引发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产业革命。这个具有反讽意义的历史比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蒋亚林的历史叩问。
蒋亚林作为一个残酷的言说者,还表现在把《大盐商》想像与书写成一个“准”悲剧。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⑦,法国的罗伯·葛利叶论述悲剧的崇高时说过:“哪儿有距离,分离、二重性、分裂,哪儿就可能把它们作为痛苦来体验,随后还会把这种痛苦抬到一种崇高的必然性的高度。”⑧康氏家族的毁灭是生活中的悲剧,但小说没有把它写成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因为,作者所展示给读者看的康氏父子,差不多是负价值与负价值的毁灭。读这部长篇,让读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是:一方面,作者很自豪地展示、描述了扬州历史上由盐商带来的传统文化的“辉煌”,如他所说,是“如同太阳”般的福祉于历史的扬州;另一方面,作者又很刻意地把作为大盐商巨头的康世泰写成了失败了的“反英雄”,让我们觉得蒋亚林是蓄意制造了一个自身的悖论。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在想像与书写中间,作者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消解了,关注历史是表面的,进行历史戏说也是表面的,真正想留给读者的,是新历史主义常常所书写的那种“无历史”的“历史”,是作者心中的臆造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悖论背后的思考——即如前所述作者的追问与悲叹。正是因为如此,小说虽然写了守信、守慧等人的死亡,虽然写了大女儿的骗婚,虽然写了康世泰的囚禁与落荒而逃,虽然写了蓝姨削发为尼……但这些对于读者来说,都不能产生崇高感和疼痛感。因为作者怀着那份太多的沉重在追问和悲叹历史,于是审美理性把作者叙述“如同太阳”的那份崇高感和疼痛感消解殆尽。悲剧审美总是产生崇高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作为崇高的研究对象,“在一些事物身上,它既体现了大自然的崇高,又体现了人的崇高:这样的结合就叫它做悲剧性”⑨。也就是说,真正的悲剧才会产生真正的悲剧性。对照蒋亚林的文本来看,《大盐商》虽然写了悲剧题材与悲剧内容,但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反英雄思维的消解、颠覆,让这部小说的归属似是而非,最后只能定格在“准”悲剧的审美价值之上。——这里,蒋亚林的历史想像与书写,与传统的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小说划清了界限,并以自身的悖论思维,显示了与既往新历史主义小说同中有异的个性特点。
三
笔者认为,《大盐商》进行隐性的悖论构思,是整部小说思想最为深刻的预想。同时,这部小说的悖论吁请最相适宜的艺术形式,达到诗意表现的、最为华丽的高度。——作者的悖论,顺理成章地创造了小说的“隐喻”修辞,这正是笔者对蒋亚林写作策略的一个发现。
美国社会学家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对中国的近现代史进行研究,说上海“一直是中国的缩影”,并说它“提供了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的锁钥”。⑩如果说上海可以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缩影”,那么,隋唐时期已成为繁华名城的扬州,就可以作为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写照。而蒋亚林在《大盐商》中的历史想像,更是把她作为大清王朝的一种国家意义上的想像。写到扬州盐商的纳税怎样成为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写到乾隆亲临巡察时怎样权重于扬州,写到以康世泰为首的盐商们怎么百般虔诚地恭迎和陪驾,写到乾隆皇帝怎样恩赐康世泰“孔雀翎”封号,康世泰怎样在扬州盐政界呼风唤雨、极一时之盛,以及最后写到康守信“走私”案被告发,使康家在顷刻之间轰然倾圮,这些描写中间无不隐喻着作者对国家兴亡的想像意味。——蒋亚林出奇地、很自我地运用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所常用的“隐喻”修辞。
美国著名的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隐喻,它把所报道的事件同我们在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中已经很熟悉的模式串联起来。”⑪在怀特看来,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除了消解性和颠覆性而外,在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中间还有着特别明显、强烈的批判性特征。正因为如此,蒋亚林想像与书写的“隐喻”修辞,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其理论的根据。
在文本表现方面,作者用“隐喻”进行文化批判,则是很有心计地安设了两个方面的书写策略。首先,用“高潮即谢幕”的构思,寓意着宿命的象征。作者采取了截取历史横断面的写法,有意遮蔽掉康氏家族从发迹到强大的数十年历史。即实际只描写康世泰接受御赐“孔雀翎”封号的、前前后后的三四年,也就是仅仅截取“鼎盛即倾圮”的一小段历史,并且就这一“横断”的历史予以渲染、放大了的书写。而这“横断面”的强调,归趋的唯一旨意则是相反相成的审美抑扬——明写“高潮”而实写“谢幕”,明写“鼎盛”,实写最后疯狂的“倾圮”。作者没有像一般悲剧用“误会法”来设计偶然性因素导致必然性命运的结局,诸如罗密欧误因为朱丽叶真死而误杀自己、贾宝玉不识“掉包计”而误娶薛宝钗等等。因为《大盐商》的“准”悲剧,没有处理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而是把人物处理为对自己命运与前途的无可问知。作者用“隐喻”作了“天意”的安排——因“盐引案”的祸端,导致皇帝绝杀的圣旨。这个“天意”,其实是蒋亚林审美创造中理性的预想,故意用突发式的、急转直落的结局,让自己对扬州盐商历史的追问与悲叹,在文本上找到切中肯綮的表现形式,正如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说的,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⑫,为内容所吁请,形式便灌注了悲剧审美情感而不仅仅是形式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桑塔亚那的“美是对象化了的快感”等命题一样,在20世纪初的西方美学界成为经典名言。)从创新的角度看,这一书写策略在结构形式上,则是有意打破与刷新传统家族小说以纵向展开的历时性的叙述模式。这种打破与刷新,只能解释是为了彻底颠覆康氏家族的历史,并为一个“野史”或“稗史”或“寓言”文本的创建而使用一个艺术奇招,从而让读者去品味这一奇招的形式意味,即“寓言”写作的诉求——仅仅是“准”悲剧的“倾圮”,而绝非悲剧性的“倾圮”。
使用“隐喻”的第二个书写策略,是用书中康世泰二女儿芝芝的“噩梦”,对家族命运进行象征性的暗谶。小说塑造了在整个康氏家族中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芝芝,她与家庭的道德伦理、人生观念、生活方式完全相悖,是家族的一个精神叛逆者。作者以这个人物从其老家先后三次来扬州作为全书的叙述脉线,而且全书以这一人物的叛逆性寄托着扬州想像与书写的光明和希望。这些让她成为小说故事的参与者,准确地说,她更是康氏家族命运的“见证者”。作者以她来担当“隐喻”——暗谶的角色,是绝无仅有的选择。从她第一次来扬州、回到老家之后做“噩梦”的细节,可以分析、欣赏作者在形式上经营“隐喻”修辞的精妙。这个细节出现在第二十三章,此章以《谶》命名,其实仅看小标题,就可以明白作者所传达的信息。作者一直没有具体描写“噩梦”的内容,但围绕着这个“噩梦”,进行了有层次的、欲扬先抑的书写。首先,写在做梦之后的芝芝显得异乎寻常的焦虑,谁问也不肯透露。其次,写“噩梦”使她忧心忡忡,于是她执意要赶往扬州的家探个究竟,这个决定说明,此梦与父兄的命运息息相关。第三,写她到扬州之后,再三向家人打听家里“发生了什么”,见到兄嫂也还是不肯透露“噩梦”的内容;在三嫂修竹雨再三逼问下,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在家做了不止一次梦,有预感”,“不是好梦”。第四,写芝芝回到老家以后,康氏家族因“盐引案”事发而厄运即至,问罪、囚禁、罚款,落得家破人亡、狼狈不堪的结局。小说的最后,以芝芝第三次来扬州眼睛和心灵的伤感,描述康家老宅易主后物是人非的凄凉情景,以交代“噩梦”终于成“谶”。可见,如此先抑后扬、曲致有序的书写,渲染了宿命、魔咒和神秘主义的气氛,便把“梦谶”与“隐喻”和谐地整合起来,为康氏家族的书写创造了沉郁顿挫、“梦谶”成真的抒情氛围。
总之,当把康氏家族这个历史文本放在“国家”意义上想像和书写的时候,蒋亚林便把自己的小说变成了“隐喻”文本。如怀特所说,“历史叙事……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⑬。故此,“隐喻”背后的审美意趣使作者对扬州盐商历史的追问和悲叹,倍生沧桑感和现代性。作者以先锋文学的姿态把《大盐商》处理成“准”悲剧的时候,外延的批判意义,也是隐喻的暗谶,正是指向了故事发生的乾隆盛世王朝及其保守、腐败、专制和拒绝改革开放的国家机器。笔者认为,作者在历史批判中对于负价值的审美给读者以“隐喻”的想像和思考,同样也让读者沉入历史的终极叩问而感到沉重起来。毫无疑问,这正是小说在思想上最令我们思考与玩味的出彩之处。

2011年12月1日初稿
12月5日二稿
12月11日定稿
【注释】
①⑤参见韦明铧《两淮盐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第8页。
②④⑥蒋亚林:《〈大盐商〉跋》,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第385-386页、第385页。
③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⑦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⑧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⑨《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美学》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⑩[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⑪⑬[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第171页。
⑫参见[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 扬子江评论的其它文章
- 作品的命——长篇《好人难做》创作谈
- 语言的功能与诗歌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