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杰: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本刊记者 张天奇
张同杰: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本刊记者 张天奇
他先后独立获得中国科学院亿利达奖、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优秀乙等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北京青年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北京师范大学第七届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此外,他参与的教学成果《观测宇宙学》荣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参与出版的科普类电子出版物《探索宇宙》,由于其所涵盖的天文知识内容丰富详实、界面设计现代动感、交互链接快捷方便等特点,荣获第三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提名奖。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国家光学天文台
自古以来,宇宙就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宇宙学说。如中国的浑天说、盖天说和宣夜说;西方统治中世纪欧洲1500多年的托勒密的地心说、16世纪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牛顿力学创立以后,随之建立了经典力学。到了20世纪,在大量天文观测资料和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现代宇宙学。
宇宙的“大”和人类的“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生的长度和宇宙的年龄相比更是相形见绌。可是,人们生活在宇宙中,宇宙也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去漫步太空,遨游宇宙。
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教研室主任张同杰无疑是探索先锋中的一员。与航天工作者不同的是,张教授所研究的领域是天体物理学中的宇宙学,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不断地求索和追随辽阔而深邃的宇宙。
记者:宇宙在我们普通人眼里仅仅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在科学家眼里则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您正是一位研究宇宙学的科学家,能谈谈两者的区别吗?
张同杰:两者区别很大。普通人眼里宇宙的概念,一般是通过观看科幻电影或者阅读科普读物、哲学所形成的。事实上,科幻电影和科普读物也是根据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哲学也是直接来源于自然科学。由于宇宙非常大,普通人眼里的宇宙只是直观上能够感受到的,银河系或者其他的星系等等,所以他们会把注意力停留在一些有趣的事情上,比如外星人和UFO等。关于外星人和UFO,新闻媒体已经炒了很多年了,但是由于这些事件没有太多可信的证据,所以现在正规的科学刊物上和权威杂志上都没有过正式的报道,报道的都是一些非官方权威的杂志。
科学家眼中宇宙的概念,是以宇宙整体为出发点的。在时间上,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7亿年;在空间上,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天文学家通过光学望远镜、射电望远镜或者其他更为先进的望远镜可能把整个宇宙都观测到。研究宇宙学,目的是想了解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过程等等,也包括地球在宇宙学背景下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去研究,从物理的角度和化学的角度,而不是停留在一些有趣的事件上。毕竟科学幻想与真正的科学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科学性不是那么强。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写一些科普作品,因为宣传宇宙知识也是必要的。
记者:您是怎样走进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的?在求学道路上,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最深?
张同杰:我小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数学家。学生时代老师们常对我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也常常给我们讲数学家陈景润、华罗庚的故事,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后来我考大学时填报的志愿也是数学系。但是有很多科研工作者后来都没有实现当初的理想,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学我被录取到了山东德州师专(现德州学院)物理系,虽然物理学也离不开数学,我当时还是想过转去数学系学习。但是接触了更多物理学知识之后,发现我对物理学更感兴趣,特别是把物理学的基础掌握得更扎实了之后,反而觉得数学缺乏比较实际的东西,相对来说较为枯燥。当时德州师专很多老师如王宝泉,王兴孔,姜万录,曹志明,陈式诚和贺金玉等老师对我在物理学和数学上影响很大,这些老师的教诲更加奠定了我学习物理学的决心。其中贺金玉老师(现任德州学院院长)在电动力学方面的指导,以及在人生目标的规划方面的点拨和鼓励,使我终生受益,没有他的指点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取得现在的成绩。在山东省教育学院数学物理系(现齐鲁师范学院物理系)读本科时,郭守元老师讲授的课程是关于数学物理方法的相关内容,在课堂上,他经常会讲一些宇宙大爆炸的知识,这对我影响也很大,加上我在课余时间也经常阅读相关报纸和书籍,渐渐地对天体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3年终于考取了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研究生。从研究物理学发展到研究天文学,其间跨度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二者关系较为密切.物理学中很多理论都是从天文学观测总结而来的,比如开普勒根据前人对太阳系行星多年的观测数据总结出了开普勒三定律。
我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读研究生的两位导师对我影响都很大。宋国玄老师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他引领我进入天体物理的研究领域。宋老师研究的是星系的计算机数值模拟,使我掌握了数值模拟这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沈有根老师研究量子宇宙学,我跟随沈老师做量子宇宙学方面的博士论文,这是非常前沿的领域。宋老师在数值模拟方面的指导为我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数值计算基础,而沈老师则在早期宇宙理论方面帮助我奠定了宇宙学理论的基石,两位导师的完美联合指导对我的博士论文和日后的科研有着极大的帮助。此外,两位导师高尚的人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受体制的影响,国内很多科研人员都很浮躁,甚至急功近利,但两位老师,尤其是沈老师仍然对自己严格要求,时刻牢记华罗庚先生对他的教诲,做学问一丝不苟,不计名利,让我由衷地佩服和尊敬,永远是我科研道路上的楷模。
记者:在天体物理方面,您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呢?
张同杰:谈不上重要成果,只是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谈一谈的地方。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中一方面就是在宇宙学的数值模拟方面,我们做了弱引力透镜方面的研究。举例来说,在距离很远处有一个天体或类星体等,它发出的光经过星系或者星系团到达望远镜时,会发生引力透镜效应,因而该天体或类星体可能会形成几个像,如果背景是一个星系,星系的形状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引力场的扰动造成的,我们用数值模拟去研究这些问题。目的是为了确定宇宙中这些物质的含量,目前能够观测到的宇宙中物质成分占了30%左右,其中包括用一般的电磁波能探测到的重子物质,以及只能间接探测到的暗物质,而另外70%左右则是暗能量,是我们目前很难直接观测到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银河系、星系团和大尺度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它们是从早期很小的密度扰动,经过了引力不稳定性慢慢从非线性阶段到线性阶段逐渐形成的。在经过非线性阶段的时候,损失很多信息,我们观测到的只是复杂的非线性阶段之后的结果。我们通过小波技术,利用数值模拟出的图像,能有效找回损失掉的信息,这对于研究整个宇宙及其各个阶段的状态具有重要意义。找回的信息越多,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也就越清楚,这是我们最近几年做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和研究生于浩然关于这方面最近的两个研究成果,其中一个已经在国际著名刊物《天体物理[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杂志上发表[2011 ApJ ,728, 35(arXiv:1008.3506)]; 另一个工作(arXiv:1012.0444)正在回复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杂志审稿人的意见。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从2006年以来一直做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就是利用哈勃参量数据对宇宙学模型进行限制。在我们做这项工作之前,美国有一个小组,通过利用星系的年龄而得到的数据,对标量场的势进行了限制,但是他们没有把这批数据用在宇宙学参量的限制上。宇宙学参量就是指宇宙中物质占多少暗能量占多少等数据情况,我们是国际上第一个把这批数据应用在宇宙学参量限制上的科研团组,现在国际上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同行都在关注我们的这项工作的成果,所以引用率很高。目前我也正被邀请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综述性文章(arXiv:1010.1307),很快也会在美国Advance in Astronomy上发表。另外,我和研究生马骢在这方面做了更加深入的工作,即对这批数据做了一个模拟,研究模拟出的数据在将来对宇宙学参量的限制能力。我们的工作将在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杂志2011年3月第729卷第2期[March 10,2011,v729-2.issue (arXiv:1007.3787)]发表。
这两方面工作近几年在国际上是很有影响的,目前项目进展状况良好。第一个项目是我带着几个硕士生在做,而且和加拿大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的天体物理学家进行合作,进展非常顺利,第一项工作结束之后马上还会有一系列的工作紧接着进行。现在我们把小波技术应用在大尺度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信息损失降低上,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们还设想把它运用到天体物理结构形成的各个领域中,比如引力透镜等方面。这个项目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已经得到了国际的公认,论文还没有发表就已经被引用了。关于第二个项目,因为现在哈勃参量的观测数据还不多,将来会越来越多,所以前途更是不可限量。至于我们对这些数据所进行的模拟所呈现出的对宇宙学的参量的限制能力会有怎样的效应,随着未来对宇宙观测的更深入,数据的增加,我们的工作会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记者:关于宇宙运行的周期,发展变化规律,一直有很多普通科普爱好者乃至公众都很感兴趣,比如前一阶段流行的“2012世界末日说”,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未来的宇宙将有怎么样的变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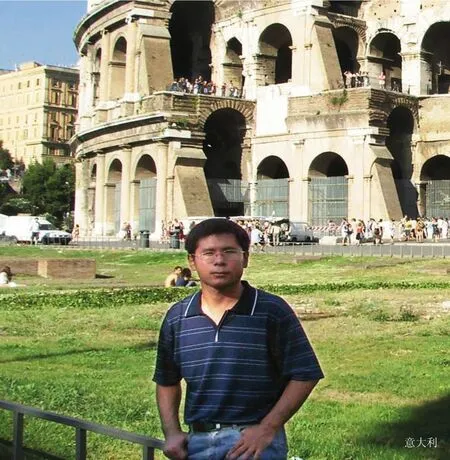
张同杰:人们对它的关注是有原因的,最近几年自然灾难很多,海啸、火山、地震等频繁发生,人类去思考这些问题很正常。环境污染是上百年造成的,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各种污染成倍增加(详细数据参见美国能源部长华裔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访华期间的演讲),虽然现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这是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基础上的。最近大量的自然灾害,与人类对地球肆无忌惮地开采、掠夺是有关系的。人们看问题,更应该从历史角度,不应该从迷信和渲染的角度去看问题。关于“2012”的问题,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宗教人士的观点都不尽相同,他们是从圣经的角度谈世界末日,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人之间的观点也是有矛盾的。当然我是从科学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天体物理学家是不相信世界末日的。我认识一个著名的宇宙学家,他曾经计算过“世界末日”,也就是地球被毁灭的概率。他使用的是科学的方法,考虑了各种因素,比如地球上大的自然灾害,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附近超新星爆发后喷射的物质流扫过地球并对地球产生威胁等因素。他经过计算,得出了:在未来10亿年之内,地球被毁灭的概率是很小的,当然不排除地球上大量能源的耗费,大量的污染对生态的破坏和对地球局部的破坏,但综合几个重要的因素来看,他的推算是没什么问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Nature杂志上。“2012”的预言是玛雅文化的一部分,很古老,很深邃,我们看玛雅文明要像看神话故事一样,但所谓的预言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从天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记者:我们从您的经历中了解到,您走访过很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您在学术交流中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
张同杰:近十年之中,我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一些国际顶尖大学和研究所,与国际知名天体物理学家进行讨论合作研究,深感国外研究机构学术管理的合理性和学术氛围的科学性。当然,这与西方文化本身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而国内学者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以及东方文化本身一些特点也是导致国内学术氛围差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国内学术评价和管理以及各级教育理念和模式存在严重的不合理性,因而不能与国际先进机制接轨,导致国内学者急功近利,没有办法也不愿去做那些耗时长很难出成果的研究方向,也恰恰是这些方向才有可能有重大发现。这也是国内学者很难做出开创性研究成果的重要原因,这也许可以部分回答“钱学森之问”。
我2002至2003年作为国家访问学者访问了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天体物理研究所,多伦多大学物理系和天文系的研究生除在本系外还可以在加拿大天体物理研究所选择任何导师做研究。在五年的博士生学习中,学生在前两年要换几个方向,跟不同的导师做研究。在最后两至三年之中确定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另外,加拿大和美国的暑期很长,有3个月,政府会在暑期资助本科生到大学和研究所跟教授做研究,即暑期学生(summer student)。这样的机制能够较早地让本科生进入科研领域。在2005年至2006年,我获世界实验室资助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每天上午10点的coffee time令我印象至深。每周一到五的coffee time中教授和研究生都可以讨论学术问题,也可谈学术之外的问题。这样的交流大大增强了研究生与教授之间的沟通。回国后我也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一个研究领域进行不同方向的研究。我的研究生除了跟我作研究外,还要到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和国外其他导师合作研究。这样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研究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记者:现在您作为导师,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方法和特色?
张同杰:我现在带了六个研究生,其中有两个博士,四个硕士。在我看来,博士生的指导可以放开些,只需限定具体的科研方向即可,让其自己探索,发现科学的想法。硕士生的指导和博士生相比,需要更加的具体化,细致化。因为本科生还没有完成他们自己学习阶段的基础课程,也没有研究生的理论基础和科研训练,所以我采取了不同的指导方法。首先,筛选出的本科生的学习基础应该是扎实的,在学业上应该是有余力的,对这些学生可以进行科研训练挖掘他们的科研潜力。当然也有一些对科研非常有兴趣但成绩稍差的学生,不要压制他们的积极性,在兼顾他们功课学习情况适当让他们做些基本的科研工作。
我把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三个团队有机结合在一起,根据学生的特点分配不同的任务,他们之间相互协作、相互指导,形成一个合作群体,效率很高。我在本科生科研方面的成绩已经引起国内研究同行,高等院校管理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号称“科学之祖”,相传,他晚上走路,头望星空,看出第二天有雨。但一不小心,一脚踏空,掉进泥坑,后被人救起。第二天果然下了雨。有人讥笑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然而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哲学如此,科学亦如此。
张同杰采访中也提到了温总理的这首“仰望星空”。“我们所研究的项目都是学科上比较前沿的问题,前景都是非常好的,”他这样说,“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脚踏实地,克服受体制影响所形成的浮躁风气。”
这就是踏实努力、硕果累累的张同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他们正用实际行动谱写着青春,诠释着梦想。
专家档案:张同杰,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7月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天体物理博士学位。张同杰教授长期在一线从事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除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外,同时还担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青年学者(PUCHEP Fellow),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北京天文学会会员,国际天文联合会(IAU)宇宙学分会会员等。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利用弱引力透镜限制宇宙学模型,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引力透镜宇宙学研究,主持在研国家教育部自主科研基金项目——宇宙大尺度结构与暗能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