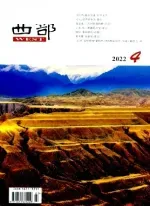窗内窗外
文/曾令兵
窗内窗外
文/曾令兵
上午第二节语文课一下课,华就溜进了宿舍。他几乎每天上午的三四节都逃课,也不纯粹是厌恶英语和化学,他是躲在宿舍里窥视一段令他心惊肉跳的秘密。
华压根儿就不想上高中,他喜欢学中医按摩,将来当一名出色的按摩师。可开煤窑暴富起来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让他学那行当,父亲给县一中掏了两万元,买了个“高价生”的指标让华入学了。
学生宿舍是一座五层的男女生混合宿舍楼,一二层住女生,三四五层住男生。华一口气跑上四楼钻进自己的宿舍,窜到后面的窗户边,迫不及待地拉开窗帘的一角向下鸟瞰:下面是两间快要坍塌的瓦房和一处用石头圈着的猪舍,十来头瘦猪在青石挖凿的长槽边哼哼唧唧地叫唤不止。一阵秋风吹来,猪舍上的石棉瓦吱嘎吱嘎地怪叫。华的目光透过低矮瓦屋的木窗钻进了屋里,紧挨窗户放着一张床——用碎砖头垒砌的床,上面的苇席有两个破洞,露着稻草。枕头是一节木桩,一床脏得几乎看不见花色纹理的破棉被狗一样地卧在床头。这时,柴门突然响了一下,一只肮脏不堪的水桶撞开了柴门,桶底擦着地,里面黏糊的泔水飞溅出来,紧接着便看见高不过四尺的木墩挑着泔水艰难地迈进了院里。瘦猪们突然骚动起来,哼哼唧唧叫唤得山响。木墩放下泔水担子,拿瓢把泔水舀到猪槽里,舀有半桶时才掂起桶一下子倒进槽内。有一头小猪被挤出石槽后抬头望着主人哀叫,木墩用瓢在泔水桶内搅了搅,舀了一瓢稠糊的泔水跳进圈内。小猪在吃“小灶”的当儿,木墩爱怜地用右手抚摸着它的头,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
华没有听见也没有兴趣听他和猪们的对话,他最期盼的是木墩的下一个节目。果然,木墩在料理完这些活儿后就粉墨登场了。他先洗手洗脸,然后进屋换了衣服,拿起梳子镜子站在窗边打扮。这时的木墩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华子的视野下,他先是把自己的头发像油头小生那样向两边分开,但又觉不妥,便又把头发向后梳成个大背头,学者一般……这些表演虽然华烂熟于心,但每次看来都令他好笑。
木墩正梳妆打扮时,院里响起了笃笃的响声,一个拄着双拐、面容丑陋的四十多岁的女人进了院,笃笃的响声同时敲进一上一下两个男人的心里。木墩猴急火燎地从屋里窜出来接迎女人,华的眼球似要蹦了出来。“好你个矮子,还见异思迁,往家里不断领换女人改变口味……”华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华一阵兴奋,这个被木墩引领到家的情妇足可以当木墩的老娘了。前两次木墩招回来的两个女人虽也很丑,但都很年轻。第一个约二十出头,是个长着一张豁嘴且下肢麻痹的女子,第二个二十五六岁左右,是个一脸麻子的少妇。华亲眼目睹了木墩和她们亲昵爱抚、掐皮捏肉乃至做爱的全过程。
木墩领那女人进到屋里,女人的目光在屋里搜寻一番后就势坐到床沿,木墩连忙接了拐杖放在门角处。女人的手开始不安分地在木墩的头上游走,木墩受不了她那份温存,踮起脚要和她接吻,可女人太高了,他踮起脚来也触及不到女人的嘴唇。木墩突然挣脱女人的怀抱搬来一条矮凳,站在矮凳上的木墩才和坐在床上的女人热情地接上了“轨”。亲了一会儿嘴后,木墩跳上床火急火燎地就要解女人的衣服,女人一甩手把木墩摔倒在一边,嘴里说着,手里比划着。华离得太高,根本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见木墩的嘴一张一合,右手也比划着,好像是在讨价还价。终于,两人达成协议,女人开始主动脱衣了。
华照样看得浑身燥热满脸发红,就在华再次俯视那道颠鸾倒凤的美妙风景时,二楼一间女生宿舍的窗户里突然飞出一只硕大的青鸟,青鸟扑扑棱棱地落到木墩的窗台上。创造风景的木墩和女人以及看风景的华同时都被吓了个愣怔。女人“啊”了一声,顺手推掉骑在肚皮上的小男人,拉起破棉被盖在光着的身上。醒悟过来的木墩穿衣下床走到窗台边,这时他才看清落在上面的是一幅绿色的窗帘。他抬头往楼上看,所有的窗户上都挂着绿色窗帘,根本看不见里面的世界,但他分明看见二楼中间一扇窗户内有个美丽苍白的少女此刻在关望着他。他想起过去常常从那扇窗户掉下香蕉、橘子、糖果甚至硬币纸币的幸福时光,心里异常激动。那个面色苍白一脸病态的少女从不向他院子里扔垃圾,只向他偷偷地“空降”幸福、实惠和快乐,今天的窗帘肯定又是她抛下的。木墩幸福地仰视并回忆着,恍惚中他仿佛看见四楼一间屋子窗帘的一角动了动,一个身影便隐没了。

华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连忙蹲在地上,他心里怦怦直跳,居然还有一双眼睛——一双和自己同样焦渴的女生的眼睛——也在窥视别人的隐私!他分明看见那幅窗帘是从楼下抛下去的。那个女生是谁?我一定要找到她!华于是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撩开窗帘的一角偷看,只见木墩正站在马凳上挂窗帘,绿色窗帘挂在了木窗上,木门也悄悄地关上了,屋内那道神秘的风景在华的眼前消失了。
华跑到三楼,尽管他已初步断定窗帘是从二楼女生宿舍的某个房间抛下的,但他还是从三楼开始一间间地敲门,敲完了三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一间屋里有人。他问宿舍管理员看见哪个房间有人,管理员一扫过去冷冰的面孔热情地说:“谁敢像你公开逃学,男生宿舍除了你没有第二人歇课”华想:莫非他也看到了窗外矮子木墩的事,今天对我这样客气?他边想边下到二楼的女生宿舍,他不能贸然敲女生的门,就问女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说高二文科六班的“老病鬼”陶淑娜歇课在宿舍里,不过才走了。华隐隐约约感觉到女管理员好像也发现了他躲在宿舍内偷看别人隐秘的事,说话时眼睛一眨一眨的,乜斜的眼光似要穿透他的五脏六腑。华使劲回忆才想起陶淑娜那病恹恹的形象,难道是陶淑娜抛下的窗帘吗?可华想得脑子疼也没想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又上楼去了。
中午开饭时华在餐厅里寻找陶淑娜,同学们说她又住院了。华把上午发现的秘密说给几个要好的哥们分享,几个人听后笑得几乎都人仰马翻,绰号叫“奔儿”的哥们竟还笑得把饭从鼻孔里窜出箭一样射到另一个同学脸上。这时木墩挑着泔水桶来了,他径直向两口大陶缸走去,一部分同学已吃罢饭,泔水缸里已倒进了半缸泔水。木墩放下铁桶舀泔水,由于个子太矮,他只好在脚下垫两个土胚砖才能够得着。有个大个子男生过去帮他舀泔水,大个子男生抓起一只铁桶,扑通一声放进缸内灌满一桶泔水提了出来,木墩感激地望着他。木墩挑着泔水走过华他们身边时,几个人起哄:“木墩上午又干美事了,‘大鞋’套‘小头’不晃晕你小子才怪哟”
“你人小鬼大,还不停换口味呢……”
“木墩,谁送你的窗帘,说不准以后还有人送你绿帽子哩……”
木墩不搭理他们,落荒而逃,在身后的浪笑中,木墩有几滴清泪砸在了地上。
接连几天,华再也没有发现木墩向家里引领女人。即使有,也被那绿色窗帘严严实实地遮挡着,华再也看不到里面的秘密了,他对那幅窗帘和扔窗帘的人恨之入骨。
一天上午,华逃课后躺在床上给开除了学籍的同学大川打手机,忽闻窗外传来打骂声,他连忙挂了手机起身拉开窗帘向外看,只见一个黑瘦老汉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没头没脑地朝木墩打去,木墩抱头鼠窜,老汉撵着追打,边打边骂:“你个败家子胆大包天,竟敢偷卖猪儿换钱玩女人,我今天不打死你个龟孙才怪!”又一棍下去,咔嚓一声棍子断了,木墩惨叫一声扑通倒地,额上窜出了一股鲜血。老汉还不住手,抡起半截棍子又打下去。华心里酸溜溜的,他再也不忍心老汉打下去了,急中生智顺手抓起床单扔了下去,飘飘洒洒的床单正好罩住了暴怒的老汉,老汉不知所措,待揭开床单子知晓后,就把怒气转嫁给了华:“我打儿子管你屌事?你们的老子办工厂盖高楼大厦,都把爷儿们的土地占光了,逼得老子没地种没活干!地征用了,征地款又叫那帮龟孙子给挥霍完了,我们的日子咋过?”他骂了一阵见没人接茬,就捡起那条九成新的床单走了。华这才放了心。
晚上,没有上自习的华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掂着一个罐子来看木墩。木墩看见女人喊了一声:“妈”,便牤牛一般哭叫着扑进女人的怀里。女人看着遍体鳞伤的儿子,泪如泉涌。她燃火烧了开水,放进些食盐,再把毛巾放进里面浸泡片刻,然后拧干放在儿子的伤处蒸敷,木墩躺在她怀里小猫一样温顺。
女人做完这些,这才打开罐子把里面的排骨汤倒出来让儿子喝。看着儿子香滋滋的把汤喝了,女人这才开始数落儿子:“木墩呀,你也是快奔三十的人了,咋不长一点儿人心。你后爹今天打你是狠了点,可也是为你好啊!女人可是无底洞啊,以后可不能再干那傻事!等攒下钱,妈给你正儿八经娶个媳妇……”
木墩嘴笨,说不出什么,只是憨厚地望着母亲点点头。
母亲走了。木墩忍痛把身子靠在墙上,等待二楼中间那扇窗户内的那个好心少女重新向他“降”下幸福快乐、实惠和安慰。他想今天自己挨了皮肉之苦,慈心少女一定会安抚和犒劳自己的。记得有次他挨了继父的打骂后躺在院子里的地上哭泣,哭着哭着睡着了。梦中他仿佛感觉有一只小蛇爬到了他的耳朵上,搔得好痒。他惊叫一声醒来,发现耳朵旁吊着一个小瓶子,他连忙用手抓住瓶子,便有一根长长的红绒线从高处掉下来。他抬头向上看,一张少女苍白的脸一闪就不见了,红绒线吊下来的是一瓶红花油,木墩用它涂抹伤处,很快就不太痛了。
秋凉阵阵,木墩身上的伤愈来愈痛,好在那香甜的回忆和温馨的期盼支撑着他,他才没有疼得叫出声。上午多亏她关键时刻用床单救了我,要不后爹非打我个筋断骨折……他想着想着,又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突然有什么东西砸在了他身上,砸醒了他。他一摸,是一个馒头。楼上的学生经常向下扔馒头,他们故意不扔到猪圈里,有时扔到院子里,有时扔到泔水桶里,溅起一串水花,惊起一片笑声。他把馒头用力扔到猪圈里,惊扰得熟睡的猪们一阵骚动。这时他抬头向二楼的窗户望望,还亮着灯,但没有一点动静。忽然从最高层的一扇窗户内飘下一团什么东西,呼呼啦啦散在他的头上和身上。他打亮火机一看,是一包花生皮、桔子皮和香蕉皮,他恼怒而又失望的扶墙站起,艰难地回到了屋内。
木墩休息了,但浑身疼痛得没有一点睡意。身上越痛,脑子里那个少女的形象就愈清晰,有关她对自己的好事就不停地涌来。
记得前年元旦那天中午,他正在喝着玉米稀饭,那个少女隔窗扔下一包东西,他捡起来打开一看,是一只鸡腿,木墩感激地向上望了一眼,便俯下头贪婪地啃起来。木墩想着想着,不禁流出了涎水。横竖睡不着,他就掀开窗帘向二楼中间的窗户再看,恰巧这时窗帘拉开了,一扇玻璃也打开了。木墩蹦跳的心险些要跳出喉眼,一个模糊的影子在窗户旁一闪,便有一个东西扔了下来。木墩不顾浑身疼痛一跃跳下床,跑到门外打亮火机查看,可地下看不到什么东西。他再往上看,只见墙半腰的电线上挂着一个半旧的乳罩,正在夜风中飘飞。他的头一下子胀大了,联想起白天抛下的床单,木墩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连忙找来竹竿把乳罩轻轻地挑下来,抱在怀里回屋睡了。
那一夜木墩把乳罩抱在怀里,睡得出奇的香甜。
陶淑娜患白血病住进了省城医院,学校发动紧急募捐。华是全校学生中捐款最多的一个,他捐了三百,因此他作为学生代表随老师到省城医院看望了陶淑娜。集体看望陶淑娜离开医院后,华向老师撒了一个谎又回到医院病房,陶淑娜正望着鲜花出神,她母亲转过脊梁在偷偷流泪。华轻轻推门走进去说:“伯母您放心,淑娜的病一定会好的。”陶淑娜的母亲连忙擦了泪换作一副笑脸面对着他和女儿。华又说:“伯母,请您老回避一下,我想和淑娜单独说一些学校的事。”母女俩先是都一脸诧异地望着他,接着陶淑娜的母亲走了出去。
屋内只他们两人了,华单刀直入:“淑娜,木墩的绿色窗帘是你送给他的吧?”
陶淑娜没有一点血色的脸突然红艳起来:“不不……不,我没有。”
从她那突然红润起来的脸颊和失态的结巴中,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良久的尴尬过后,恢复常态的陶淑娜说:“木墩是个可怜的残疾人,别再耍恶作剧戏弄他了,我求你替我多关照关照他……”
华点点头。
从省城医院归来,华倍加关注木墩的情况,然而木墩的院子里比过去风平浪静多了。他更加勤快地挑泔水,精心地伺候着那些猪们。特别令华感到纳闷和不解的是,一有时间他就钻进屋里,拉严窗帘闭门不出。有几次华看见那个拄双拐的女人和豁嘴的姑娘分别来找他,都被他非常坚决和恼火地吆喝走了。莫非木墩金屋藏娇了?华这样想。
华升了高二,学习越来越紧张了,木墩的事就渐渐遗忘了。期中考试下来,华的考分有了明显提高,班主任老师表扬了他。华心里高兴,一高兴老毛病就又犯了,他给被开除学籍的同学大川打手机,叫他星期天安排一桌,他要带几个弟兄共同庆贺庆贺!
周日那天,华把本班前五名尖子生和三个铁哥们都叫到了酒桌上。华让大家开怀畅饮时,自己却首先喝醉了,他先是把陶淑娜抛给木墩窗帘和他抛给木墩后爹床单的事都抖了出来,然后强令五个尖子生和他一样大碗喝酒。他舌头打着卷儿说:“苟富贵,勿相忘,日后弟兄们考上清华北大当上了大官,别把老哥我忘了。我知道自己肚里喝了多少墨水,这辈子考大学是没指望了……”华说罢自己抢先又喝了一碗酒,然后令大家都要再干一碗,说谁要是不干就是看不起大哥。那五个尖子生平时都是囚在笼子里的鸟,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哪喝过这么多的酒,但酒酣中的男人谁也不想当孬种,都一仰脖子把酒灌进了肚里。结果是三个人喝得胃出血住院,两个人胃里焦灼如火要死不活的,也要到医院洗胃。
为了这事学校坚决要开除华,华的父亲好话说了一箩,眼看还不管用,然后就给校长塞了一个八千元的红包,又宴请了学校领导班子和班主任一次,校方最后给了华一个处分,总算保住了学籍。
日月如梭,转眼华步入高三下学期。高考在即,但华的思想却总是抛锚,脑子乱成了一锅粥,时而是陶淑娜仇恨的目光,时而是木墩锋利的菜刀,时而是母亲自缢的惨状,根本找不到一丁点儿高考的感觉。
陶淑娜死了,据说她走得那么快与华公布了她的隐私有关。
自从华醉酒全盘托出了陶淑娜的隐私后,全校哗然,议论纷纷。
“我说那个病姑娘老是躲在宿舍内,原来是在……”
“陶淑娜送给木墩窗帘,是公开支持木墩嫖娼……”
“看来我们学校要加强政治思想和法制教育工作了……”
传闻飞遍了校园的角角落落,还飞到了医院,飞向了陶淑娜的家乡。那些传走了调的流言,刀一样地戳在了陶淑娜的病体上,加快了陶淑娜死亡的进程。
木墩再到校园挑泔水时,几乎再没有人同情他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道道或鄙夷或嘲弄或冷落的目光,男生向他的身上和泔水桶里扔石子土块,女生向他身上吐口水。每当此时,木墩求救似的目光穿过校园的角落搜寻解救的对象,偶尔让华碰上了,华会毫不留情批评并制止同学们的那些行为。
自从陶淑娜死后,木墩就开始无休无止地磨一把菜刀,磨得锋利无比,磨得华心里寒嗖嗖的。木墩的目光阴冷歹毒,吓得那些试图再向他身上投石子土块的男生马上缩回了手。可终于一天冲突还是发生了,一个高二男生捡起一个石子朝木墩的泔水桶掷去,石子没有落进桶内,打在桶腰上叮当一声脆响。木墩放下担子拿起扁担紧追几步,一扁担把那个男生打翻在地,然后又把他拖到泔水桶旁,掂起一桶泔水扣在了那个男生的头上。
校方正式决定不再允许木墩到学校挑泔水了。木墩的猪们断了食源,饿得叫喊连天。木墩的后爹来了,对他一顿毒打后,卖了几头大一些的猪,又重新给木墩找了个挑泔水的地方。华心里既害怕木墩又同情木墩,他给木墩“空降”烧鸡,木墩连看都不看一眼就顺手扔给了猪们;他给木墩“空降”人民币,木墩拾起来刺啦一声撕个粉碎。华心里煎熬着,他想照顾好木墩以减轻自己心里的悔恨,可木墩根本不认账。
华的父亲在城里多处金屋藏娇的事终于被华的母亲发现,母亲要死要活,但在邻人的劝说下最后还是默认了。父亲给了母亲五十万的养老金,母亲离婚不离家,可她还是经常疯疯癫癫的说想死。
华的心情因此一落千丈,父亲的行为让他觉得无脸见人,临考还有三个月,华大部分时间都不去教室,而是独自呆在宿舍里。再说老师也只关心前三十名学生,像华这样摆尾巴的学生老师根本不管,由他们信马由缰。
这样华有足够时间来关照木墩了,可一连两天,华发现木墩没有开门露面,猪们饿疯了,把顶猪舍的木柱都咬断了,猪舍塌了一角。华想木墩一定是病得不轻,否则他不会放下他心爱的猪们不管的。于是他偷偷来到校园南边,左观右看见没人,然后手扒围墙翻了过去。华到街上买了一大兜吃食快步向木墩家里赶去,他刚一进院,木墩便像警犬一样灵敏地从屋里出来了。木墩的头发很长,身上骨瘦如柴,刀子一样放着寒光的眼睛紧盯着华。华被他的目光盯得周身发冷,结结巴巴地说:“你病了,我……我来看看你……”“滚!我要杀死你们这些龟儿子!”这是华第一次听到木墩流利的语言。木墩刚说完,突然从腰里拔出寒光闪闪的菜刀向华劈来,华扔掉手里的东西拔腿就跑。华一口气跑到了学校围墙边,瘫软在地,休息了好一阵他才有力气重新翻墙跳进校园。等他回到宿舍撩起窗帘向下看时,他发现自己送去的东西已被猪们吃掉,只留下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子。
又是两天过去了,华仍然不见木墩出户。只是那些猪们得到了安抚,石槽里不知啥时放进了一些囫囵玉米,它们在抢食。华再看那幅绿色窗帘,窗帘纹丝不动地遮挡住了里面的秘密。
陶淑娜让我关照他,可他如今在屋里是死是活我都不知晓,我是如何关照他的?华问自己。想到这里华便忐忑不安,他在屋里转悠了一会儿,忽然掏出手机接通了大川。晚上大川来了,隔着围墙递给华一根带铁钩的长竹竿,华在院内接住,大川接着就翻进了校园。大川告诉华,木墩的后爹因屡次上访状告镇干部贪污征地款,前几天遭暗算,肋骨被打断了三根,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公安局也说破不了案抓不到凶手,医药费没人管……华听了无语,酸溜溜地送走了大川。
第二天华一觉睡到上午十点,他撩开窗帘看,瓦屋依旧平静,木门依旧紧闭,窗帘依旧遮盖。华觉得自己不能再坐等了,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带钩的长竹竿伸了出去,长长的竹竿带着华的好奇、焦虑、关心和期盼伸进了瓦屋的木格窗内,钩子哆嗦着,终于勾起窗帘,露出了那片神秘的小天地。只见木墩的床上放着一堆生红薯,他躺在床上,怀内紧抱着一个半旧的米黄色乳罩。窗帘被挑开,有几丝金光射进屋内,黑暗中的木墩好一阵才睁开眼睛。当他惶然醒悟时,猛地跳下床赤脚推门跑出去,从腰里拔出菜刀,手起刀落,噌的一声,竹竿一刀两断。华的胳膊颤抖着,慌忙把半截竹竿收回屋内。他看见木墩豹子一样上蹿下跳,手里的菜刀在烈阳下闪着金光,挂在脖子里的乳罩在胸前一上一下地飘飞、一左一右地摇摆……
离高考还有五十七天,华却决定放弃高考。夜里,华买来些瓜果食品红白酒和要好的同窗告别。有了上次的教训,他让几个准大学生喝红酒,他和几个学习差的同学喝白酒。天太热,酒又攻心,大家心里油煎火燎。十一点多钟“宴席”结束,大家上床歇息。华拿了张苇席睡到了走廊上,华在走廊上睡了一阵仍感到心里躁热,就拿着席子爬到楼顶去睡下了。
升入高三后,华他们的宿舍也升到了五楼。大祸正悄悄逼近五楼,暗夜中有一个黑影爬到了五楼,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华所在的宿舍。黑影从腰间拔出刀,从下铺挨着一个一个地杀“西瓜”,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八个睡在下铺的学生无一幸免,血水顺着走廊和梯间汩汩地流向楼下。
幸免一死的华疯了,他手舞足蹈地狂叫着:“啊哈哈——啊哈哈——您们知不知道,我有十个妈啊……”
两天后,警方宣称凶杀案告破,凶手是一个叫木墩的残疾弱智青年。
据说木墩是在一座乡野的孤坟旁束手就擒的,当时他像一个血人,身边扔着一把红鲜鲜的菜刀,怀抱一幅绿色窗帘,内裹一个米黄色半旧乳罩,正躺在孤坟边鼾声动地。警察给他带上手铐时,他嘴里还在喊道:“窗帘,窗帘,别忘了她送给我的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