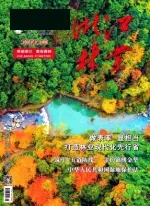雾锁江郎山
□撰文/ 杨菊三
雾锁江郎山
□撰文/ 杨菊三

雾天去观光赏景,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游程是安排好的,我们几位“采风者”还是向江郎山进发了。
入得山中,雾气依然。朦胧中照旧辨得清绕膝之草、冲天之林以及躲躲闪闪的花光叶痕,而想要看得再远一点,便是连轮廓也不露的苍茫了。
我曾经路过江郎山,知道江郎山的主景是岿然壁立的三爿石。江郎山海拔原本不高,所以只现磊落明朗,对云呀雾呀的缠绵便被忽略了。
上山去,总要看看江郎诸峰的英姿。观赏三爿石的最佳处是霞客亭,我们几位脚力不错的便向右边的山径出发了。三四百米的路程,一会儿便到了,抬眼望去,凌风崖上的霞客亭正在向我等招手致意呢。
小巧玲珑的霞客亭,全部石砌,四周凌空,旁边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徐霞客称誉江郎山的一段文字。想当初,徐霞客三上江郎山,很为这里由丹霞地貌成就的三爿石所感动,在与黄山、雁荡山、鼎湖峰的比较中,写下了“自为变幻,而各尽其奇也”的赞语。
将霞客亭孤筑于此,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里四周尽是险峰,在此观赏三爿石最得姿态。然而时过境迁,当年徐霞客有否来过此地,已无从查考,现在除了简简单单的一亭一碑外,了无其他踪迹。但我断定,徐霞客是来过这里的。
我们运气不好,一切的希望都被浓雾包裹得严严实实。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连三爿石的影子都浑然不见,只有对着它们的方位大声地乱叫一气。
十一点多了,我们按原路向左拐弯,没多时,便是由三峰顺势构筑的“一线天”了。江郎山的三尊巨石自北向南呈“川”字排立,每尊通高300余米,形成天然石柱。石柱既高,石缝亦深,由此自然而然地孕育出天开一线、地袭一隙的“一线天”景观。
“一线天”在中华大地上还有不少。近旁如灵隐寺的“一线天”,玲珑秀逸;武夷山的“一线天”,雄阔奇妙;太姥山的“一线天”,环环相连;而我们眼前江郎山的“一线天”,则大气磅礴。它长450米,有“百步云梯”盘旋而上,宽5米,两旁峭壁陡立。
“一线天”外,都是云雾。我们在“云梯”中的石阶向上攀登的时候,不甘寂寞的雾气也紧紧地相随着,不时在我们的周边弥漫开来,让人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但这雾气也怪,漫不到一半路程,居然悄悄地退了。再漫,再退,就是进不到“一线天”的深处。
“一线天”的尽头是登天坪,我从狭缝中探出头来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惬意油然而生。登天坪的面积有700多平方米,在这四周尽是峰林的地方,也算是开阔地带了。
江郎山的三尊巨石各有各名,郎峰、亚峰、灵峰排列有序,主峰824米,其他两峰雄姿也不相上下。江郎山的江郎,很多人都把它和南朝文学家“江郎才尽”的江淹混淆起来。其实,民间流传的说法有许多,江氏三兄弟登巅化石的传说比较流行。
站在登天坪,近距离地观赏江郎三石是比较过瘾的。但须仰望,那真是壁立千仞,摩天插云呀!三尊巨石,一道风景,既雄奇,又险峻,石柱的下半截苔藓铺排,浅草摇曳;而上半部却绿树碧痕,林木叠翠。尽管有大雾遮着,有山岚漫着,我还是循着白居易的诗意,品出“安得此身生羽翼,与君来往醉烟霞”的韵味。
当然,距离近了,三爿石的通体面目也不能全盘入目了。近时虽然看得真切,但要一览全貌,还是应该站得远一些更佳。距离产生美么!这样想着,我又重生远距离欣赏三爿石的念头。于是约了几位摄影爱好者,下了“一线天”,回到了霞客亭。此时,云雾已在涌动,这是开天眼的前兆,等了不到10分钟,那天果然慢慢地收起了云头,三爿石也渐渐地有了轮廓,在云雾的作合中,波翻浪涌,缥缥缈缈,忽儿崭露头角,忽儿销声匿迹,竟有了一种仙女般的柔情和灵动。我们欢呼雀跃,将相机对准三爿石,轻轻地按下了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