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时光之上
文/周庆荣
画/吴建雄
爱:时光之上
文/周庆荣
画/吴建雄
沉默的砖头
会有这么一天的。
一块一块的砖头,在建筑的下面,它们来决定一切。
苔迹,不只是岁月的陈旧。
蚂蚁,或别的虫豸,访问着这些沉默的砖,它们或许爬出一个高度,它们没有意识到墙也是高度。
有一天,这些砖头会决定建筑的形状。
富丽堂皇的宫殿或不起眼的茅舍,这些砖头说了算。
上层建筑是怎样的重量?
沉默的砖头,寂寞地负重。它们是一根又一根坚硬的骨头。
它们就是不说话,更不说过头的话。
它们踏踏实实地过着日子,一块砖挨着另一块砖,它们不抒情,它们讲逻辑。
风撞着墙,砖无言。风声吹久了,便像是历史的声音。

秋夜
月,真的如钩。
挂半夜的思念,一生的离愁。
站在寂静处,秋风阵起,天空里星星的眼神,一丝凉意在前。另一丝寒意,在后。
不是我待在北方的秋夜里,固执地预言寒冷。不是我拒绝跟随日晷的影子,与温暖随时随地厮守。
大片大片的棉田,棉花雪白。
寒冷的人们啊,快点去那里。拨响长弓,弹出棉絮里飞扬的暖意。手摇纺车,一切还来得及,纺纱,织成暖衣。
如钩的月,挂着我半夜的思念。没有方向,我的思念漫无边际,谁此时正感受着深秋的凉,谁还未找到自己的棉田,我就思念谁。
至于一生的离愁啊,我一边行走,一边自己为自己取暖。这漫长秋夜里月光的清冷,就当作是冰镇过的光明吧。

圆明园
你们一定有能力,再去毁灭另一座园子。
阳光如注的时候,百花盛开。
我们进不去,太监走着软步,在园子深处。他们不一定有着很好的心情,但圆明园是一座美丽的花园。
你们一步就跨进去了。
大红的中国灯笼变成火把,火光冲天。你们这些狗杂种,你们在花园深处,你们以为自己心情很好,就像后来的日本强盗,觉得可以毁掉别人的江山。
圆明园是一座美丽的花园。
你们不走软步。我赶到现场的时候,迟到了一百五十年。
火光可以更亮一些。
上帝,看啊,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国书生,挥剑,想阉了那些杂种!

荷花与芦苇
冰清玉洁的美人和草莽英雄,这是我印象中的荷花和芦苇。
啊,荷花和芦苇!它们,谁是谁的背景?一片湿地,风和日丽时的家园,暴风骤雨时的家园。
潮湿的环境。秋天里,芦苇花苍茫成草莽英雄的头颅。这时,荷花开始残败,英雄的心情像深秋的气候。芦花熟了,头发蓬松。
冰清玉洁是多么的美好。
挖地三尺,怀念与寻找。美人如藕,英雄,站在没膝的污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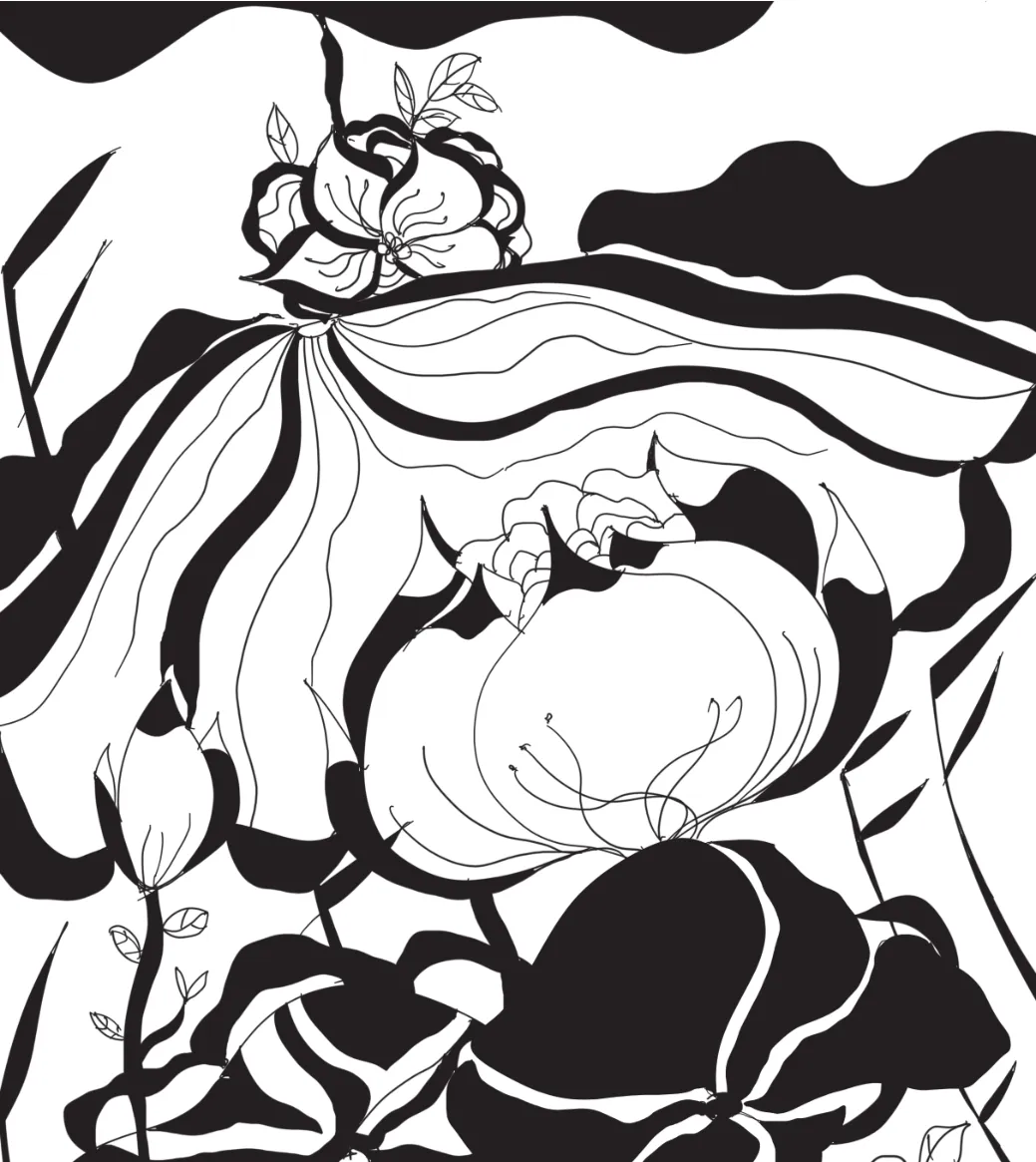
我的爱情
你不安静地在某一个方位出没。
你弹出一指流星,落下,我成为草原上孤独的篝火。
不需要把场景放得那么遥远,我常常固守苍茫。我的爱总是大于爱情,浪漫早已是忧郁的怀念。在这个稍显寒冷的冬季,我看到落叶翻了一个筋斗,它们和泥土待在了一起。
我的灵魂真的像闲云野鹤,但我心思缜密。我记住每一个黄昏晚霞的瑰丽,所有绯红的面颊一定是记忆里的传奇。天涯和海角都是漫漫长路,什么样的旅行能比得上我临窗而坐?
在时光之上。
我的爱大于爱情,我的爱情啊,它尘埃落定。

冬日漫步
一层冰在平静地总结着北方这片湖水。最后的水鸟,哪里是它们最后的阵地?
冬日的时光,心情可以暂时不去荡漾。落叶的飘零,不是忧郁的理由。在寒冷的空旷里,我选择信步。风可以再大些,大到摧枯拉朽;风可以再寒冷些,冷到我觉得这样的冷只与气候有关,它不是人类的一种宿命。
是啊,结冰了,起风了。
冰再厚些,封杀冷漠。直到我可以在冰面上行走,踏上一脚,再踏上一脚,我所走过的路程,有一个季节的记忆能让我自豪,自豪到终于把冷漠踩到了脚下。
而风呢,它一边把天空吹干净,一边寻找飞鸟远去的踪迹。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以行走的方式将自己温暖起来。

周庆荣: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江苏。已出版著作多部。代表作有《爱是一棵月亮树》《我们》《有理想的人》《英雄》等。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