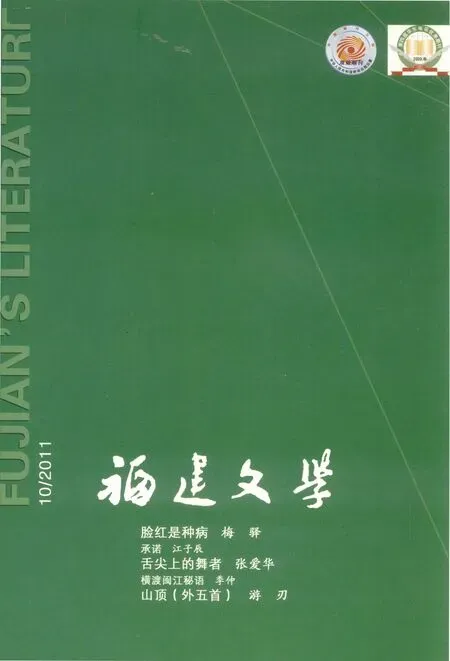满月酒
林落木

大儿子和二儿子打了好几个电话,德舜都不接。我就是不接,有本事,你们就自个儿办好满月酒。德舜正拉着孙女程听的手,在烟城车站转乘回禾镇的班车。听着腰间手机的铃声响个不停,德舜憋了一肚子的气,反正自己也要回老家喝酒。邻居开食杂店的老程旧房翻新,乔迁新居,今晚办酒席。
上个月的今天,已生了女儿程听的二儿媳在烟城医院生了个儿子,全家都乐坏了。德舜忙前忙后,忙得不亦乐乎。那几天,除了老太婆,还有亲家母也来医院照顾。德舜当家当习惯了,一会儿让二儿子按医生吩咐的去续费,一会儿让老太婆抱孙子时当心点,一会儿打发亲家母回二儿子在城里套房去煲鸡汤,一会儿提醒儿媳注意给孩子多裹些衣服。老太婆有些不满,就你精明,就你能的,那你也生个儿子来看看。一下子呛得德舜说不出话来。他看见儿媳偷偷地发笑,让自己很下不了台。
德舜有过一个女儿,三十多年前,家里揭不开锅,妻子奶水不够,他把还没满月的女儿送给沿海人家当童养媳,只换回了二十几斤薯干,如今也不记得女儿在哪里。自己那也是童养媳的媳妇哭了几天后,也就认了这个事实。德舜依稀记得大姐曾说过,自己其实还有一个姐姐。但解放前,兵荒马乱,缺衣少食,也送人了。德舜偶尔也伤心,解放前解放后,生活怎么都是一个样的。
但不高兴归不高兴,大儿子生的也是孙女,读小学了,由老太婆照看。如今程家终于有了个男孙,这才是自己最大的高兴。碰见村里人,德顺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他愿意给村里人说家里高兴的事。十几年前,大儿子考进浙江大学,村里人大多知道清华北大,唯恐别人不懂得浙江大学,他跟村里人说,浙大跟清华北大是一样规格的大学,全国前几名的。大儿子毕业分配到市设计院,他就跟村里人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工程师的,当设计师的,工程设计项目一个接一个的,一年下来,奖金福利跟分红够买套房子。二儿子相亲,他就跟村里人说,儿媳妇娘家是大户人家,承包果园几百亩,一年收入七八十万,怪吓人的。
德舜话多,在车上,不知怎么的,就跟一个年纪差不多的老汉攀上了话。看着老汉满脸皱纹,他就颇有感慨,好像感慨从老汉的皱纹里跑出来的。德舜说自己吃苦习惯了,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觉得累,又觉得理所当然,是应该的,命该如此。老汉也感叹说,自己也是这个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德舜感到,两个儿子对他的话不那么在意了,他们要自己拿主意了。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都当父母亲了,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了,有主见了。但德舜有些委屈,孩子也不能因为成了家,立了业,就什么事情都独自主张,有些大事,还是要尊重父母的,要服从上辈人的意见,比如买房子,要不要买,怎么买,买几套,房子位置,落户名字,等等,都是大事。作为年轻人,百密一疏,考虑终归不会周到。若是嫌贵,犹豫一下,今年没买,明年房价就涨了,过了这村,没了那店。
德舜告诉老汉说,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他就劝说儿子买套房,按揭贷款,最好买两套,为子孙后代留下厚实的家底。但大儿子埋怨说,生活压力大,会失去乐趣的。二儿子说,不小心就会变成房奴。
就由着孩子去吧。老汉对德舜的委屈很是同情,他用同病相怜的口吻对德舜说,人也是不经老,在儿女眼里,人一老,就跟不上时代了,没用了,得靠边站。德舜嘟囔着说,没办法,谁让自己是当父母的,他们以为我们是瞎操心,其实,哎……
快下车时,德舜不以为然地对老汉说,什么房奴,对后代交代得过去,在村里风光些,当房奴也是值得。老汉微笑着,赞许地点了点头。
下了车,德舜心里还是有气。这回为在哪里办孙子的满月酒又引起了争端。程听满月时,按老家风俗,没有办。这次他主张在老家办,风风光光地办,请村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来喝酒,为了不让儿子反对,他拍胸膛说自己负责酒宴的费用。二儿子反对他的做法,对他所谓的面子不以为然,说满月酒也不是什么大事情,简单点就行了,现在村里人少了,也请不到什么人,到时候在附近酒店办两三桌,请父母双方和一些亲戚来聚聚就行了。况且大家都忙,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父子一样的脾性,谁也说服不了谁。德舜一赌气,回禾镇去了。这次他没有把孙女扔给老太婆,只给老太婆说要回家喝乔迁酒,顺便给龙眼树疏果。老太婆一听,急了,明天就是孙子满月了,还疏什么果,你忘了上次摔伤了腿骨?明早赶快回城里。你不来,算什么回事,亲家也是要来的。
德舜心里说,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从禾镇下车到禾村家里,只需十分钟的时间。下车时,德舜才感到肚子饿,他问孙女饿坏了没?
快六月了,天气有点热。德舜往村道旁大片大片的菜地看去,他感到心里忽然轻了许多,堵在心里的事情虽然还在,但好像暮色里的山峦一样,模糊了,看不清楚了。
眼不见,心不烦,此时,有关田野里的庄稼和蔬菜占据了德舜的心里。过去孩子小的时候,德舜召唤全家种菜,油菜花,花菜,包菜,菠菜,蚕豆,芥蓝,丝瓜,等等,哪样赚钱就种哪样,种了一茬又一茬,浇水,施肥,采撷,收割,几乎都是全家听从他的号令齐上阵,然后他用三轮脚踏车运到镇市场去卖,有时在田地里直接卖给收菜的市场摊主。这些蔬菜就像孩子一样,很听话,很乖巧,服从有劳才有获的规则,服从辛苦劳动的主人,仿佛懂得主人的辛酸苦辣,懂得主人的付出。主人买来了菜苗,等于是收养了它们;主人撒下了种子,等于是培育了它们。它们得感激主人,听主人的话,用卖菜所得的收入来回报主人。
爷爷,我肚子饿。程听愁着眉头说。
德舜抱起了孙女说,乖,等下吃酒席,好不好,听听听爷爷话。
程听嗯了一声说,听听听爷爷话。
程听又问,爷爷,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德舜轻轻地刮了下孙女的鼻子说,傻瓜,这是咱们的老家,老家你懂吗?
程听说,不懂,你说老家是什么,有那么老吗?
德舜听了笑起来,禾村就是老家。
程听说,你还没回答问题呢,什么是老家?
老家嘛。德舜想了一会儿说,老家就是你爷爷的爷爷的家,也是爷爷的家,也是听听的家。
程听想了一下说,不对,不是听听的家,是爷爷你们老人的家。
老家老家,老了回来住的家。老家不定会让人活到老,但会让人想到老。德舜觉得自己好像在绕口舌。
程听在暮色中睁大了眼睛,满眼疑惑。
德舜沉积着暮色一样的感慨,继续往家里走。他看见了稻田,想起自己和老太婆从前劳动的情景。大儿子挑着秧苗,二儿子一手提着装有水壶和瓷碗的竹篮,一手拎着装有馒头的塑料袋。那时候,德舜干活累了,直起腰,双手倚拄着锄把,微笑着望着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虽然淘气,争着吃的玩的,但有自己站在那儿,为他们主持公道,哥哥要让着弟弟,护着弟弟,但弟弟也不能总是占着便宜,有时也要让给哥哥。让他们做到公平竞争,互助互爱,就像村里互助组一样。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服从自己的统一指挥和安排,避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出现。
想着想着,德舜就觉得这辈子过得实在是很不容易,自己也很不简单。一个这么大的家庭,没有一个主心骨行吗?虽然偶尔会想起女儿,有点后悔,但又能怎样?后来日子好了点,可自己和老太婆已过了年纪,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爷爷,你今天肯定有不高兴的事情。程听说,这次六一儿童节,我没得红花和奖状,也没你这么不高兴。
德舜愣了下,去年你不是得了红花和奖状?是不是今年表现不好?
吴腾表现比我还不好,他凭什么就有奖状?程听马上就嚷起来。
吴腾是二儿子套房邻居的孩子,和程听一起念大班。他接送程听,经常在幼儿园门口碰见接送吴腾的邻居老人。周末有的时候,自己有事,出去了,就让程听到吴腾家一起看动画片。
吴腾很乖,很听话的。你是不是不听老师的话?德舜知道孙女的脾气。
不就是跟老师顶了一回嘴嘛。程听有些委屈。担任班级小队委的程听经常在课堂上直接向老师报告谁做小动作、谁不听课看漫画、谁在底下说话,惹得一些同学不高兴。辅导员课后委婉批评她不要在课上揭发,程听顶嘴说,那同学会说我是暗探了。
德舜不知道内情,也有些严肃地批评程听,不许跟老师顶嘴,这样不礼貌,懂不懂?
就你懂,就你懂,是老师的错,不是我的错。程听一下子就泪水汪汪的。
德舜赶紧笑着说,不是的,听听没错,听听说来我听听。
听孙女诉说了一遍,德舜心里叹口气,说,还是听听勇敢,有责任心,对班级有爱心。听听也是很聪明的,应该在课后再报告老师。
背后报告老师,同学会以为我是班上的卧底,卧底是什么,爷爷你不懂,卧底是灰太狼。
现在的小孩啊。德舜笑了起来。
到了老程食杂店,程听看见旁边一幢混砖新房外挂着一串一串红灯笼,一排临时搭盖的土灶蒸汽腾腾,焖豆腐醇厚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拉着德舜的手说,爷爷,是不是这里?
德舜哈哈一笑,听听长大了,识得地方了。
老程抬头一看,哟,德舜回来了,不在城里享福,怎么转回乡下来?朝德舜身旁一瞧,哟,孙女也回老家了。
刚才听爷爷讲老家的含义,虽然听了不大明白,但从这陌生人嘴里听到老家这一个词语,她觉得大家好像都以为只有她不大明白老家的含义,就撅着嘴说,老家到处乱糟糟的,谁稀罕呢?
老程的老伴在店里停住忙碌的双手,招呼他进来。老程让老伴应付别的事,自己坐在里屋桌旁,陪着德舜喝茶。跟车上的老汉一样,德舜和老程一聊就聊到儿孙身上。从前,德舜愿意跟村里人说儿子的工作,说儿子买房,说孙女的聪明,说能够令自己喜兴的事情,说旧房翻新,还有上个月儿媳生了第一个孙子。但这次,他不想说孙子满月酒的事了。
老程大儿子出来迎客,见了德舜,打个招呼,就掏出了烟。德舜摆了摆手说,没抽没抽。老程大儿子就笑了,还是德舜会过日子,哪像我们,抽的抽,喝的喝,一年下来,没剩几个钱。老程在一旁听了,脸阴了下来。
老程有三个儿子,一个在外揽泥水工,一个跑出租车,一个在镇里租摊位卖肉,收入无多。这次老程旧房翻新,是三个儿子贷款凑钱盖起来的,一人一排,同墙共壁,合成一幢,体现一家团聚,兄弟连心。他们揣测老程开店子,应该有一大笔积蓄,但老程也只是拿出五万。三个儿子都不相信老头子只有五万,几次提起,都被老程顶回去。三个儿子都愤愤不平的。
去年老程孙子满月,就在这底层开张食杂店的三层楼房里办了八九桌酒席,自己也被请来。德舜记得自己当时就跟老程说过,要是二儿媳生了孙子,他要在新翻盖的楼房办个八九桌,好好庆贺一下程家有后,香火不断。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禾村一队几乎都姓程,自己家应该露脸些,在别人眼里或者心里的默默对比中,把别人家比下去。
要把别人家比下去,德舜想,按照农村的眼光,不外乎就是比赚钱,盖楼房,儿子出人头地,儿子生孙子,一家人无灾无难,平平安安。还有,他觉得,有什么家事要办得风光些,自己脸上有光彩。但今天,人家风风光光地又办了酒席,而且比去年更隆重,更热闹。一对比,德舜心里又来气了,可二儿子不把自己的意见当成一回事,不把孙子满月酒当成一回事,平平淡淡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习惯把家事当成一回事,习惯把家事办给全村人看,办给亲戚看,办得热闹,体面,仿佛不这样,就对不起祖宗。德舜有点沮丧地想,莫非真像今天车上邂逅的老汉说的那样,自己落伍了,怎么做都是错的。
德舜带着程听回家整理床铺被褥后不久,一阵鞭炮声响过,热腾腾的焖豆腐作为头道菜就端上来了。现在,农村酒席不比以前了,用的料都是很时兴的,鲍鱼,九节虾,鱿鱼,白切羊肉,焖豆腐,烤猪蹄,土笋冻,等等都有。也有本地地道特色菜,令人百吃不腻的有焖豆腐,卤面,还有五花肉滑,炒泗粉,卤面,西天尾扁食好像不上正式酒宴,成为纯粹的风味小吃。
看着孙女吃得很高兴,德舜让孙女吃得慢一点,嚼得细一点。他心里想,孙女不是平时没吃到这些,儿子其实还是很孝顺的,赚了钱,家里伙食不错,饮食要求高了,经常叮嘱他和老太婆注意这,注意那,海鲜多吃些,海带木耳多吃些,肉类少吃些。不知不觉的,孩子当起了家,成了家里的主梁骨。
同桌的德舜都认识,只是程听不认得。程听念幼儿园大班了,在城里念,当然不认得老家的人了,但老家的人认得。他们喜欢在热闹的场合跟孩子闹着玩,他们听德舜说孙女书读得好,聪明伶俐,于是,他们边吃菜边问程听,你叫什么名字,说来听听,听听好听不好听?
程听大方地说,我叫程听。
一位名叫程伟的,听了哈哈大笑,听听,程听,听听好听不好听?真好听。
程听听了,也不禁笑了起来。
程伟又问,爷爷好,还是爸爸好?
隔桌一位阿姨笑着说,乡下人就会讲乡下话,这怎么好比较呢?这个问题多土啊。听听,我们不听他的。
程听不怕生地说,谁说得好听,我就听谁的。
啧啧,才几岁呢,多会说话啊,简直是人精。那位阿姨称赞着说。
那位阿姨直夸德舜家真是有福气,孩子争气,在城里工作,一个个精灵麻利,不用老人操心,连五岁孙女都那么大方,长大了肯定有出息的。
阿姨末了对程听说,你看,你爷爷多疼你,现在还是女孩子听话,体贴人。
德舜听了心里很受用,一天来的郁闷消散了许多。但还是忍不住说,还不是当个免费的保姆?
自己一家几乎都在城里了,大儿子大儿媳工作忙,二儿子二儿媳应聘在公司跑业务,经常出差,扔下孙女、孙子,两个老人只好住在两个儿子套房里,洗衣做饭,擦洗地板,照料孙子,送孙女上学,督促孙女弹琴,一天下来,忙得腰肩酸疼。德舜想,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哪家不是这样子?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
就在这时候,楼上传来了争执声,好像是老程的声音。窗户关着,声音隐隐约约的,听不甚清楚。
程伟低声告诉德舜,肯定是跟老程三个儿子又为老程的积蓄有关,老程三个儿子老早就怀疑老程把积蓄隐瞒起来。老程替自己辩护,我干吗要把积蓄隐瞒起来?三个儿子说,谁知道呢?伸手摸心,自个儿知道。老程差点气出了心脏病。
程伟感叹着说,真是子孙不孝啊。
那位阿姨在旁边劝程伟说,别乱说,小声点,别让老程儿子听见,听见了会打死人的。
程伟又感叹着对德舜说,还是你有福气啊,儿子能独立自主,家里盖了房,年老了,还去城里带孙子享福呢。
德舜忙摆摆手,谦虚地说,大家都一样,都有着自己的苦和乐。
德舜平常不怎么喝酒,但今天还是喝了半瓶多红酒。
大儿子又打来了电话,儿子告诉他,明天一早就回来,要不要用车子去接?他说,不要了,他要带程听在家里住一宿。儿子又特意交代,明天千万别去爬树疏果,树就放着吧,龙眼能收多少就多少。
德舜说,知道了。
儿子似乎反问他,去年爬树摔下来,你还记得不记得?
德舜一听心里又来气。摔断手骨一年来,儿子儿媳他们似乎把他当成小孩一样教育,他理解他们的用心,但不能就此看轻了他,好像把他当成教育孙辈的反面教材。他们没吃过苦,不理解自己的心思,不理解农村人的想法,不理解自己对果树付出的心血。自己是不忍看着龙眼树挂着龙眼,而主人没有把它们采下来。儿子嫌弃果树,可这十来年,还不是靠果树交学费,盖房子。虽说另有赚钱的门路,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己靠果树赚钱,轻车熟路的,心里有谱。
孙子满月酒,不是有你们吗?在城里办,又没人看见,缺少我一个没啥关系。
想到这里,德舜心里气更大了,你们不看重我的意见,那就别指望我出来捧场,反正你们嫌我没什么用处。德舜就这样决定了,明天带孙女去果林蔬果。
吃好早饭后,德舜一大早就扛起自家的长竹梯,拿着大剪刀和小锯子,往老程家屋后的山坡去了,德舜的果林就在那里。程听睡眠不足,一路上嘟着嘴,情绪不高,我要让爸爸用车来接我回家,老家一点都不好玩,爷爷骗人。德舜安慰说,到了到了,树林里好玩的,晚上我们就回去。
龙眼树虽说只有二十几株,但这几乎是德舜一个人照顾到现在的。在德舜眼里,这二十几株龙眼树就是他的孩子。有些树老了,那是包产到户时候,由村里按人口划分过来的,德舜把它们当做领养的孩子。有些是自己和老太婆后来在老树之间的空地块上栽种上去的,他把它们当做亲生的孩子。如今,不管是亲生的,还是领养的,都已经长大了,它们依然一年一年地回报自己的养育之恩。德舜想,虽然现在村里人不大看重果林了,近几年来,自己也或多或少疏忽了它们,没像十几年前那样,经常扛着锄头去除除草,以免让杂草跟龙眼树争夺有限的肥料养分,或是挑了担粪水,浇到树根延伸的地方,增加龙眼树的养分,让龙眼树长得更茁壮些,争取来年龙眼长得更多更大些。那些年,德舜的日子几乎是绕着它们过来的。
近年来,儿子对他照顾龙眼树有看法了,认为现在不依靠果林过活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比如照看孙子,帮老太婆做家务,或者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避免给他们增加后顾之忧。尤其是疏果、裁枝、摘果等危险举动,更是让他们提心吊胆。
我知道你们心里打什么小九九的,自私。德舜想着,爬上竹梯。刚踩上半腰梯,他就感到脚底有点晃,有点不踏实的感觉。德舜疑惑着想,去年就不是这样子,难道自己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德舜只疏剪树冠周围的龙眼果,树冠顶上的竹梯够不着,他就爬到树杈,小心翼翼地修剪果枝,裁择刚刚成形的龙眼。这些约摸无名指头大的龙眼,表皮稍显粗糙,不像熟透的龙眼那样呈黄褐色,而是淡绿色的。它们密密麻麻地挤成一簇一簇的,好像一团一团婴儿挤在那里。而德舜用剪刀,把它们当中个头比较小的疏剪了,把形状比较难看的疏剪了,把生命力比较弱的疏剪了。至于怎么判断,就全看自己了,优胜劣汰,自然规则吗,从来都是这样的。可是今天,德舜觉得自己有些难受,有些舍不得,又觉得自己不得不这样。
德舜想到那些孩子生得多的家庭,养不起,就把丑的气力不足的男孩送了人,或者把女娃送人。去年,程伟的儿媳生了个丫头片子,两个月后,村里人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孩子,程伟家人说是患了先天性心脏病死了。德舜想,也许是吧,也许把她遗弃在福利院或者车站等地方。谁都说不清楚。
这么想着,德舜忽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刽子手,残忍地杀死了龙眼树多少无辜的孩子。为了能够采收又圆又大的汁多可口的龙眼,自己就遗弃了那么多跟它们争夺有限养分的果仔。有时干脆把整条带着整簇整簇果仔的龙眼枝条裁剪了。它们现在在哪里?当然已经腐烂了,化为龙眼树根的养料。那些被裁锯下来的龙眼枝条晒干后,当做柴木被送进了灶膛。
恍恍惚惚的,德舜仿佛看见了三十多年前刚出生的女儿,她满月时,养父家肯定不会办满月酒。她慢慢地长大了,但长得慢,像丑小鸭,像躲在角落里细小的龙眼果仔,不起眼。为了养父家的哥哥、弟弟,她被冷落一边,吃剩饭剩菜,上山砍柴,下田种地。哥哥弟弟上学去,而她起早贪黑,挑水做饭。也许,她知道自己童养媳的身份,但没有一丁点儿亲生父母的信息。在一些黑夜里,她睁着消瘦的眼睛,想着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想象着亲生父母的样子。她怎么也想不出来,她苦闷,忧郁。德舜想,她肯定恨自己,但她想不起亲生父母的模样,就像自己也记不起她现在的模样。
她长大了,许配给养父母家的哥哥,也许哥哥看上了别人,就许给弟弟。也许,弟弟也没看上她,养父母就把她半嫁半卖,把她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德舜知道,这是沿海农村的风俗。德舜感到自己的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揪成一团,可沿海那么大,自己要去哪儿找?
就在这个时候,德舜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听听。然后从树上低头去看程听。德舜走神了,脚底一滑,身子从树上摔了下来。快落到地面时,德舜下意识地用手肘往地上一撑,胳膊一阵剧疼。他知道,自己又犯了错误。
坐在儿子车上的时候,德舜手臂疼得特别厉害,抬不起来。大儿子皱着眉头,准备送他到医院去检查。程听在旁边安慰他,爷爷,骨头断了,医生接起来就好了。德舜不想说话,他想起那些被自己疏剪后落在地上的枝条和零碎的果仔。德舜疼得又叫了声,哎哟,哎哟。浑身无力,脑子像婴儿那样混沌、空白、原始。
车经过稻田时,德舜心神恍恍惚惚的,好像回到了过去,依稀看见自己和年轻的妻子在田里干活时的情景。清澈的小溪从田野中穿过,向木兰溪流去,那里有着庄稼人的欢乐。金黄色的油菜花在田野上飘忽着,年幼的女儿双脚蹒跚,自己和妻子正挥着锄头。女儿远远地喊起来,妈妈……爸爸……之后便是咯咯咯的笑声。于是,他看见,在和煦的阳光下,在黑褐色的田野上,自己直起腰,用左手在眼眉上搭起小凉篷,随后就用双手倚拄着锄把,微笑地看着年轻的妻子推掉锄头,跑向女儿,把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抱起了她。
德舜闭上了眼睛,想,那时,自己的二姐又在哪里?
孙子的满月酒,德舜躺在医院里,正挂着瓶,有理由不去了。他只吩咐孙女说,昨天跟爷爷回老家,受了委屈,中午好好吃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