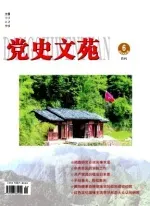拨云显真貌 平心论古人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几点看法
郭平阳 王 博
(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拨云显真貌 平心论古人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几点看法
郭平阳 王 博
(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当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几种认识上的偏差,而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除了文献资料的差异性和评价主体的主观性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评价标准上的不同。因此,必须在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鉴别、分析等多种手段,在理性的标准下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历史人物 评价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意思是说,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历史无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只有那些卓越非凡的人才能遗泽后世,名垂青史。然而,历史的本性在于真实,历史的进程也是无数人物合力推动的结果。因此,拨开笼罩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各种迷雾,用正确的方法再现其真实面貌,用发展的眼光评判其功过是非,于历史有“正本清源”之功,于今天有“经世致用”之益。
一、江山代有才人出,古今评价有差异——评价历史人物容易出现的几种偏差
当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尤其是对有争议的人物进行评价容易出现如下几种认识上的偏差。
第一种是难以脱离“非此即彼”的思维底色。这种评价观认为历史人物的价值“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好人”,穷尽赞誉之词,认定其一好百好,甚至是文过饰非,掩盖其错误与不足;对“坏人”,大都恶评如潮,认定其一错百错,甚至是妄自揣测,忽略其成就与贡献。例如在对孔子评价时,认为其儒家学说是五千年的国学经典,应该大行其道,甚至称应该“独尊儒术”,将其作为国家核心价值取向。这种评价很明显忽略了儒家学说中存在的保守性、片面性和务虚性。又例如在对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评价时,认定其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穷兵黩武的祸国者,却看不到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断然拒绝日本人要其出任“华北王”时所体现出的民族气节。这些都是将历史人物绝对化、脸谱化的表现,事实上是一种不健康、不科学的评价观。
第二种是脱离历史背景,以今天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例如历史上对秦始皇的评论褒贬不一,主张“贬”的评价认为秦始皇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其维护王朝统治是以对劳苦大众的压迫为基础的,“焚书坑儒”甚至称得上是历史的倒退。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的“集权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做法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毛泽东早年就曾经讲过治理中国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又如有人批判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包含的“阴阳五行、迷信怪异”的内容是不科学的,以今天的病理学理论来看不值得借鉴。这种评价也很明显地脱离了历史的实际,“以现代的标准衡量古人,以偏概全,管窥蠡测,变得荒谬可笑”[1]P9。
第三种是习惯于“盖棺定论”,不擅于用发展的眼光来评价历史人物。这种评价观忽略了历史研究的相对真实性和科学性,不能历史地、动态地评价历史人物,轻易盲从定论,是一种片面的评价观。例如对陈独秀的批判曾经为其扣上了包括“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等在内的九顶帽子,然而随着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以及更多资料的解密,对陈独秀的评价逐渐客观公允,目前就只剩下“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一顶帽子。
二、千秋功过是与非,差异多因道和理——评价历史人物出现偏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评价标准各异
评价历史人物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结论大相径庭的原因很多,例如依据历史资料的真实性、评价历史人物时的主观性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评价标准的多元化。综观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可以将其集中归纳为“道”和“理”两个标准,即道德标准和理性标准。
所谓道德标准,就是用伦理学中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等概念,即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来评价历史事物(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例如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现代社会共有的道德规范,例如对“贪赃枉法、奢靡淫乱”等丑恶现象的否定,对“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等优良品质的肯定等。这些标准得到了人类的普遍认同,不为某一阶级所专有,不因时空转换变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正因为道德标准的普遍适用性,道德标准便成为人们评价历史事物最常见的标准。而所谓“理性标准”,也称为生产力标准,即以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为尺度的一种评价标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基本观点,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是认识和评价历史事物的根本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历史人物既符合道德标准,又符合理性标准,例如创造“康乾盛世”的两位清朝皇帝采取的轻徭薄赋、鼓励手工业、发展文化等措施,既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展现了开明君主的形象,又符合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如为革命倾注毕生心血的 “国父”孙中山,以 “三民主义”为纲领救中国,符合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其个人魅力使其在革命党人中一呼百应,甚至连反革命分子对他也较为尊崇。曾经背叛了革命的军阀陈炯明曾为孙中山亲拟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但由于历史的纷繁复杂,同时用道德标准和理性标准对同一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却会得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例如孟子 “孝悌忠信”和“民贵君轻”的思想符合道德评价的标准,但是他对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宣扬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成为为剥削制度作辩护的重要依据,这是与理性标准背道而驰的。又如对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孔子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其根本意思是认为孔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在道德标准和理性标准之间,究竟应该以哪个为主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以理性标准作评价,“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及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2],同时辅之以道德评价,力求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并提倡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汗牛充栋文加献,多法并举相与析——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的几条原则
历史是由无数相对真理集合而成的绝对真理。历史更是一种“过去式”,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总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因此,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借助于大量史学资料。国学宝典《四库全书》的编纂历时十五年之久,仅书籍资料的征集就耗时六年有余,最终形成了包括4部44类66个属的国学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在创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时,曾经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吨档案,花费了五年半的时间才完成这部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著作,其目的,就是要无限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然而,《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该书作者在资料收集时重“文”不重“献”,即只注重收集整理档案、文集、史书等“死”的资料,而忽略了当事人这一重要的“活”资料。 历史(History)一词源自于希腊语“Historie”,意思是“见证者”。这就说明,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研究历史事物的重要资料。《荷马史诗》就是一部由口头资料整理而成的口述史,其中包括特洛伊木马在内的很多传说已经被现代的考古研究所证实。因此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对近现代人物的研究可以通过广泛采访当事人的方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古代人物进行研究时,要注重对日记、书信等能够代表或接近第一手资料的文献进行考证。只有做到“文”“献”并重,才能研究好历史人物。
然而由于“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3]P96,史学资料和历史事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史学资料来自于各种混乱的、相互矛盾的、片面的和混乱的历史片断,经过一代代史学家的搜集整理,不可避免地便加入了个人的主观色彩和阶级立场,甚至还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史学资料甚至是对历史事实的伪造或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四库全书》中就存在着不少学术偏见和历史局限性。司马迁也曾说过他编纂《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P2735。这个“一家之言”就不言而喻地说明了其性质是价值判断的产物。因此,要运用史学资料研究人物,首先必须对史学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甄别和研究。这个甄别研究史学资料的过程就是“相”的方法,即对感性认识的整理和改造,这是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
“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5]P267。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则应该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这是研究历史人物最为关键的阶段,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析”。运用“析”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注意几条原则:
一是要承认阶级价值,坚持正确的立场。应该认识到历史认识不是体验性的感性认识,而是与价值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形成正确判断的前提。同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离开评价主体的主观性,不能离开阶级判断,否则评价就是无本之木。今天我们了解历史、评价历史,目的都应该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爱国主义立场,树立一切为党和国家的建设服务的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讲话中就讲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个概括就不仅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而且也符合团结参政党、做好统战工作的需要,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又如抗日战争期间,历史学家陈垣选择抗清思想家顾炎武作为研究对象,起到了激励抗日热情的作用。50年代我国曾隆重纪念过世界历史上的许多文化名人,比如拉伯雷、雨果等,这一举措对于促进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互相尊重、和平共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要坚持唯物史观,即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形成正确认识的灵魂。首先是要从客观存在而不是主观认识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例如,不能依晚清当局的性质和曾国藩朝廷重臣的身份而将其引领 “洋务运动”定性为“挽救清政府所作的最后挣扎”,而应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和进步意义。其次要与历史背景联系而非片面孤立地评价历史人物。例如,应该看到李鸿章的“卖国求荣”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悲剧,也应该看到陈独秀在屡次作出错误决策时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和干扰。再次是要用发展的而非静止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例如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就对作家们的性质作了敏锐而深刻的预测,即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最后是要坚持理性标准优先的原则,将历史人物的活动置于生产力标准之下。对此,史学家嵇文甫曾强调说:“所谓进步性乃是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言,只是从当时看,而不是从现在看。如果拿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古人,当然都不够格,都是落后的,还有什么进步性可言呢? ”[6]P9
三是要坚持“个人”原则。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就曾明确指出:应该重视历史人物的作用,敢于讲历史上的“个人”。评价历史人物固然应该坚持理性标准,将个人活动置于实践和生产力的标准之下,但是,不应该忽视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尤其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例如,两汉时期对西域的开发经营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但是如果没有武帝、明帝那样雄才大略的帝王,没有张骞、班超那样冒险绝域的英雄,没有卫青、霍去病及祭彤、窦固那样英勇果敢的统帅,没有成千上万的远征大军,那么两汉对西域的经营就不会有那样巨大的成就。但是,坚持“个人”原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杰出人物理想化和现代化,尤其是不能“文过饰非”,应看到“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论如何杰出,但比之我们今天的新的英雄人物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7]P296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邓小平也曾经说过,“要懂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8]P358因此,总结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目的都是要面向未来,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1][6]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问题》[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周世范.《中国历史精要》[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汉书》卷 62.《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7]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万 强
郭平阳,男,西安政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军队人才与人事管理。王 博,男,西安政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军队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