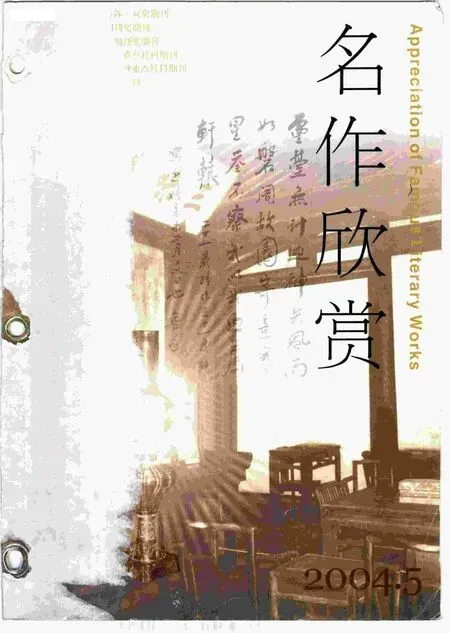马洛:康拉德的代言人
——修辞叙事理论视角下的《黑暗的心》的叙述者马洛
⊙林如心[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642]
马洛:康拉德的代言人
——修辞叙事理论视角下的《黑暗的心》的叙述者马洛
⊙林如心[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642]
从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出发,《黑暗的心》中的叙述者马洛是一个自觉的叙述者,同时也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是康拉德的代言人。修辞叙事理论视角下的叙述者马洛,是一种崭新的解读。
修辞 《黑暗的心》 叙述者 马洛 康拉德
美国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提出从“作者代理、文本现象、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序5)的修辞角度对叙事作品进行解读。依据费伦的这一相关理论,本文分析了《黑暗的心》中的叙述者马洛是一个自觉的叙述者,同时也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是康拉德的代言人,从而对马洛的叙述者功能作一次修辞解读的崭新尝试。
从根本上讲,《黑暗的心》是一部关于马洛讲述他到非洲营救库尔兹的经历的叙事。实际上,马洛的讲述是同故事叙述,确切地说,是自身故事的叙述。在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中,同故事叙述是指“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层面的叙述”。“当人物——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时”,“同故事叙述可以进一步确定为自身故事的叙述”。([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171)在马洛的讲述中,由于他既是一个叙述者又是一个人物,且还是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因此我们知道,马洛的讲述不仅是同故事叙述,而且是自身故事的叙述。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费伦相关的读者理论,对《黑暗的心》中马洛的叙述者功能这一特定的文本现象做出反应的是作者的读者和实际的读者(作者的读者即“假设的理想读者,作者就是为这种读者构思作品的,包括对这种读者的知识和信仰的假设”;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即“特性各异的你和我,我们的由社会构成的身份”)。([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111)而且,在反应过程中,读者同时采取了作者的读者和实际的读者这两种立场(费伦借鉴了拉比诺维茨的读者观,后者强调读者同时采取他所提到的各种立场)。([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111)
一、马洛是一个自觉的叙述者
根据费伦的相关理论,自觉的叙述者:(1)在叙述的时间视角说话;(2)常常就自己的叙述发表议论。①
读者发现:一方面,当马洛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他是在叙述的时间视角说话。他对整个故事的了解始终是他的视觉的组成部分,这使读者明白他是在讲述过去的经历;另一方面,马洛常常就自己的叙述发表议论。因此,在该叙事中,马洛是一个自觉的叙述者。
(一)马洛在叙述的时间视角说话
下面的例子足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当马洛讲述他很快得到任命前往非洲时,他说:“几个月后,当我设法找回他的尸体时,我才听说原先的冲突只是为几只母鸡而引起的。”②(第8页)在公司的办公地,马洛看到两个女人起劲地结着绒线,他说:“当我远在那儿时,我常常想起这两个女人,守护着通往黑暗世界的大门,手中结的黑绒线像是用来编织温暖的遮尸布。”(第11页)
通过上面例子中的“几个月后”、“当我远在那儿时”这些字眼,我们仿佛清楚地听到了马洛在向我们讲述他过去的经历。“根据杰拉尔德·热内特在旁观者与说话者,即视觉与声音之间所做的区别”([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译,2002:37),我们发现,康拉德典型地把我们置身于马洛在叙述进行时的视觉和声音之内。
(二)马洛常常就自己的叙述发表议论
这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黑人和白人的存在的议论
一方面,非洲大陆及黑人真实且亲切地存在着。
非洲大陆博大深邃。在航行中,马洛深深地被绵长的非洲海岸所吸引;远古森林的那种静寂的力量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汽船沿河上行进入到一个没有被文明世界的诸如印花布、玻璃珠子等产物所“点缀”的原始世界时,马洛感觉到正被“这个由植物、水和寂静组成的奇异世界的压倒一切的现实所围绕”(第43页)。虽然大自然的“内在的真理从不显山露水”(第43页),但他“仍然感觉到那种力量”(第43页),“感觉到它那种神秘的静寂”(第43页)。马洛叙述到,他那只小汽船缓慢地逆水而上,“如同一只在高大门廊的地板上爬行的呆呆的小甲虫”(第45页)。这,不正好说明了在大自然面前,号称文明的白人却显得如此的渺小吗?白人们渺小得无法读懂神秘的大自然;这,不也正好和他们的“白人优越论”形成强烈的对比吗?
在非洲的海岸边,惬意的涛声和时不时由黑人划出的小船让马洛产生瞬间的现实感。看到白人们的汽船缓缓滑过,海岸上那些“史前时代的人”(第45页)的纯粹反应是“快乐、恐惧、悲哀、忠诚、勇气、愤怒”(第 46 页),而这,马洛称之为“真理——剥去了时间外衣的真理”(第46页)。马洛断言,为了经历这种真实,白人们需要具备的是和黑人们一样拥有的“与生俱来的力量”(第46页)和“审慎的信仰”(第47页),而不是像“那种只要用力一摇就会纷纷飞落的布条”(第46页)的没用的“原则”。
另一方面,欧洲白人的存在则是孤寂、近乎虚幻的。
在叙事开头,刚刚到达非洲的马洛便感到越来越孤立,他发现他和那些莫名其妙地轰击非洲丛林、对着山崖进行毫无目的的爆炸、虐待黑人的白人们根本就不一样。当发现库尔兹在半夜里爬回岸上时,马洛断言说虽然库尔兹的灵魂也曾审视过自己,但他的“灵魂已经疯了”(第90页),因为他处在极端的孤寂中。在欧洲社会环境里,马洛讽刺到,多亏警察的维持,白人们才得以驱除心中那种“丑闻、绞架和疯人院的可怕的恐惧”(第65页)。
另外,马洛的议论还告诉读者:白人们的存在给人的感觉几乎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贸易站里那些手里拿着长长的棍棒、无所事事的朝圣者让马洛感到“这一辈子还从未见过如此虚幻的东西”(第28页)。贸易站貌似慈善实则是虚伪,白人们的工作等都是“虚幻缥缈”(第30页)的。即使是那个带着“绝对纯粹,无所谓得失,不求实效的冒险劲儿”(第73页)到非洲来的俄国商人看起来也是不真实的,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不太可能,无法解释”(第72-73页)。
综上所述,非洲大陆是“史前大地”(第45页),马洛的沿河上行仿佛是回到“创世之初”(第42页)的旅行;黑人是“史前时代”(第45页)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文明人的祖先。不言而喻,在黑人面前,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成了极大的讽刺!
2.对殖民主义的控诉
读者发现:马洛在议论中还揭露了殖民主义、西方文明的本质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控诉。
马洛到非洲的一个深刻感受是:白人是非洲的入侵者。他们在非洲海岸上建立了许多贸易口岸,其中有些地名在马洛“听来像是在一块肮脏的幕布前上演的一出污秽的闹剧的剧名”(第14页)。一艘法国军舰莫名其妙地疯狂地轰击一片大陆,有人却说他们在轰击“敌人”(第15页)。在公司贸易站,马洛第一次深刻体会到殖民行径的残暴(第17页)。马洛刚到非洲时见到的划船的黑人充满着活力,而他在地狱般的丛林中见到的黑人“甚至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生灵,只是疾病和饥饿的黑影而已”(第19页)。其实,这些即将像动物般死去的“黑影”让读者很快想起了马洛的断言,那就是:他在非洲看见了“暴力的魔鬼,贪婪的魔鬼和欲望的魔鬼”(第18页)。在中央贸易站,马洛也很快地发现:“左右着人们,驱动着人们”(第18页)的正是这些魔鬼!读者意识到:当马洛说“工作仍进行着”(第19页)时,实际上他是不无讽刺地、尖锐地指出了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大陆的不断的破坏以及他们对黑人的无休止的摧残!在公司贸易站,马洛还发现,所谓的西方“文明”只是一些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诸如锅炉、火车车厢等“文明”的装饰品。此外,公司会计师把账簿一本本放得整整齐齐的、欧洲白人按照定期合同合法地从海岸各地招来黑人劳力,白人们的这一系列行为其实是毫无意义和自欺欺人的。
马洛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白人们到非洲来的一个诱惑就是象牙。公司经理、制砖人以及朝圣者等把象牙当成上帝般朝拜。在公司经理的叔叔带领下的黄金国探险队那帮狂热的人“想的只是如何从大地的深处把宝藏挖出来,尽管这个意愿背后根本不存在什么道义,如同窃贼撬开保险箱时那样”(第38页)。马洛断言,对比起饥肠辘辘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约束能力的非洲“食人者”,欧洲白人必须为那体现了他们食人般的本质的在物质财富(象牙)面前张开吞噬之口的贪婪而感到负疚;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库尔兹,一个权力欲与物欲膨胀、在邪恶面前低头的人,则必然遭到我们的唾弃。
不能忽视的是,野人伙夫和黑人舵手都是所谓的西方“文明”的牺牲品。野人伙夫“是经过教化的一个典型”(第47页),他脑子里“塞满了令人进步的知识”,“仿佛被一种奇怪的魔力所奴役”。而曾被马洛的前任训练过的黑人舵手是马洛“所见过的傻瓜中最没主见的一个”(第58页)。在土人的进攻中,马洛发现要他保持安静,“倒不如去命令一棵树别在风中摇晃”(第59页)。可怜的他已经被训练得像白人一样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了。
二、马洛是康拉德的代言人
费伦采用了韦恩·C·布思对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区分。可靠的叙述者即“共用隐含作者之标准的叙述者,像隐含作者一样观照叙事中的事实”。([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82)不可靠的叙述者即“偏离隐含作者之标准和/或偏离隐含作者对叙事中事实的观照的叙述者”。([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82)布思的区分导致的一个重要阐释习惯“往往把这种区分与同故事叙述关联起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有一个人物——叙述者,不管这个人物是主人公、目击者或与行动相隔甚远的转述者,可靠性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82)另外,在同故事叙述中,“一个叙述者的人物可能是功能性的,甚至于充当隐含作者的替身,隐含作者通过这个替身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84)
如上所述,马洛的讲述不仅是同故事叙述,而且是自身故事的叙述。要特别注意的是,马洛作为叙述者的叙述是建立在他作为人物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事情的基础上的。因此,概括地说,马洛是主人公、目击者和叙述者。此外,众所周知,《黑暗的心》是一部自传作品,康拉德通过马洛向读者讲述他在非洲的亲身经历。因此,作为自觉的叙述者的马洛对于非洲大陆和黑人真实的存在、欧洲白人存在的孤寂与虚幻的叙述和议论,以及他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控诉,刚好体现了康拉德向读者揭露他在非洲所发现的真相的目的。也就是说,马洛共用了隐含的康拉德的标准,马洛的叙述是可靠的叙述,马洛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
不能忽略的还有一点,除了《黑暗的心》以外,作为叙述者和人物的马洛还出现在康拉德的一些其他作品中。在其著作《青春》的引言中,康拉德是这样说马洛的:“He haunts my hours of solitude,when,in silence,we lay our heads together in great comfort and harmony。”③
综上所述,马洛就是康拉德的代言人。换句话说,马洛就是康拉德的替身,康拉德通过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不过,说马洛是康拉德的代言人,并不等于说马洛就是完全的康拉德。费伦指出,“同故事叙述者的可靠性有时在叙事的整个进程中”会有所“波动”。([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2002:83)事实上读者也可以发现,叙事中有几处地方足以让我们窥见马洛模棱两可的态度。比如,马洛说“库尔兹先生根本不算是我的偶像”(第78页),但他很快又说“我甚至得像那些黑人一样唤醒他……他内心深处那高傲而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第89页),这令读者感到,对于马洛来说,库尔兹仿佛是某种需要给以抚慰的邪恶之神。又如,马洛因为库尔兹的非洲情妇很可能同他一起主持了某些“以一些无法形容出来的仪式作为结束”的子夜舞会而感到厌恶,但当她出现时,他却用“美丽绝伦”(第81页)等词来描述她。的确,马洛的这些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他的可靠性特权的程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马洛作为康拉德的代言人的叙述者功能,因为从根本上讲,马洛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
结 语
总之,在《黑暗的心》中,马洛是一个自觉的叙述者,他不但在叙述的时间视角说话,还常常就自己的叙述发表议论。正因为如此,读者才得以发现,马洛对于非洲大陆和黑人真实的存在、欧洲白人存在的孤寂与虚幻的叙述和议论,以及他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控诉,刚好体现了康拉德向读者揭露他在非洲所发现的真相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读者还发现,马洛共用了隐含的康拉德的标准,他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是康拉德的代言人。在这部作品中,通过马洛,康拉德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道德鞭笞、对所谓的西方文明提出了质疑。
① 费伦在Narrative as Rhetoric中的第一部分第三章中的Closing the Distance 和 the Paradox of Frederic’s Narration的相关内容中提到了这两种表明同故事叙述者的自觉性的迹象。
② 本文所使用的小说译本是《黑暗的心》,康拉德著,孙礼中、季忠民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该译本的引文页码在本文中均置于括号中,不另外注。
③ 见York Notes on Heart of Darkness,by Hena Maes-Jelinek,England:Longman York Press,1982,p.43.
[1] Hena Maes-Jelinek.York Notes on Heart of Darkness[M].England:Longman York Press,1982.
[2]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s,Audiences,Ethnics,Ideology[M].Ohio: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3]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 and the Secret Sharer[M].New York:Bantam Dell,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New York,1902.
[4] 康拉德.黑暗的心[M].孙礼中、季忠民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5][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J].国外文学(季刊),2002(2).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8s026)
作 者:林如心,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