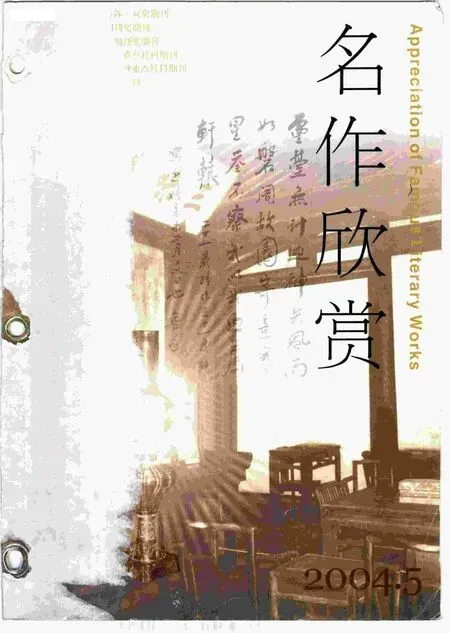书写新旧更替时代的女性生活
——凌叔华小说集《花之寺》的创作主题
⊙刘文菊[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广东 潮州 521041]
书写新旧更替时代的女性生活
——凌叔华小说集《花之寺》的创作主题
⊙刘文菊[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广东 潮州 521041]
凌叔华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的创作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映闺中少女的黯淡生活;二是揭示太太阶层的庸俗生活;三是展现新式妻子的矛盾生活。凌叔华用讽刺与悲悯的手法书写新旧更替时代的女性生活,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倡导女性的独立和解放。
凌叔华 《花之寺》 创作主题
凌叔华1928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由十二篇短篇小说组成。小说集的创作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映闺中少女的黯淡生活。刻画豪门闺秀的内心世界,表现旧式少女无法主宰命运的失落和茫然,讽刺和怜悯她们悲剧性的命运,有《绣枕》《吃茶》《茶会以后》《再见》《说有这么一回事》《等》;二是揭示太太阶层的庸俗生活。揭露旧式太太寄生虫般的生活,审视和批判她们麻木丑陋的灵魂,有《中秋晚》《太太》《有福气的人》;三是展现新式妻子的矛盾生活。表现新女性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禁锢的痛苦和无奈,肯定和突显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有《酒后》《花之寺》《春天》。凌叔华以清婉细腻的笔致、清逸淡雅的风格、讽刺悲悯的手法,塑造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书写新旧更替时代隐秘的女性生活,镌刻一代女性的历史印痕,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发展图景,倡导女性的独立和解放。
一、反映闺中少女的黯淡生活
凌叔华擅长描写闺中少女微妙的心理变化和黯淡的生活处境,如《绣枕》中以精美绣枕寄托婚姻愿望的大小姐、《吃茶》中因误会而遭受爱情创伤的芳影、《茶会以后》中对现代生活感到无所适从的阿英和阿珠姐妹、《再见》中不愿与昔日男友再续旧情的筱秋、《说有这么一回事》中伤悼姐妹情谊的云罗和曼影、《等》中在期盼中等来了未婚夫死讯的阿秋。与同时代庐隐《海滨故人》中追求爱情自由的露莎、白薇《打出幽灵塔》中以死抗击父权压迫的萧月林相比,这些婉顺的旧小姐是被时代抛弃到角隅中的女性。凌叔华借助隐喻性的意象讲述“老中国最后一代豪门贵族之女的经历和命运”,揭示“那隐秘、灰暗、无意义、无价值的一面”①,刻画“高门巨族的精魂”②,通过讽刺性的情节表现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借助隐喻性的意象刻画闺中少女的心理
凌叔华把敏锐细腻、真切传神的传统写意画技巧融进小说创作,通过富有韵味的意象来刻画旧式少女细小隐蔽、曲折微妙的心理变化,如《茶会以后》中的花、《吃茶》中的镜子、《绣枕》中的绣枕等,这些意象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性,喻体与人物有相似性,是女性心理和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1.“花”的意象
小说集中多次出现“花”的意象。如《吃茶》中忽明忽暗的花影象征着芳影由灿烂变为黯淡的爱情梦想、《茶会以后》中残败的花象征着阿英和阿珠稍纵即逝的美好青春、《绣枕》中灰色的荷花象征着大小姐被践踏的爱情理想、《再见》中迎风招展的盛开秋芙象征着筱秋与昔日男友相逢时的喜悦心情。“花”成为书写女性命运的载体,达到花人互喻、花人合一的境界。《吃茶》中久居深闺的芳影误以为留洋学生王斌爱慕自己,爱的感觉就像花影一样朦胧模糊、忽明忽暗,她“看着窗上花影因日光忽明忽暗,花枝因微风摇曳,婀娜生姿,只觉得心里满满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③。等到误会揭开的时候,她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望着窗上的花影,依旧是因风摇曳,日光却一阵阵的浅淡”,幽暗的花影映衬着内心的惨淡,隐喻了她尴尬难堪的人生处境。《绣枕》中的大小姐冒着酷暑精心绣制一对靠枕,“一个绣的是荷花和翠鸟,那一个绣的是一只凤凰站在石山上。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娇嫩羞涩、鲜艳欲滴的粉红色荷花是大小姐萌动的少女情怀。可是,寄寓了美好愿望的绣枕无情地被践踏,“真可惜,这样好看东西毁了”,“这荷花不行了,都成了灰色”,被毁掉的是大小姐的梦想,像灰色一样黯淡了的是大小姐的命运。
2.“镜子”的意象
小说集多次出现的另一个意象是“镜子”。幽居女性通过照镜子表达自恋与自怜,透过镜子可以洞察深闺少女的妙密心理。如《茶会以后》中当阿英想到茶会上张家二小姐“那对双眼皮的眼,圆溜溜地转,倒不错”,便也对着镜子学起来,“镜里的她也正溜着圆圆的眼珠”,镜子的意象不仅揭示了阿英对现代时尚生活既排斥又羡慕的矛盾心理,也揭示了她们被时代悬置在半空中的尴尬处境。《吃茶》中镜子成了芳影的知心朋友,“只有那妆台上一方镜子,她不但不想疏远,还时时刻刻想去看看她”,镜中的她幽怨自怜,她在镜中幻想着甜蜜的幸福生活:一时诗情画意都奔向她的心头和眼底……未了想到“水晶帘下看梳头”,她连镜子都不好意思看了。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切仿佛水中月镜中花,自作多情的误会让爱情的幻想彻底破灭。镜子成了表现旧式少女惆怅迷惘的心理和残酷命运的喻体。
除此之外,“绣枕”也是一个经典的意象,是大小姐本体生命的隐喻和象征,绣枕和大小姐互为喻体,最终被玷污的绣枕,“不仅暗示着男性社会对女性的粗暴蹂躏,而且似乎也表现出整整一套上流社会的优雅与美,连同这位旧式高门巨族的大小姐一道,逝去了黄金时代并再没有生路。”④
(二)通过讽刺性的情节书写闺中少女的悲剧命运
大多数“五四”女作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创作自传体或准自传体小说,如庐隐《海滨故人》、白薇《悲剧生涯》、苏雪林《棘心》等。凌叔华的创作则不同,她借鉴契诃夫的小说叙事技巧,选择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运用客观写实的叙事风格,在平静淡泊的叙述语调中,通过“讽刺与悲悯兼容”⑤的手法来表现女性的悲剧命运。如《绣枕》《吃茶》《茶会以后》《再见》在情节上都有着反讽性的场面和结局。夏志清教授认为《绣枕》是“中国第一篇依靠着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⑥。大小姐希望通过展示精巧的女红以求得美好的姻缘,然而具有莫大的讽刺性意味的是,两年之后“好看极了”的绣枕又辗转回到了大小姐面前,只不过已是面目全非、污迹斑斑,原因是寄寓着纯洁爱情的绣枕在送去的当天就被践踏,后又凄惨地流落到下人手中,小说通过“绣枕图”和“伤枕图”⑦两幅讽刺性的生活横截图,展现大小姐微妙的心理变化,表露对行将就木的闺阁传统的哀婉与嘲讽。在这几篇小说中,除了鲜明的讽刺色彩外,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的温情和悲悯之心,对于这些旧式少女,作者并没有进行激烈的批判和嘲讽,而是在温和的讽刺和宽容的批评中表现出同情之心,正如沈从文所说,“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⑧。
二、揭示太太阶层的庸俗生活
小说集也刻画了一群庸俗的太太,如《中秋晚》中愚昧无知、笃信天命的敬仁太太;《太太》中贪图享乐、爱慕虚荣的太太。她们深受封建旧文化的毒害,不思进取、落后平庸,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最后一批残留物。凌叔华深刻地审视这群庸常之辈,无情地批判她们空虚庸俗的生活和令人憎恶的行径。这群太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旧文化心理的牺牲品;二是新旧文明夹缝中的寄生虫。
(一)旧文化心理的牺牲品
《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毫无自我生命价值内涵和精神特质,她把全部的幸福都寄托在仪式化的迷信铭记:“吃团鸭—团圆,不吃团鸭—恶兆”⑨,并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信仰膜拜这种封建文化,在恐惧、迷茫、无知中将自我的生命意义消解殆尽。《中秋晚》借鉴契诃夫小说的回环往复式结构,写了这个家庭在四个中秋之夜的变故。在新婚的第一个中秋节晚上,太太精心准备了一桌团圆宴,她笃信“吃了团圆宴,一年不会分离”,但两人因敬仁去料理干姐后事没有吃团鸭而发生口角,并且打碎了供过神的花瓶,太太将这一切均视为恶兆,从此夫妻失和。到第四年,家道败落,夫妻流离失所。面对这一切,太太认为这是她命中注定的,她没能认识到悲剧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封建旧文化心理。《有福气的人》中的章老太也是旧文化迷信心理的牺牲品,凡是不遵循封建习俗的东西她都要诅咒。这类被封建旧文化所毒害的旧式太太,彻底丧失了灵魂,她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是如此可鄙可悲。
(二)新旧文明夹缝中的寄生虫
《太太》中的太太爱慕虚荣、贪图享乐,把家庭、丈夫、孩子抛在自我生活之外,似乎挣脱了传统妇女“三从四德”的束缚:不打理家务,热衷赌牌,女儿没棉鞋冻坏了脚,丈夫的袍子和金表也被典当。这类太太有着庸俗市民的劣根性,她们既舍弃了传统女性的良好品德,又没有获得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成了最彻底的寄生虫,她们“兼容并蓄的是两种生活方式中最富于寄生性的特点”⑩。《太太》中的太太与冰心《两个家庭》中的陈太太如出一辙,冰心通过描写现代新女性亚茜和传统陈太太两个家庭截然相反的命运,倡导“新贤妻良母主义”,主张现代女性“为女”和“为人”的统一。凌叔华对庸俗太太阶层的批判,与冰心有异曲同工之妙,旨在揭示寄生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夹缝中的旧式太太面临悲剧命运的原因,是传统贤妻良母的美德与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精神的双重沦丧。
三、展现新式妻子的矛盾生活
小说集还塑造了徘徊在现代女性精神与传统性别角色之间的新式知识女性妻子,如《花之寺》中冒名女性读者给丈夫写情书到花之寺约会的燕倩;《酒后》中对异性朋友产生“一吻之求”冲动的采苕;《春天》中在琴声春愁中忆念昔日男友的霄音。这些新式妻子的婚姻生活挣扎在旧道德与新思想之间,具有双重人格和矛盾心理。燕倩们婚姻里的“杯酒风波”传达出女性解放的新观念:婚姻并非女性实现人生价值唯一的终极点,唯婚恋至上、把婚姻当职业的传统爱情婚姻观已岌岌可危。
(一)突显新式妻子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
《酒后》中微醉的妻子采苕要丈夫永璋同意她去吻一吻醉卧的异性朋友子仪,永璋深爱着娇妻,沉浸在甜蜜的婚姻生活中,采苕却对丈夫的柔情蜜意充耳不闻,子仪是她爱慕已久的朋友,虽然最后她又决定不吻了,但是这种诉求却表现了女性想要争取作为一个妻子以外的另一种权利,一种除了爱与被爱之外,还能有自己的情感天地和人生追求的权利,这一心理也是家庭女性试图超越夫妻之爱的大胆尝试。与丁西林改编的同名独幕剧相比,更加突显出小说独特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视角,剧本以丈夫为中心、以男性为视角,嘲讽和揶揄妻子的冲动与妄想;而小说则以双重视点的叙述视角,以采苕为叙事主体“表现女性自觉意识的冲动”⑪,突显了女性的主体精神。《春天》展示了同一主题,霄音提笔给昔日男友写信以表安慰之情,怕被丈夫知晓又将信纸搓成团擦桌子再扔进字纸篓,霄音的内心潜藏着不安宁的生命律动,沉睡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萌动,她想寻找女性作为妻子这一性别角色之外的价值主体,表达她渴望平等自由、独立自主的精神追求。
(二)表现新式妻子割裂的内心世界
新型家庭中的新式妻子有着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禁锢的努力,她们尝试着挣脱传统男权文化的束缚,但这种抗争和叛逆又是不彻底的,鲁迅曾对这种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作了分析:“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⑫这类新式妻子的内心世界被割裂开了:一方面,她们作为一个独立于男性之外的主体,有新的价值观念和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她们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酒后》中采苕在与丈夫的关系中,妻子的性别角色规定了她在行为上只能是个被动者,是丈夫的附属品,她必须恪守妇道、忠诚守节;在与朋友子仪的关系中,她扮演的是一个主动的爱慕者和追求者,是具有独立意识和主体精神的新女性。作为一个矛盾分裂体的采苕无法完成亲吻行动,何希凡教授认为“酒后的醉态产生了超常态的心理颤动波澜”,最终还是“将这一切还原为波澜不惊的温馨与宁静”。⑬《花之寺》中的燕倩同样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既是安分守己的妻子,又是不安分的情人,在这两种角色的转换中,既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又体现了传统角色和现代女性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燕倩们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禁锢的努力“都展示了拥有了新妻子身份的女性试图恢复叛逆之女的独立自主、张扬个性的渴望,以及囿于太太角色的道德规范不得不压抑、放弃自我欲望和力量的痛苦无奈”⑭。
综上所述,小说集《花之寺》塑造了高门巨族的闺中小姐、市民阶层的庸俗太太、新型家庭中的新式妻子,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从横轴上看,这三种不同的女性群体并存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展现了“五四”新旧更替时代纷繁复杂的女性生存现状;从纵轴上看,女儿,妻子、母亲这三种不同社会性别角色的女性群体展现了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些女性形象看似是不同的个体,实则是相互转换、互为一体的,婉顺隐忍的大小姐、芳影、阿秋可能就是婚后的敬仁太太;爱慕虚荣的阿英、阿珠可能就是庸俗的太太;傲然卓立的筱秋可能就是追求新生活的采苕、燕倩。与其他“五四”女作家所礼赞的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叛逆之女相比,凌叔华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或许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不具理想性和感召性,但却是一份贴近历史的、真实的女性经验,是一份对“五四”女性文学独特的贡献。夏志清教授曾对凌叔华的文学创造才能作了很高的评价,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凌叔华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①④⑤⑨⑩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4,75,76,78,80.
②⑫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0.
③ 凌叔华.花之寺 女人 小哥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
⑥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8.
⑦ 崔涛.画意淋漓风怀清逸——论凌叔华小说的绘画美[J],名作欣赏,2008(4):57-60.
⑧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74.
⑪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4.
⑬ 何希凡.夜阑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读凌叔华小说《酒后》[J],名作欣赏,2008(2):37-39.
⑭ 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128.
作 者:刘文菊,文学硕士,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